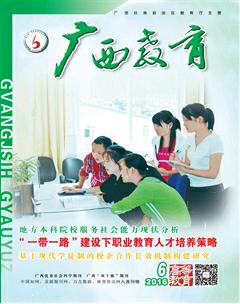廣西民族院校旅游英語教學改革探析
李新荷
【摘 要】分析廣西多民族地區對旅游人才的需求,以廣西民族院校旅游管理專業本科生作為研究對象,從課程設置、教材選用、教學模式、師資建設方面對旅游英語教學改革進行探討,旨在為旅游英語專業人才的培養提供參考。
【關鍵詞】廣西 民族院校 旅游英語 教學改革
【中圖分類號】G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450-9889(2016)06C-0130-02
隨著經濟全球化以及區域經濟一體化趨勢的不斷加強,中國—東盟戰略伙伴關系日益密切,廣西以其多民族地區獨特風土人情、便利的地理位置、豐富的自然旅游資源、日漸完善的服務設施每年都吸引了大批的入境游客。游客的增長意味著對旅游英語專業人才需求的大量增加。少數民族地區獨特的風俗文化決定了這些地區所需的旅游英語人才具備的知識和條件要區別于普通的旅游英語人才。旅游英語人才的素質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該地區的國際旅游服務水平,同時也直接關系到該地區的國際旅游行業的發展,甚至會影響到該地區在國際上的形象。民族類院校旨在為少數民族地區的經濟文化事業發展培養高素質的人才,此類院校的學生構成與其他普通院校不同,少數民族學生占相當大的部分,少數民族學生基礎教育和成長的環境背景與發達地區的學生很不一樣,這要求教師要針對少數民族學生的特點進行課程的設置,采取不同的教學模式來達到人才培養的目標。
一、旅游英語課程性質
旅游英語是英語專業旅游方向和旅游管理的專業必修課程。學生通過該課程的學習,掌握旅游英語的基本語言特點,熟練掌握旅游行業及學科的術語,學習旅游管理英語詞匯及旅游專業英語的特定表達方式,了解旅游業的基礎知識,掌握本行業、本專業最新動向,掌握實用文體的寫作,并能夠實踐中理論聯系實際,更好地服務于社會。
旅游英語屬于專門用途英語,它具有兩大明顯的特點:一是使用者有明確的使用范圍,即由于特定行業的需要,使用者在其工作領域內必須使用英語;二是有特殊的語言內容,即專門化內容。教師在進行課程設置時應將本課程的特點與少數民族學生的特點相結合,設計出合理的課程設置。
二、課程設置
針對廣西民族院校學生以及旅游英語課程的特點,本文在旅游英語課程設置方面提出了以下幾個需要改善的地方:
(一)夯實基礎,開設語音課程。大部分本科高校將旅游英語這門課程安排在大三時開設,大學英語是其先修基礎課程。民族類院校的招生按照國家政策向少數民族考生傾斜,因此這類院校有一半以上的學生是來自基礎教育較為落后的的少數民族地區。因客觀條件的限制和方言的影響,少數民族學生的英語聽說能力普遍不強,有些學生在語音方面存在系統性的缺陷。在筆者教授的三屆旅游管理專業的學生中,有不少的少數民族學生因受方言的影響,無法辨別和完整的發出清輔音,例如把[p]發成[b]、[t]發成[d]、[f]發成[v]。要想糾正這種系統性的語音缺陷,需要學生努力去修正,同時也需要教師花費很大的時間和精力去指導。英語聽說對于涉外旅游行業的實踐尤為重要,因而民族院校要非常重視大學一、二年級的基礎階段的英語學習。同時,教師在進行基礎英語階段的課程設置時應考慮開設專門的語音課程以規范學生的發音,進而提高學生的聽說技能水平。
(二)完善專業課程設置。本科院校中開設旅游英語課程的一般是英語專業和旅游管理專業,兩個專業的課程設置對于旅游英語課程的學習各有利弊。英語專業一般學習過跨文化交際相關的課程,因此在旅游英語課程學習過程中,英語專業的學生更容易理解學習材料以及不同國家之間的文化差異。但是旅游行業的專業知識的不足,有時候也會讓學生在學習的過程中遇到很多的困難,如術語、行業運營流程等。旅游管理專業的學生則反之,他們專業知識有系統的學習,但是跨文化的知識卻非常的匱乏,這同樣讓他們在學習過程中產生很多的困惑。因此課程的設置應考慮增加跨文化交際相關的課程,這對于從事國際旅游行業的從業人員是至關重要的。
三、教材的選擇
當下出版的旅游英語教材不少,但很多教授旅游英語的教師反映用得稱心的教材并沒有多少。有些教材過于陳舊,出版時間和所選擇的文本材料都已經不適用于當今的旅游行業。另外,有不少教材片面地強調“大而全”,導致教材的內容過于寬泛,沒有針對性,內容深度不足。還有些教材在內容的安排上只側重某一方面的技能學習,很大一部分的教材沒有設計聽說譯的內容,而僅有文本閱讀的內容,這不利于培養學生全面的語言技能。鑒于此,本文提出幾個改進的措施。
(一)選用符合學生水平、地區特點的教材。廣西的民族院校學生有一半以上是來自基礎教育落后地區,學生的英語基礎,尤其是英語聽說水平相對于發達地區仍然存在較大的差距。此外,少數民族學生因家庭經濟條件限制,很少有旅行的經歷,特別是遠途旅行,因此學生的視野受此局限,旅行體驗、對旅游景點的認知和跨文化知識相對不足。鑒于此,選擇符合少數民族學生特點的教材對實現旅游英語人才培養的目標極其重要。教師選擇的教材應符合以下的要求:
1.教材內容的難度要符合學生的水平,不宜太難,最好不要選擇原版的英文材料。
2.教材內容應涵蓋聽說讀寫譯幾個方面,并設置相應的訓練項目或習題。
3.教材要有適當的跨文化知識的補充,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彌補少數民族學生這方面知識的不足。
(二)教研組自編補充教材。民族院校是專門為少數民族地區培養高素質專業人才的機構,其大部分畢業生畢業后主要工作服務的地方還是民族地區,因此教材的內容最好是能與地方的旅游行業、旅游資源相關的材料。但是,現存的旅游英語教材多是面向發達地區的,這些教材未能很好地結合當前廣西民族地區旅游發展的現實需要,因此很難形成與培養目標相適應的風格和特色。鑒于此,在未能選擇到滿意的教材的情況下,教師可考慮自編和改編教材。McDonough & Shaw 認為,有 5 種改編教材的方法,即增補、刪減、簡化、修改、重組。教師可通過網絡、圖書館渠道收集整理與本地旅游行業、旅游資源相關的英文材料,并將之運用于教學實踐。
四、教學模式
Hutchinson & Waters 認為專門用途英語內容以及教學方式均取決于學習者的學習需求,因而與普通英語在內容與教學方式上存在著一定的差異。Strevens 認為,專門用途英語教學的目的和內容,主要或全部不是由普通教育的目標來決定的,而是由學習者對英語的功能和實際應用的需求所決定,因而二者有著不同的教學目的和內容。以上學者認為教學設計應圍繞學習和應用的需求來進行,因此教師在可以在以下幾個方面進行改進:
(一)以學生為中心,多樣化教學。少數民族學生多來自教育欠發達地區,受當地教育的硬件和軟件條件的限制,他們在基礎教育階段接受的多是傳統單一的教學模式。而旅游英語是一門專業性、實踐性很強的課程,對聽說讀寫譯各個方面的技能提出更高的要求,僅僅依靠傳統的教學模式自然無法達到理想的學習效果。教師在教學的實施過程中應以學生的興趣愛好、學習需求為中心,采取多樣化的教學模式。在教學設計上教師應考慮最佳的教學形式和方法,如課堂討論、角色扮演、學生課堂展示等,讓學生充分參與到課堂教學中,以此激發學生的學習熱情,同時參與過程中更好地理解和掌握課程知識。如在教授Itinerary(旅游線路)這個單元時,筆者先讓學生在課堂上談論他們認為最難忘的一次旅游經歷,進而引導學生思考如何進行旅游線路的設計。在學生的討論結束之后,教師和學生一起學習課文中提供的幾個成功的旅游線路設計的案例,分析旅游線路中的英語文字表述的語言特點、線路設計的成功之處。在學習課文的案例之后,筆者鼓勵學生通過利用網絡、圖書館,以及實地考察等途徑,親自為本地設計一個旅游線路,并準備好在課堂上進行展示。這樣的教學設計既能理論聯系實踐,又可以激發學生的積極主動性,讓學生真正地掌握這章節的內容。
(二)以行業需求為導向,充分利用實訓室和實踐基地進行實踐教學。旅游英語是一門實踐性很強的學科,教師在教授過程中應以行業的需求為導向進行教學的設計。隨著中國—東盟自貿區的建成和中國—東盟博覽會永久落戶廣西南寧,廣西的入境旅游行業面臨著全新的發展機遇,這迫切需要我們培養出更多適應廣西與東盟旅游業發展的人才。廣西民族院校的旅游英語的教學也應適應發展的趨勢,關注行業的新動向,及時更新教學材料,積極改進教學手段。此外,各高校應加大對實訓設施和實訓基地的投入,讓學生在實踐中學習。教師應充分利用這些條件,進行模擬教學、模擬訓練,在實訓中切實提高學生的行業技能。筆者教學計劃中的理論課時和實踐課時的比例是1∶1,經過近三年的教學,筆者發現實踐教學選擇在實訓室中進行模擬訓練的效果非常的好。首先,這樣比較接近真實的環境,更能激發學生的興趣和積極性,學生們在進入實訓室之前愿意花更多的時間和精力去做資料查詢、英語材料撰寫等前期的準備工作。其次,學生在模擬訓練時也更加的投入,更加的專注。由于本地的經濟比較落后,民族院校無法得到足夠的資金、技術和當地企業的支持,這導致民族院校在實訓室、實習基地方面的建設方面還存在很多不足的地方,這需要學校和政府共同克服困難,從各方籌措資金用于投資,積極聯系相關企業共建實習合作平臺,從而改善實訓室、實訓基地建設落后的局面。
五、師資隊伍建設
當前,在高等院校中教授旅游英語的教師多為外語系的普通英語教師,多數教師本科和研究生階段學習的專業和旅游行業的知識聯系并不多。而本門課程的專業性和實踐性要求教師必須具備外語和旅游兩個專業的知識,新形勢的發展也對旅游英語的教師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雙師型”教師的建設迫在眉睫。“雙師型”教師的培養一方面需要英語和旅游兩個不同專業的教師之間相互學習;另一方面學校要積極與企事業單位合作,派教師到企業實習,邀請有豐富從業經驗的專業人員到校進行培訓。教師自身的知識結構完善和教學技能的提高是實現人才培養目標的前提。
【參考文獻】
[1]莫莉莉.專門用途英語教學與研究[M].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8
[2]McDonough,J.and Shaw, C.Materials and Methods in ELT[M].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1993
[3]Hutchinson,T.&Waters,A.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A learning-centered approach [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7
[4]Strevens,P.ESP after twenty years; a re-appraisal [C]//in M.Tickoo(ed.).ESP:State of the Art.Singapore: SEAMEO Regional Language Centre,1988
(責編 黎 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