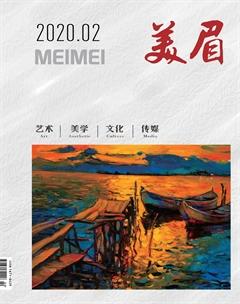音樂(lè)表述中的再現(xiàn)性
墨日根高娃
關(guān)鍵詞:體裁;無(wú)伴奏合唱;語(yǔ)法;語(yǔ)義
合唱是以多聲部人聲為表現(xiàn)形式的音樂(lè)藝術(shù),能最直接地表達(dá)音樂(lè)作品的思想感情。合唱藝術(shù)的最高形式是無(wú)伴奏合唱。在無(wú)伴奏合唱作品中,欣賞者能夠發(fā)現(xiàn)美的形式,觸及美的情感,感悟美的內(nèi)涵。在穿越時(shí)代、跨越地域的蒙古族無(wú)伴奏合唱藝術(shù)中,人們能夠欣賞到節(jié)奏之美、旋律之美、和聲之美、復(fù)調(diào)之美、織體之美等聲樂(lè)之美。
一、從體裁看蒙古族無(wú)伴奏合唱的產(chǎn)生和演變
錢(qián)亦平、王丹丹的《西方音樂(lè)體裁及形式的演進(jìn)》中提到了“體裁”是文藝作品的種類(lèi)或樣式。而體裁作為音樂(lè)語(yǔ)言的表述方式,包含音樂(lè)功能、音樂(lè)形態(tài)、音樂(lè)風(fēng)格、音樂(lè)規(guī)模及審美理念等內(nèi)容。隨著蒙古族的繁衍發(fā)展,蒙古族音樂(lè)作為源于生活、折射生活的藝術(shù)形式,呈現(xiàn)出明顯的類(lèi)化特征。以抽象音響作為符號(hào)的藝術(shù)形式,通過(guò)異質(zhì)同構(gòu)的形態(tài),音符連續(xù)地行進(jìn)游走等引起情緒上不同的變化。情感類(lèi)化的體裁模式,被視為文藝作品的樣式與種類(lèi),為把握作品的思想情感提供了依據(jù)。蒙古族無(wú)伴奏合唱作為一種獨(dú)特的音樂(lè)樣式,具有較穩(wěn)定、較成熟的機(jī)構(gòu)規(guī)則和情感體現(xiàn),對(duì)于藝術(shù)的創(chuàng)作生產(chǎn)者,體裁就是概括生活、升華生活的框架,把各種零星雜亂的表象進(jìn)行重組,從而建構(gòu)新的意象,這就是蒙古族無(wú)伴奏合唱中經(jīng)常出現(xiàn)的馬形象、額吉形象、羊羔形象、草原形象、勒勒車(chē)形象、奶茶奶食形象等體現(xiàn);對(duì)于藝術(shù)的二度創(chuàng)造者來(lái)說(shuō),體裁是二度創(chuàng)造者再現(xiàn)藝術(shù)形象的目標(biāo),對(duì)原有構(gòu)成要素的特定體會(huì)去感受一度創(chuàng)作者的內(nèi)心情感細(xì)節(jié),從而精準(zhǔn)無(wú)誤地詮釋本真的音樂(lè)形象;對(duì)于欣賞觀(guān)摩者,體裁是讓對(duì)象了解音樂(lè)內(nèi)容暗示,通過(guò)欣賞去領(lǐng)略作品的感情內(nèi)涵。由此可見(jiàn),體裁具有情感符號(hào)的意義,對(duì)于創(chuàng)作、表演、欣賞這三個(gè)層面的實(shí)踐體來(lái)講,都暗示了其實(shí)踐的意象。聲樂(lè)發(fā)展早于器樂(lè),無(wú)伴奏合唱源自歐洲,在中世紀(jì),教會(huì)是文化藝術(shù)的中心,一切文化、教育、藝術(shù)都受教會(huì)統(tǒng)攝,音樂(lè)方面更是教會(huì)音樂(lè)占據(jù)統(tǒng)治地位。無(wú)伴奏合唱更加注重和諧,在音質(zhì)的表達(dá)上體現(xiàn)了一定程度的隨機(jī)性。哲學(xué)家們認(rèn)為被人聲感動(dòng)是自然的,被樂(lè)器感動(dòng)是不道德的,提倡用純?nèi)寺晛?lái)凈化民眾的心,作曲家的創(chuàng)作也都局限在單一的宗教聲樂(lè)題材,如格里高利圣詠、奧爾加農(nóng)、迪斯康特、坎蒂加、彌撒曲、經(jīng)文歌等。隨著歷史的發(fā)展,時(shí)代風(fēng)格的變遷,蒙古族無(wú)伴奏合唱在不同的歷史時(shí)期、不同維度創(chuàng)作中,在保持最基本的多聲部結(jié)構(gòu)形式和蒙古族風(fēng)格元素基礎(chǔ)上,又呈現(xiàn)出多種多樣的藝術(shù)形象。作曲家的創(chuàng)作手法愈發(fā)成熟,使無(wú)伴奏合唱這一音樂(lè)形式的表現(xiàn)潛力得到挖掘,最后能承載更多濃郁的民族情緒,這個(gè)過(guò)程體現(xiàn)了和諧的審美觀(guān)。
二、蒙古族無(wú)伴奏合唱的語(yǔ)法分析
楊春時(shí)的《藝術(shù)符號(hào)與解釋》中對(duì)語(yǔ)法給出了一定的定義,藝術(shù)符號(hào)是繼承了原始符號(hào)的內(nèi)涵語(yǔ)法。相對(duì)外研語(yǔ)法而言,內(nèi)涵語(yǔ)法是根據(jù)符號(hào)的內(nèi)容含義進(jìn)行符號(hào)的意向組合。藝術(shù)作品的內(nèi)容一般情況是要通過(guò)藝術(shù)語(yǔ)言去表達(dá)和交流的。“語(yǔ)言”并不是專(zhuān)指所謂的“文學(xué)語(yǔ)言”,而是包括了一切藝術(shù)門(mén)類(lèi)種類(lèi)中的許多表現(xiàn)手段,所以,音樂(lè)中的節(jié)奏、音質(zhì)、音色、旋律、和聲、聲部、織體、組合、配器等多種藝術(shù)表現(xiàn)手段都被統(tǒng)稱(chēng)為音樂(lè)的語(yǔ)言。如音樂(lè)旋律中,有某一片段的曲調(diào)連續(xù)使用,這是反復(fù)語(yǔ)法。在聽(tīng)到的旋律中,作曲家利用人們熟悉作品的音調(diào)片段與動(dòng)機(jī),引起觀(guān)眾聽(tīng)眾的聯(lián)想,這就是借代語(yǔ)法。旋律中,上下兩個(gè)樂(lè)句沒(méi)有接近相似的因素,這是對(duì)比語(yǔ)法。旋律中,有三個(gè)樂(lè)句以上結(jié)構(gòu)相同的音調(diào)連續(xù)出現(xiàn),這就是排比手法。蒙古族無(wú)伴奏合唱的語(yǔ)音,常用核心主題縈繞貫穿出現(xiàn),核心主題是賦予音樂(lè)獨(dú)有的性格特征面貌,是具有少數(shù)民族音樂(lè)的語(yǔ)言特殊表情含義的音形音調(diào)進(jìn)行的聚攏形式。盡管核心主題在形式上是多變的,并且可以從固定成型的狀態(tài)中分解、融化在其他表現(xiàn)形式中,這樣就把“轉(zhuǎn)喻”的原型形象,在通過(guò)特有的、明確的、固定的結(jié)構(gòu)形式將原樂(lè)句的對(duì)比、擴(kuò)展的其他模式予以意象化的組合,形成創(chuàng)新,形成風(fēng)格,顯現(xiàn)的審美意義。核心主題是蒙古族無(wú)伴奏合唱特有存在和決定作品性格的主導(dǎo)因素。音樂(lè)的敘事方式不同于文字的敘事方式,無(wú)法明確地對(duì)人物、地點(diǎn)、情景、發(fā)展、結(jié)束做出具體細(xì)化的描述,只能通過(guò)特定節(jié)奏、音型、音調(diào)、音色等要素的呈現(xiàn)和變換,通過(guò)異制同構(gòu)的原理來(lái)象征性地描述。音樂(lè)的敘事方式是采用原始符號(hào)的意象組合形式,即內(nèi)涵語(yǔ)法,將音響意象以音樂(lè)特殊的構(gòu)成方式進(jìn)行排列組合。核心主題在音樂(lè)作品中的反復(fù)出現(xiàn),加強(qiáng)欣賞者的感受,強(qiáng)化音樂(lè)形象的畫(huà)面。蒙古族無(wú)伴奏合唱中動(dòng)機(jī)是音樂(lè)發(fā)展的種子性因素,賦予蒙古族音樂(lè)元素獨(dú)特的性格特征,對(duì)音樂(lè)本身來(lái)說(shuō)至關(guān)重要,色·恩克巴雅爾創(chuàng)作的《八駿贊》《大地之聲》、永儒布創(chuàng)作的《孤獨(dú)的白駝羔》《諾恩吉雅》的主題動(dòng)機(jī)中頻繁使用大小二度及增減音程,動(dòng)機(jī)的外形多變,從凝固的成型狀態(tài)逐漸演變?yōu)槎喾N飄忽的意向組合,也會(huì)運(yùn)用多個(gè)動(dòng)機(jī)的發(fā)展成多個(gè)段落主題,風(fēng)格不失地域味道,藝術(shù)效果構(gòu)成審美意象。蒙古族無(wú)伴奏合唱的語(yǔ)法是理解蒙古族音樂(lè)內(nèi)涵的鑰匙。
三、蒙古族無(wú)伴奏合唱的語(yǔ)義分析
人們普遍認(rèn)為,音樂(lè)就是一種“純藝術(shù)”,而不是一種語(yǔ)言,也沒(méi)有所謂的語(yǔ)義性。然而,在整個(gè)音樂(lè)歷史發(fā)展的進(jìn)程中,隨處可見(jiàn)對(duì)音樂(lè)語(yǔ)義性的表述與解釋。音樂(lè)的語(yǔ)義性是相對(duì)其傳統(tǒng)意義上的非語(yǔ)義性而言,音樂(lè)具有語(yǔ)義性就藝術(shù)本體而言有其重要的美學(xué)含義,其形成取決于語(yǔ)言音調(diào)和音樂(lè)音調(diào)的關(guān)系,音樂(lè)的互動(dòng)性與音樂(lè)的聯(lián)想。正因?yàn)橐魳?lè)的語(yǔ)義作用,才讓音樂(lè)具有傳情達(dá)意的功能。法國(guó)浪漫派作曲家、指揮家柏遼茲在談到音樂(lè)的表現(xiàn)時(shí)說(shuō), 在試圖描寫(xiě)密林、清泉、荒漠、雪地、湖泊、田野、山川、日升日落等現(xiàn)象時(shí), 只能描寫(xiě)這些自然界物質(zhì)對(duì)人們的視覺(jué)沖擊和感覺(jué)。音樂(lè)則可以充分表現(xiàn)出甜美的愛(ài)情與無(wú)休止的嫉妒、憂(yōu)傷的心情與熱情的派對(duì), 但是不能夠準(zhǔn)確表現(xiàn)引起這些心理情感的具體事物。蒙古族音樂(lè)語(yǔ)言的使用,在無(wú)伴奏合唱這一藝術(shù)門(mén)類(lèi)中得到充分的提煉和升華,是對(duì)語(yǔ)言語(yǔ)義準(zhǔn)確合理地運(yùn)用, 快慢結(jié)合、抑揚(yáng)頓挫、承上啟下、輕重緩急以及多樣的語(yǔ)氣,都帶給觀(guān)眾不同的情感。沒(méi)有系統(tǒng)地學(xué)習(xí)語(yǔ)言,我們無(wú)法讀懂或聽(tīng)懂異國(guó)文化的語(yǔ)言和文字,但是音樂(lè)是無(wú)國(guó)界的,是能表情達(dá)意的藝術(shù)門(mén)類(lèi),加之音樂(lè)的代入力、感染力、煽動(dòng)力等能觸動(dòng)人們的心弦去思索、去遐想、去憧憬、去向往、去感受異域文化。比如永儒布創(chuàng)作的長(zhǎng)調(diào)與無(wú)伴奏合唱《孤獨(dú)的白駝羔》,開(kāi)始部分人聲部分的演唱就會(huì)使人們產(chǎn)生憐惜的小駝羔沒(méi)有奶吃的情緒,長(zhǎng)調(diào)領(lǐng)唱的哼唱讓人恍如親眼見(jiàn)到那一條寒風(fēng)中無(wú)助的小駝羔,身臨其境那種悲涼的氛圍。這就是由音樂(lè)聯(lián)想到的對(duì)象開(kāi)始誘發(fā)、觸動(dòng)、感悟、憧憬與之相關(guān)聯(lián)的聯(lián)想,從而使聽(tīng)眾對(duì)音樂(lè)的理解變得更加清晰、透徹、準(zhǔn)確,并由理解到欣賞到喜愛(ài),在感悟上是豐富的、直觀(guān)的。音樂(lè)作品通過(guò)不同音色音質(zhì)的音響,可以直接模仿被表現(xiàn)對(duì)象所特有的聲音與動(dòng)靜。比如蒙古族特有的樂(lè)器馬頭琴,在色·恩克巴雅爾創(chuàng)作的無(wú)伴奏合唱《蒙古靴》與永儒布創(chuàng)作的《漂亮的黑色走馬》中都有模仿馬蹄踏地的節(jié)奏、馬的喘氣、馬的嘶鳴、馬的奔騰、馬的力量,觀(guān)眾不由地聯(lián)想到馬背民族的熱烈、豪邁粗獷、不拘小節(jié)的民族性格及蒙古人生活的場(chǎng)景寫(xiě)照。音樂(lè)有語(yǔ)義,自古以來(lái)“ 悅”與“說(shuō)”通用。《禮記·樂(lè)記》的一段論述中,用“說(shuō)”而不用“悅”,是有其含義的。“說(shuō)”包含了語(yǔ)義、情感等一切所欲表達(dá)的內(nèi)容,“ 悅”則是有情感之含義。法國(guó)哲學(xué)家、文學(xué)家盧梭認(rèn)為,音樂(lè)旋律不僅會(huì)模擬, 它還會(huì)說(shuō)話(huà), 它的語(yǔ)言是非分節(jié)語(yǔ), 而是活的、激情的、熱烈的語(yǔ)言, 它包含了比詞語(yǔ)本身大一百倍的力量。蒙古族無(wú)伴奏合唱能將心靈的一切活動(dòng)再現(xiàn)出來(lái)、表達(dá)出來(lái),而且使你看到生活的一切,看到生命是怎樣熄滅而歸于寂靜的。
無(wú)伴奏合唱這一音樂(lè)形式是構(gòu)成蒙古族風(fēng)格最重要的部分之一。蒙古族無(wú)伴奏合唱體裁的發(fā)展,離不開(kāi)許多蒙古族作曲家持之以恒的努力,在不斷突破前人,不斷創(chuàng)新的創(chuàng)作中融入了時(shí)下最進(jìn)步的社會(huì)思潮和人們的理想,目前,這門(mén)音樂(lè)藝術(shù)已經(jīng)完全成熟,并且深受全國(guó)乃至世界聽(tīng)眾歡迎和喜愛(ài)。在欣賞蒙古族無(wú)伴奏合唱時(shí),應(yīng)該時(shí)刻把握體裁發(fā)展的脈絡(luò)和線(xiàn)索,對(duì)不同時(shí)期體裁形態(tài)產(chǎn)生的變化給予精準(zhǔn)和深入的分析梳理,要深刻理解促進(jìn)體裁演變和后續(xù)發(fā)展的社會(huì)原因。音樂(lè)和語(yǔ)言的相似之處在于它們都是交流工具,都能做到“有所說(shuō)”,如果將蒙古族無(wú)伴奏合唱音樂(lè)視為一種語(yǔ)言游戲,強(qiáng)調(diào)的正是音樂(lè)本身的“說(shuō)”的形式和交流功能。語(yǔ)法語(yǔ)義不是文學(xué)的專(zhuān)利,音樂(lè)較之前者,由于有了“情感”的助力和基調(diào),語(yǔ)法性、語(yǔ)義性更強(qiáng)。音樂(lè)作品具有了意義,才能為聽(tīng)眾所理解、所認(rèn)可、所喜愛(ài)、具有意義的蒙古族無(wú)伴奏合唱也就必然具有更強(qiáng)的語(yǔ)義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