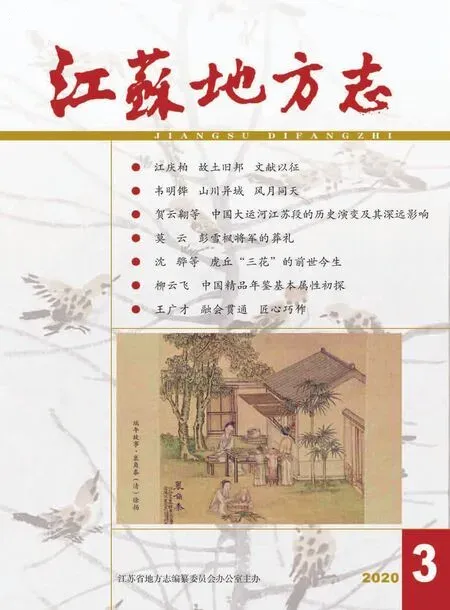從馮夢龍《山歌》談吳歌的傳承與發(fā)展
◎ 侯楷煒(蘇州市相城區(qū)地方志辦公室,江蘇蘇州215133)
提 要:吳地山歌又稱吳歌,其產(chǎn)生發(fā)展源遠流長,流傳區(qū)域早已不限于吳語地區(qū)。明代中晚期,是吳歌發(fā)展的極盛時期,馮夢龍就是這個時期最具影響力的代表人物。他以大量的精力從事吳歌俗曲的采集、整理、編輯、評點,刊印了《掛枝兒》《山歌》兩本民歌專集,對我國的民間文學(xué)事業(yè)作出了重大的貢獻。作為馮夢龍家鄉(xiāng)和吳歌傳唱中心的蘇州,新中國成立以來,在吳歌的挖掘、研究方面做了大量工作。2006年,吳歌被列入首批國家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保護名錄。近幾年來,隨著馮夢龍文化研究的不斷深入,在吳歌的保護與傳承、創(chuàng)新與發(fā)展方面開展了一系列的活動,取得了一定成果,對于弘揚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繁榮新時代文化事業(yè)具有十分重要的現(xiàn)實意義。

江蘇馮夢龍山歌會
吳歌,是我國傳統(tǒng)文化寶庫中一筆珍貴的文化遺產(chǎn),是吳文化中的一顆璀璨明珠。吳歌作為一種文化現(xiàn)象,伴隨著先民的生產(chǎn)勞動、祭祀習(xí)俗和生活娛樂活動而發(fā)生發(fā)展,它和古代的“楚聲”“蔡謳”“越吟”等同屬“南國之風(fēng)”,與古典文學(xué)的精粹唐詩、宋詞、元曲并列于我國的文學(xué)之林。蘇州藝壇上的“三朵花”昆曲、評彈、蘇劇,其淵源都離不開吳歌。
一
吳歌包括“歌”和“謠”兩個部分。“歌”即“山歌”,也包括一些俗曲之類,“謠”接近于“順口溜”。吳歌在內(nèi)容上承載著吳地(指蘇、浙、滬一帶的吳語地區(qū))人民的生活史跡,反映下層人民的思想感情、喜怒哀樂和理想愿望,也可以說是江南農(nóng)民和下層市民的生活史。它的歌詞內(nèi)容來自生活,反映生活,表現(xiàn)在勞動、生活、思想、愛情等方方面面,豐富多彩,具有社會認(rèn)識、教育、娛樂、審美等功能,是觀察吳語地區(qū)社會生活、風(fēng)情民俗的重要手段。吳歌既包括情歌,又包括勞動歌、時政歌、儀式歌及童謠兒歌等。吳歌在形式上有其淳樸清麗的風(fēng)格,委婉動聽的曲調(diào),含蓄延綿、溫柔敦厚的語言和深厚的水文化特點。它猶如涓涓流水一般,清新亮麗,一波三折,柔韌而含情脈脈,與吳儂軟語有相同的格調(diào),有其獨特的民間藝術(shù)魅力。
明代,吳歌有了很大的發(fā)展。特別是明代中葉,隨著城市經(jīng)濟的發(fā)展,市民隊伍的壯大,民歌也在城鎮(zhèn)流行起來,并很快進入一個繁榮階段。當(dāng)時,中國南北各地流傳著各種小調(diào)和山歌,這些小調(diào)和山歌達到了“不問南北,不問男女,不問老幼良賤,人人習(xí)之,亦人人喜聽之”[1]的程度,就像當(dāng)今的流行歌曲。明代文學(xué)家卓人月曾說:“我明詩讓唐,詞讓宋,曲又讓元,庶幾吳歌《掛枝兒》《羅江怨》《打棗竿》《銀絞絲》之類,為我明一絕耳。”[2]這些民歌有幾種固定的曲牌,其曲調(diào)優(yōu)美動聽,而且好記易學(xué),就是不識字的村姑野夫,也可以即興編了詞來唱,用來表達他們內(nèi)心的憂喜。這種小調(diào)和山歌與當(dāng)時文人們嘔心瀝血、字斟句酌寫成的作品大異其趣。它以真實、通俗、生動、強大的藝術(shù)力量,沖擊著封建正統(tǒng)文學(xué),也影響了一部分文人,使他們開始愛上這類為正統(tǒng)士大夫們不屑一顧的創(chuàng)作。他們把這些小調(diào)和山歌記錄下來。例如龔正我輯有《急催玉歌》,程萬里輯有《蘇州疊疊錦》,醉月子輯有《吳歌》等。其時的馮夢龍也注意及此,而熱愛程度則遠勝他人。他給民歌以很高的評價,稱世上“但有假詩文,無假山歌,則以山歌不與詩文爭名,故不屑假。茍其不屑假,而吾藉以存真,不亦可乎?”[3]他認(rèn)為可以“借男女之真情,發(fā)名教之偽藥。”用男女的真情,去揭露封建禮教的虛偽性。他以極大的熱情,深入到民間,親自耳聆筆錄,整理了《掛枝兒》和《山歌》兩本民歌集,使明代以前的800余首時尚小曲免于湮沒。
二
馮夢龍收集整理民歌時,態(tài)度十分認(rèn)真嚴(yán)肅。他選擇的標(biāo)準(zhǔn)是“情真”,即要有真情實感。同時,也注重語言、韻律、聲腔和風(fēng)格特色。采集時基本上保持了民歌的原樣,即使有個別改動,大都用附注說明。對于有些幽僻的方言,他或用眉批標(biāo)出字音、字義,或在末尾點明方言俗語的意思。因為民眾沒有曲律知識,他們唱歌只憑自己的感覺,所以唱詞總有不協(xié)之處,馮夢龍只是做了一些糾偏補弊工作。萬歷三十八年(1610)馮夢龍37歲時,《掛枝兒》(又名《童癡一弄》)一刊印問世,即受到各方重視,“馮生掛枝兒,譽滿天下”,不少人“靡然傾動,至有覆家破產(chǎn)者”。[4]但同時他也受到社會上一部分正統(tǒng)文人的攻擊,連他的父兄也“群起而訐之”。然而,馮夢龍并不氣餒膽怯,接著又續(xù)編了《山歌》一書。馮夢龍編的《山歌》(又名《童癡二弄》),實際上是一部以蘇州為中心的吳語地區(qū)民間歌謠總集。它多用吳語,是現(xiàn)存明代民歌中保存吳地山歌數(shù)量最多的,也是我國歷史上比較系統(tǒng)的民歌專集。
《辭源》載:“山歌,榜人(即舟子)所歌,吳(蘇州一帶)人多能之,即所謂水調(diào)也。”[5]在農(nóng)耕時代,山歌是一種自娛自樂的載體,它既豐富了鄉(xiāng)間單調(diào)的農(nóng)村生活,又給勞累田間的農(nóng)民以鼓勁打氣。它一邊傳唱著吳地的風(fēng)俗物產(chǎn),一邊起著教化民眾的作用。蘇州地處吳語地區(qū)的中心,也是吳歌創(chuàng)作與傳唱的中心。馮夢龍生活在蘇州,搜集整理《山歌》,自然有其得天獨厚的條件。他輯注的《山歌》全書十卷六類。私情四句、雜詠兩句,私情舊體,私情長歌,雜詠長歌,桐城時興歌,計359首,不過現(xiàn)流行的傳經(jīng)堂本只有345首,國學(xué)珍本文庫本只有259首,這些小曲的來源全同《掛枝兒》。最短的七言四句,最長的《燒香娘娘》1460余言。從內(nèi)容來看,有反映市民生活的,有描寫勞動生產(chǎn)的,但絕大多數(shù)是情歌。
馮夢龍收集民歌的內(nèi)容之所以大多是愛情生活,是由民歌的實際內(nèi)容決定的。生息繁衍后代,是人類社會的第一要義。當(dāng)人類告別自己的童年,家庭成為社會的細(xì)胞后,便產(chǎn)生了只有人類才有的感情——情愛。即使是階級壓迫極端殘酷,經(jīng)濟生活十分貧困,戰(zhàn)爭十分慘苦的年代,人類的情愛生活也不會停止,這便是民歌中大都是愛情內(nèi)容的根本原因。特別在封建禮教的統(tǒng)治下,女子沒有機會結(jié)識異性,一直信奉的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女孩子嫁雞隨雞,嫁狗隨狗。一個女子跟自己的丈夫通常是沒有愛情的,她們要求改變呆滯寡聞的生活常規(guī),追求解放,向往以愛情為基礎(chǔ)的美滿婚姻。從馮夢龍收集的山歌中,我們觸摸到的是吳地青年男女大膽追求幸福愛情的一顆顆鮮活的心。《山歌》中對愛情的歌唱粗獷熱烈、純真樸素、一往情深,表現(xiàn)了人民反對封建禮教束縛,要求自由婚姻、個性解放的強烈心聲,具有高度的藝術(shù)技巧和魅人的力量。
馮夢龍的《山歌》中還包含了吳地飲食文化、婦女服飾及民間文化娛樂、節(jié)慶活動等豐富的內(nèi)容,從中看到明代吳語地區(qū)的風(fēng)俗民情,對研究民歌的發(fā)展以及明代社會生活均有參考作用。特別是書前編者所寫的《敘山歌》及書中大量評注,更是研究馮夢龍民間文藝思想的重要資料,也是馮夢龍對中國民歌乃至中國俗文化的貢獻所在。

三
我國有史以來,對吳歌的理論研究及文字記載十分有限,這與歷代上層社會對民間文化的偏見有關(guān)。在封建社會里,山歌被貶為下里巴人之作,不登大雅之堂。直到“五四”前后,隨著新文化運動的崛起,以魯迅為代表的一批具有先進思想的新知識分子將視角投向民間,民間文化才逐步受到正視,歌謠運動成為當(dāng)時民主運動的一個組成部分,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以北京大學(xué)創(chuàng)辦的《歌謠》周刊為引領(lǐng),打破封建文化桎梏,讓平民百姓的歌謠登上舞臺,成為學(xué)術(shù)研究的對象。蘇州作為馮夢龍的家鄉(xiāng)及吳歌的傳唱中心,當(dāng)時這些學(xué)者中蘇州籍的就有好幾位。其中顧頡剛編印的《吳歌甲集》及之后的吳歌乙集、丙集、丁集、戊集、己集、《吳歌小史》等,為馮夢龍之后的又一壯舉,在中國歌謠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新中國建立以來,蘇州地區(qū)在吳歌的挖掘、傳承與發(fā)展方面做了大量工作。1952年,蘇南地區(qū)開展了大規(guī)模的民間音樂采風(fēng)活動,《解放日報》記者鄭煌在吳江農(nóng)村進行“抗美援朝愛國日”采訪時,第一次從農(nóng)婦口中把長篇吳歌《五姑娘》完整地記錄下來;1956年常熟縣村村建立山歌隊,并自1958年起多次舉辦“萬人山歌會”;1979年,蘇州市文聯(lián)編了《吳歌新集》,之后常熟縣的《民歌十二首》、吳江縣的《吳江民歌》相繼出版;1981年,蘇州市民間文藝家協(xié)會開始搜集紀(jì)錄長篇敘事山歌《五姑娘》,并于同年在蘇州召開的江、浙、滬首次吳歌學(xué)術(shù)討論會上推出;1983年,蘇州郊區(qū)長青鄉(xiāng)發(fā)現(xiàn)吳歌《趙圣關(guān)》,吳縣鎮(zhèn)湖鄉(xiāng)發(fā)現(xiàn)長歌《孟姜女》等,同年第二次吳歌學(xué)術(shù)討論會在吳縣召開;1984年,蘇州市文聯(lián)和市民間文藝家協(xié)會編輯的《吳歌》出版;1987年,中國俗文學(xué)學(xué)會在蘇州召開“馮夢龍學(xué)術(shù)討論會”;1989年,吳歌學(xué)會編纂的《江南十大民間敘事詩》出版;1994年,蘇州民俗博物館開設(shè)“吳歌廳”;1995年,建成全國首家山歌館——白茆山歌館;2000年,常熟市發(fā)現(xiàn)長篇敘事山歌《白六姐》。2002年至今,《中國·白茆山歌集》《吳歌精華》《吳歌遺產(chǎn)集萃》《中國·蘆墟山歌集》《中國·吳歌論壇》《水鄉(xiāng)情歌》《陽澄漁歌》《中國·同里宣卷集》等相繼出版。此間,每個縣、市都編印、出版了自己的吳歌集成,甚至有不少鄉(xiāng)鎮(zhèn)也都有自己的民歌集、山歌譜。
2006年,吳歌被列為首批國家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代表作保護名錄,蘇州各級基層政府,更加重視對民間文化的挖掘保護。如常熟市沙家浜鎮(zhèn),由文化站牽頭,組成專業(yè)班子,深入石灣村,經(jīng)過一年多時間的努力,排出民歌手40多名,從他們口中搜集到各類山歌400多首。除文字資料外,還記錄下曲譜,并出版了《石灣山歌集成》。他們又將這些山歌手請進景區(qū),增添了一道亮麗的風(fēng)景線。近年,這些山歌手們還分別帶有徒弟,保證了山歌的傳承和發(fā)展。姑蘇區(qū)白洋灣街道的居民,原來大都是農(nóng)民,街道組織了大學(xué)生村官進行社會調(diào)查,對民間流傳的山歌、故事進行搜集,組織歌手們座談、獻唱。經(jīng)過兩年時間的挖掘、整理,搜集到各種山歌100余首,還組建了一支居民山歌隊。
蘇州相城區(qū)的陽澄湖鎮(zhèn),以盛產(chǎn)大閘蟹聞名,但那里的“陽澄漁歌”也蜚聲文壇,且有其獨特的水鄉(xiāng)風(fēng)情。20世紀(jì)80年代,吳縣文化館、蘇州市文聯(lián)就組織專人進行采風(fēng),發(fā)現(xiàn)了一批歌手,對散落在民間的漁歌進行了挖掘、整理。近年,地方政府和文化部門加大力度,培養(yǎng)新人,注重傳承。2007年,相城區(qū)文聯(lián)、陽澄湖鎮(zhèn)政府聯(lián)合編印了《陽澄漁歌》專集。2011年,馮夢龍故里——相城區(qū)黃埭鎮(zhèn)馮埂上,被中國社科院文研所、江蘇省民間文藝家協(xié)會和復(fù)旦大學(xué)分別列為馮夢龍的研究基地、采風(fēng)基地和研究生社會實踐基地,在民間文學(xué)(包括吳歌)的挖掘、保護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2015年,黃埭鎮(zhèn)組建了馮夢龍山歌藝術(shù)團,改編、創(chuàng)作了一批有關(guān)馮夢龍的山歌;連續(xù)舉辦兩屆“江蘇省馮夢龍山歌會”;開展“馮夢龍文化進校園——中小學(xué)生唱山歌活動”;舉辦了“蘇州市馮夢龍山歌達人賽”等。在馮夢龍的家鄉(xiāng),場頭、田頭、街頭、公園、校園、小區(qū),到處都能聽到馮夢龍的山歌。
吳歌在漫長的歷史發(fā)展過程中,也是不斷地發(fā)展變化的。作為歷史文化遺產(chǎn),它有頑強的生命力和永久的藝術(shù)魅力。它的發(fā)展變化,體現(xiàn)了時代特征。馮夢龍的山歌以情歌為多,勞動人民通過唱山歌用以抒發(fā)感情,表達愛情,消除疲勞,愉悅身心。隨著時代的變遷,人們生活方式的改變,山歌同樣發(fā)生了很大的變化。在演唱內(nèi)容上,以健康向上為主,保留原來山歌風(fēng)趣幽默、含蓄詼諧、富有鄉(xiāng)土味的特點,唱發(fā)展形勢,唱新人新事;在音樂旋律上,改原來的低沉緩慢為高亢嘹亮;在演出形式上,改原來的無伴奏獨唱、對唱為有伴舞、伴唱;在演出場合方面,改原來的田頭、場頭為專題歌會或舞臺演出,燈光、道具、服飾等一應(yīng)俱全。
改革開放以來,吳歌在保護、傳承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績。但應(yīng)該看到,民間依然留存著許多珍貴的吳歌遺存,挖掘、保護還大有工作可做,發(fā)展、創(chuàng)新更是我們的職責(z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