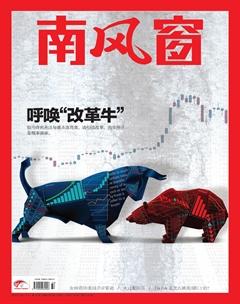為什么政治正確變成了“理性的專政”?
高霈寧

由黑人男子弗洛伊德之死所引發的抗議示威活動,其影響已經蔓延到了其他領域,好萊塢和學術界首當其沖。這并不令人奇怪,因為政治正確在這兩個領域中的影響從來都不可小覷。
“政治正確”這個詞出現于20世紀70年代,它主要是用來諷刺在言論上過度保護弱勢群體的教條主義傾向。政治正確的誕生有其獨特的歷史背景,它的興起與半個多世紀前的黑人民權運動和女權主義運動是分不開的。
這個時期的左翼運動無疑是具有歷史進步意義的。然而隨著平等的理念逐漸深入人心,并在各個領域取得壓倒性優勢之后,一種新形式的“壓迫”卻出現了。芝加哥大學政治學教授艾倫·布魯姆在《美國精神的封閉》一書中寫道,左派思想的一統天下實際上禁錮了社會的思想自由,讓人們意識不到還有其他的可能性。他甚至將其稱為一種“暴政”。1990年《福布斯》雜志在一篇文章中將政治正確比喻為“思想警察”。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在2017年進行的一項民意調查顯示,71%的美國人認為政治正確已經讓社會無法正常討論重要問題,58%的美國人迫于政治環境的壓力不敢表達他們的個人政治觀點。
左翼運動對平等的追求原本是為了保護人們的自由,但是卻逐漸走向了自由的反面。打破枷鎖的錘子最后卻變成了新的枷鎖。為何會出現如此諷刺的一幕?要回答這個問題,就需要從左翼運動的思想源頭中去尋找答案。
羅爾斯的警告
1971年哈佛大學哲學系教授約翰·羅爾斯出版了一本重要著作《正義論》。這本書被學界譽為“二次大戰后倫理學、政治哲學領域中最重要的理論著作”。《紐約時報書評》曾評價羅爾斯對自由主義理論的歷史貢獻堪比密爾和康德。
羅爾斯在《正義論》中開宗明義地告訴讀者,他的目的就是要證明,通過犧牲少數人的自由來為多數人換取利益是不正義的。《正義論》之所以能夠獲得巨大的社會聲譽,并不僅僅在于其理論上的貢獻,更在于它為當時美國的左翼思潮提供了哲學的基礎。
在《正義論》中,羅爾斯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如果在一個社會中,每個人都擁有不同的信仰,不同的利益,還有不同的天性稟賦,那么什么樣的社會制度才是正義的?或者換言之,在一個多元的社會中,怎樣設計社會制度才能保護所有人的自由?
這個問題的難點在于,不管由哪個人來回答,他都只會從自己的立場出發,認為符合自己利益的制度才是正義的,這樣也就不可能有一個統一的答案。于是,羅爾斯提出了一個“無知之幕”的思想實驗。所謂“無知之幕”,就是指每個人事先假設并不知道自己的私人利益是什么,而僅僅從一個抽象的社會成員的角度來考慮正義的問題。如果所有人都能自愿站在“無知之幕”的背后,那么這樣集體設計出來的制度就不會摻雜任何人的私利,因而是正義的。
此外,羅爾斯還提出了一個重要的觀點,即正義的制度應當保證弱勢群體利益的最大化。他認為,無知之幕背后的每個人都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弱勢群體,所以他們必須設計一個保護弱勢群體的制度,以免自己可能受到不公平的待遇。打一個比方,這個過程就像安排某個人來切蛋糕,并規定這個人最后將隨機分得其中一塊,那么按照羅爾斯的觀點,這個切蛋糕的人一定會盡量把所有蛋糕切成一樣大小,免得自己最后分到最小一塊。
羅爾斯在后期反思道,《正義論》中所構建的正義理論如果真的要在現實中推行,就不得不訴諸強制手段,也就是說必須以“正義”的名義強迫人們改變信仰。
羅爾斯的這一觀點在左派中極具代表性,因為它從哲學層面論證了為什么要反對種族歧視、性別歧視以及其他各種形式的歧視。《正義論》與黑人民權運動和女權運動遙相呼應,被左派人士奉為圭臬。
在《正義論》出版之后的20多年里,羅爾斯的思想卻也在發生深刻的變化,因為他發現《正義論》中存在一個致命的缺陷。
“無知之幕”這個思想模型的最大難題在于:如何才能讓人們自愿接受它?羅爾斯承認,現實中的每個人都是自私自利的,那怎么可能讓這些“精致的利己主義者”放下一己之私,去照顧其他人的利益呢?在《正義論》中,羅爾斯給出的解決方案是在形而上學的層面再構建一個“大我”。這個“大我”不同于現實中形形色色的“小我”,因為“大我”唯一在乎的就是公共利益。所以他認為,只有當社會中所有人都在思想上接受了這個“大我”之后,才能克服“小我”之私,讓正義在現實中落地。
但是羅爾斯后來意識到,這種想法其實相當危險。因為在一個多元的社會里,每個人的自由就體現為對自我利益的追求。而且,在像美國這樣一個80%以上的人口擁有宗教信仰的國家,自我利益的實現又在很大程度上以信仰自由為前提。如果要求社會中所有人都必須在頭腦中樹立一個無私的“大我”,那么勢必會與他們原有的信仰相沖突。
羅爾斯在后期反思道,《正義論》中所構建的正義理論如果真的要在現實中推行,就不得不訴諸強制手段,也就是說必須以“正義”的名義強迫人們改變信仰。但這絕非羅爾斯的初衷。他始終堅信,一個正義的社會制度應當基于每個成員的自發認同,而非強迫。
正義正在走向它的反面。被左派視為精神導師的羅爾斯從理論上已經洞察到了左翼運動正在走向歧路,并試圖為其尋找一條新的出路。1993年,他出版了另一本著作《政治自由主義》。在這本書里,羅爾斯不再把正義抬得那么高,而是把它明確限定在政治領域(或者說公共領域),同時把信仰安置在私人領域—讓政治與信仰井水不犯河水。他這樣做顯然是為了調和正義與信仰自由,但很難說這一努力是成功的,因為他對政治領域和私人領域所做二元劃分很可能只是一廂情愿的想法。在晚年與哈貝馬斯的對話中,羅爾斯自己也坦承還有很多兩難問題沒有辦法解決。
同時,左派對羅爾斯的思想轉變也不買賬,認為他從《正義論》中的立場上后退了。盡管《政治自由主義》凝結了羅爾斯一生最后20多年的思考,但是卻遠不及《正義論》受世人追捧。

當時正值20世紀90年代初期,隨著蘇聯的轟然解體,知識界洋溢著對現有制度的道德優越感,很難聽得進羅爾斯發出的“雜音”。羅爾斯發出的警告并沒有引起世人足夠的重視。
事實上,羅爾斯并也非第一個質疑這種意識形態的“吹哨人”。20世紀初的德國法學家卡爾·施米特更早就指出,民主制必然會走向理性專政。
被強迫的“自由”
施米特對民主的批評主要基于盧梭的社會契約論。
社會契約論所要解決的核心問題是國家權力的正當性。國家權力無疑是一種暴力,但怎樣使用這種暴力才是正當的呢?盧梭給出的答案是,國家權力的運用必須獲得全體社會成員的認可才行。
今天的美國社會早已沒有了上世紀90年代初的那份自信和樂觀。左翼運動的弊端逐漸顯現,人們對政治正確日益感到厭倦。
根據盧梭的社會契約論,國家應該是由一群原本無拘無束的自由人通過共同訂立契約建立的。訂立契約的根本目的是共同保護每個人的生命和財富,所以每個人在這個集體中都會不會失去任何自由。這個契約因為代表著大家共同的意志,就叫作公意。
如果僅僅從這一層面來看,公意與羅爾斯的“正義”一樣都是為了保護大家的自由,并沒有什么不妥。但是盧梭眼中的公意還有另一面,就是每個人必須無條件地服從公意,而且不能有任何和公意相沖突的私人利益。如果有人不服從公意,那就要動用暴力強迫他服從。用盧梭的話來說,“人民要迫使他自由”。
以公意的名義強迫人自由,就好像以正義的名義強迫人平等,其目的都在于消滅個人的私利。在公意和正義之中,個體已經消融在集體之中看不清面目。每個人都變成了沒有個性,沒有私利的符號,僅以“人民”的名義抽象地存在著。
施米特敏銳地抓住了盧梭理論中的這一內在張力,直言民主制度在本質上就是自相矛盾的。人民,用施米特的話來說,就是一只“五彩的多頭怪獸”。一萬個人就會有一萬個想法,一萬種利益。根本不可能把所有人的意見統一起來。但是民主制度卻要求人民必須形成一個統一意志。而這個統一的意志一旦出現,就成了具有統治地位的觀念,或者說成為了一種意識形態。
從表面上看,意識形態不過是知識分子們之間的口舌之爭,書齋中的思考離現實政治的刀光劍影還距離十萬八千里。但是施米特一針見血地指出,如果某種更高觀念的統治不同時意味著代表這種觀念的人的統治,那么這種觀念的統治就是毫無意義的。
在現代社會,“平等”“自由”這些自帶光環的大詞具有不容置疑的正當性。但何謂平等?自由的邊界在哪?這些問題迄今并沒有唯一的答案,每個人都可以給出自己的解釋。誰能夠代表民眾、代表平等、代表自由,誰也就可以名正言順地打壓持不同意見者。施米特將這種統治形式稱之為“理性專政”。
所以施米特認為真正的民主制是不存在的,民主必然走向理性專政。但理性專政者并不以個人的名義進行統治,而是自稱代表民眾、代表真理、代表歷史進步的方向,并給政敵貼上“無知”和“落后”的標簽。權力與真理在民主制中合二為一。就像法國大革命時期,羅蘭夫人在臨刑前的感嘆:“自由,多少罪惡假汝之名以行。”
在群眾性運動中,被激情裹挾的街頭群眾更容易披上“人民”的外衣,扮演理性專政者的角色。群眾的激情洶涌澎湃又蔓延無度,其他人唯有謹言慎行才可能避免成為被攻擊的目標。在美國當前發生這場反種族主義運動中,《老友記》編劇含淚道歉,HBO Max主動下架《亂世佳人》,Nature自責是“白人學術機構”,嚴格的自我審查背后實際折射出的是當事者對政治正確的恐懼。
今天的美國社會早已沒有了上世紀90年代初的那份自信和樂觀。左翼運動的弊端逐漸顯現,人們對政治正確日益感到厭倦。于是,反對政治正確的保守主義出現了。特朗普喊出“讓美國再次偉大”的口號,但保守主義會是美國的未來嗎?
向左?向右?
左派強調平等,但是在右翼保守主義者看來,左派只是以平等的名義制造新的不平等,以真理的名義拒絕真理罷了。而且更重要的是,保守主義者認為,平等所帶來的多元文化正在蠶食傳統價值觀,讓整個社會陷入虛無。
作為一種思想流派的保守主義較早就在美國出現了。20世紀50年代,列奧·施特勞斯出版了《自然權利與歷史》一書。他在書中批評現代社會對所有價值觀的一視同仁是有害的,因為這會讓人不明是非,不辨善惡。他認為,對平等的過分強調,是現代人在思想觀念上誤入的歧途。而在傳統社會,是非善惡的標準曾經非常清晰明確。所以施特勞斯主張,為了診治虛無主義的“現代病”,人們應當回到傳統中去尋找遺失的價值觀。
美國是一個有著濃厚基督教文化的國家。雖然憲法第一修正案中規定不設立國教,但是在公共生活的方方面面仍然隨處可見基督教的影子。《獨立宣言》把人人生而平等的理念追溯到造物主;總統在就職典禮上,手按圣經進行宣誓是延續了200多年的不成文規矩;美元上至今仍然印著“我們信仰上帝”的字樣。因此對于美國來說,回歸傳統價值觀在很大程度上就意味著回歸基督教傳統。
“9·11”事件之后,薩繆爾·亨廷頓出版了《我們是誰:美國國家特性面臨的挑戰》一書。他警告說,大量擁入的墨西哥移民已經威脅到了美國人的身份認同,讓美國面臨著拉美化的危機。在他看來,美國只有回歸盎格魯-新教傳統,才能避免分化和衰落的危險。
如果說政治正確導致被強迫的“自由”,那么保守主義帶來的則是被強迫的“不自由”—比前者更加赤裸裸,不加掩飾。
2016年特朗普成功當選總統后,美國政治開始了真正的保守主義轉向。政治素人出身的特朗普完全不顧政治正確的禁忌,從上臺伊始就力推在美墨邊境修墻以阻止墨西哥非法移民,還簽署了一項行政命令試圖廢除象征政教分離原則的“約翰遜修正案”,并且公開表態反對墮胎。特朗普的這一系列操作讓人不得不懷疑他是亨廷頓的擁躉。
真的會如保守主義所想象的那樣,僅僅回歸傳統就萬事大吉了嗎?保守主義者對于傳統的理解有多少是出于刻意的美化?很難說得清楚。但如果傳統價值觀真的像田園牧歌一樣美好,那么人類當初為什么還要走向現代文明?
保守主義者忽視的一個基本事實是:世界本來就是多元的。人與人之間必然存在著利益、種族、性別、天賦等各方面的差異。尤其是像在美國這樣的移民國家中,多元主義已經構成了社會文化的底色。保守主義者無視多元主義的事實而選擇獨尊一術,就勢必會造成政治上的壓迫。如果說政治正確導致被強迫的“自由”,那么保守主義帶來的則是被強迫的“不自由”—比前者更加赤裸裸,不加掩飾。而且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特朗普在上臺后并沒能使美國團結起來,相反,美國政治這幾年正在愈益趨向兩極化,社會的分裂也不斷加劇。
今天的美國像是被卡在門縫中間,進不得,退不得,左右為難。在政治正確和保守主義之外,是否還存在其他選擇?哲學家們沒有答案,政治家們也沒有答案。
其實這并不只是美國自己的問題,而是現代性本身的難題。自由與平等也不只是美國的夢想,而是所有現代國家共同的追求。所以,在自由平等的道路上進退維谷的并不只有美國。無論過去還是現在,同樣的戲碼也在其他國家輪番上演。
就人類歷史來看,從傳統走向現代是一場脫胎換骨的轉變,就好像生物從海洋進化到陸地,其間必然夾雜著曲折與反復。僅僅認識到自由與平等值得追求,人類才只是將一只腳邁過了現代性的門檻,而另一只腳卻還停留在原地。真正跨進現代性的大門,需要以更高的智慧來破解現代性的難題。
無論如何,歷史還遠未終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