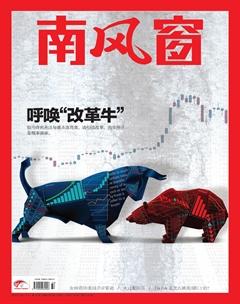“帶不走”的扶貧干部
劉郝

自2016年7月廣州市對口幫扶畢節市、黔南州以來,畢黔兩地變化日新月異—一批批扶貧干部前往大山, 一撥撥粵師粵醫組團式幫扶,一家家粵企赴黔投資生產。
廣州扎實的“造血式”扶貧不僅帶來了商機、崗位與學位,還給了貴州大山里的人們敢于做“追夢人”的底氣。4年以來,在貴州大山里,一批批廣州扶貧干部扶志與扶智并舉,民生與產業并重,他們所做的,是為當地打造一批批“帶不走的”教育力量、醫療隊伍和產業集團。
2020年,扶貧攻堅戰進入決勝階段。廣州這群“筑夢人”,為東西部扶貧協作貢獻了廣州智慧,展現了廣州擔當。
教育扶貧:扶貧要扶“志”
廣州教師詹雯本該在一年前結束掛職,從貴州畢節回到廣州天河。但是,自2018年作為一名掛職教師來到貴州畢節納雍縣后,她一再主動推延歸期。
2017年10月,詹雯作為天河教育專家團一員來貴州畢節納雍縣進行短期培訓后,主動提出支教申請,經過廣州市選拔,在2018年5月,詹雯作為一名掛職教師來到納雍縣。現在她成為納雍天河實驗學校首任校長,也是孩子口中的“校長媽媽”。
自2016年7月以來,廣州先后派出241人次教師赴畢節掛職。如何促進當地教育的長久可持續發展,成為教育扶貧干部面對的一道難題。
“這些大山里的孩子,那些每一天都在改變的舉動,那些一點點在眼里綻放的光芒,讓我現在舍不得離開。”詹雯這樣告訴南風窗記者。納雍天河實驗學校現有1260名學生,其中留守兒童約460人。學校的建成解決了約2393個易地搬遷貧困家庭適齡兒童的入學問題。
2020年6月1日是納雍天河實驗學校首次舉辦開學典禮的日子。那一天,校園里建起了一個充氣大拱門,還鋪上了紅地毯。詹雯帶領老師們穿上卡通服裝,對每個入校的孩子說:“開學了,歡迎你!”
就在開學前,孩子們聽聞新校園已建好許久,趁著教師們家訪的時候,提出想到學校看看。詹雯帶著十幾名孩子提前探校。
當這些大山里的孩子們來到學校的綠茵足球場邊時,愣了愣,脫下鞋子,擺在了一旁的塑膠跑道上。他們怕自己的鞋弄臟草場。這一細節讓詹雯久不能忘。“孩子們,穿上鞋在草地上跑!這個校園是你們的!”在校長的鼓勵下,孩子們才穿上鞋,在草地上邊跑邊蹦起來。
在詹雯看來,只有先讓孩子們愛上學校,把學校當成自己的家,才能讓他們愛上學習,并對生活抱有向往與希望。
開學的時候,詹雯給孩子們寫了一封信并送去巧克力。“我在信中告訴孩子們新學期應該如何熱愛學校,巧克力則寓意著甜甜的生活就要開始了。”
接下來的日子里,第一次穿上嶄新的校服、第一次走上講臺演講、第一次當志愿者……這一千多名孩子開始擁有了數不清的“第一次”。
“我來學校后學會彈鋼琴了。”五年級的留守兒童陸江婷,和爺爺奶奶生活在一起,“我的爺爺腳受傷,很痛,走路很慢”。來到這所學校后的變化,她的好朋友曾開玩笑說,“以前她不愛和人說話,但現在膽子越來越大了”。
當這些大山里的孩子們來到學校的綠茵足球場邊時,愣了愣,脫下鞋子,擺在了一旁的塑膠跑道上。他們怕自己的鞋弄臟草場。這一細節讓詹雯久不能忘。
占地31畝、建筑面積超過8000平方米的納雍天河實驗學校,校門口專門為家長們開辟的休憩平臺,每棟樓樓梯口鏡子上貼著“微笑面對每一天”的標語,教學樓中間有不懼風雨的露天書吧……處處彰顯著廣州扶貧干部的溫度與用心。
“這些學生都是易地扶貧搬遷過來的,每個學生的背后都有個故事。”該校一年級語文教師何靜告訴記者,這些學生的父母多是在外打工,更需要關愛。因此,老師們會更注重站在孩子的角度考慮問題。“現在比較重視與孩子的交流溝通與反饋,然后及時調整自己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方法。”
“錢會用完,物資也會消耗殆盡,最關鍵的還是內生動力,以及孩子們有沒有掌握面對社會的技能和品質。”詹雯告訴南風窗記者,扶貧關鍵在于扶“志”,要讓孩子對自己有自信、對人生有規劃,“‘志智雙扶才是阻斷貧困的根本途徑”。
“你讓他們的生命發生了改變,你讓他們眼里有光了,因為這是易地扶貧搬遷學校,身上的責任和使命是不一樣的。”詹雯向記者介紹,教育是阻斷代際貧困的重要手段,一個孩子只要成才,就能改變一個家庭。
從“打造一批帶不走的教師隊伍”邁向“打造一批帶不走的優質學校”,促進當地教育長久可持續發展,這是廣州扶貧干部在不斷努力解決的問題。
學生史香玲在給詹雯的回信中寫道:“今天中午,陽光明媚,陽光照在我們的身上,就像您對我們的心意,讓我們非常快樂。感謝有您讓我們開心一生。”同時,信上還畫上一個大大的紅色愛心。
醫療扶貧:把技術留下來
這個春節,為了幫助貴州畢節抗擊疫情,醫生黃迪狠心“拋下”了家人。大年初一,在得知“自己的醫院”被納入貴州省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定點醫院后,她便從廣州趕到了畢節市第三人民醫院,一直堅守至今。
黃迪是廣州市第一人民醫院的醫生。2019年,響應東西扶貧協作的號召,她來到廣州對口幫扶的畢節開展醫療支援。她告訴南風窗記者,相比廣州,大山里的病人更需要自己。
“沒有人,沒有團隊。”去年9月,廣州市第一人民醫院乳腺外科副主任醫師黃迪,剛剛來到畢節市第三人民醫院進行對口幫扶時就發現,健康扶貧比當時的想象要更難。在廣州的大醫院里,博士、碩士可以“一抓一大把”,但是在這里,只有寥寥可數的本科學歷的主治醫師,而且一個科里基本上只有一個主治醫生。
“小病靠扛,大病看天”是很多貧困地區的人們應對疾病的無奈做法。如果貧困地區醫療水平不提升,無力走出大山的病人,被迫把小病拖成大病,甚至因治病而返貧。廣州自從對口幫扶畢節以來,推出組團式幫扶新舉措,幫助畢節的醫療力量打造一支留得住、能戰斗、帶不走的人才隊伍。
“在廣州,技術的提升節奏非常快,國際上出現的一個新技術,我們在一個禮拜之內就能掌握。但是,在畢節,醫師們得不到好的培訓,所以技術比較落后。”黃迪告訴南風窗記者。
“我們要為畢節留下帶不走的醫療團隊和醫療技術。”黃迪這樣說。組建一支帶不走的醫療團隊,留下帶不走的醫療技術,整體提升畢節當地醫療力量,這是遠比設備和資金更為急迫的問題。為此,廣州市下定決心,要在三年之內,投入4960萬元,為畢節培養300名醫療規培生。
“在其他發達城市,可能最多拿出一兩個名額,因為不僅要占用廣州本地的規培生的名額,而且廣州也要提供醫療教學資源和培訓的補貼。”黃迪向記者介紹,這一對口扶貧力度,可能在國內都是絕無僅有的做法。同時,每個規培生,都要在廣州的幾所定點醫院中,接受規范的駐院醫師培訓,而且他們也和畢節簽訂協定,學成之后,必須要回到畢節工作。
黃迪記得,曾經有一名規培生來到廣州后,因為工作壓力太大而哭了。在廣州,一個月的手術量,就是在畢節當地三年的工作量。但在黃迪看來,醫生這個職業和其他行業不同,必須在實踐中手把手地教才能得到成長,因此,要讓這些規培生在臨床工作中反復操練。
畢節三醫的李季從去年7月開始來到廣州,在廣醫一院眼科接受培訓。他說,畢節的眼科醫生數量匱乏,當地人護眼愛眼的意識淡薄。他在廣州有高水平的老師帶教,實習的機會也很多,學成后也要回到畢節,為家鄉人民服務。“我的帶教老師都是比較專業的,他們除了臨床工作以外,教學方面也很優秀,可以由淺到深地給我們進行講解,平時上課除了給我們講解先進的知識,也很注重幫我們牢固基礎。”
黃迪記得,曾經有一名規培生來到廣州后,因為工作壓力太大而哭了。在廣州,一個月的手術量,就是在畢節當地三年的工作量。
因為缺乏資源,畢節三醫成立7年以來,至今還沒有一個具有資質的產房。黃迪最近忙著幫助畢節三醫建立一套完整的婦產科規章制度。“畢節三醫之前沒有婦產科,我們最近給他們做的事情就是把三醫的母嬰資質、婦產科的制度建立起來,接下來還要幫他們籌建一個產房。”黃迪向南風窗記者介紹。
實施對口幫扶住院醫師規范化培訓,這是廣州健康扶貧的一種新方式,也是廣州扶貧干部在由過去“輸血式”的幫扶,拓展為增強自我發展能力的“造血式”幫扶的新舉措。
產業扶貧:尊重當地優勢
鄉村振興、異地搬遷、產業扶貧與就業扶貧,這些舉措往往要涉及當地自然環境和人居環境的變動。如何在扶貧中保持當地原有特色,尊重當地的環境優勢,這成為廣州扶貧干部不斷思考的問題。
“廣州的幫扶團隊將會充分利用村子的自然天賦,與鄉村振興有效銜接。”花都派駐貴州對口幫扶干部、織金縣府辦副主任湯銘堅這樣介紹說。
按照當地人的說法,畢節市織金縣大平鄉群建村以往他們只有兩條路走,一條是坐船到對面的黔西縣集鎮購買生活用品,另一條是走陡峭的山路,到縣上最近一個集市,年輕人也要走2個小時。2017年,在廣州花都扶貧工作隊的協調下,當地開山打通第一條道路。
路通了,環境好了,這個坐落在風景秀麗的東風湖畔的群建村人氣急升。在路口的12家民宿和1家農家樂,是去年利用東西部協作資金150萬元建起的,目前農家樂已經營業,12家民宿預計今年暑假可以正式開門迎客。
湯銘堅的思路是,接下來發展鄉村旅游,要將廣州及花都的一些旅游企業和旅游團隊牽引過來,同時引導村民做好人居環境整治,力爭把群建村打造成織金縣最美的網紅打卡點。
而在畢節市赫章縣鐵匠鄉,四處青山環繞、生機盎然。尊重當地生態環境,利用當地生態優勢,400多個花卉大棚遍布廣州幫扶赫章花卉育種育苗基地。在這里,北海道薰衣草、芝櫻、安娜貝拉繡球花等種苗沐浴著充足的日光,生機勃勃。一個向著高附加值延伸的“芳香產業”正在形成。
自2016年7月新一輪東西部扶貧協作工作開啟以來,廣州市對口幫扶畢節市、黔南州,緊抓產業扶貧根本。截至目前,共有227家廣東企業先后到畢節、黔南兩地投資興業,實際投資額117.88億元,帶動12.78萬貧困人口增收。
產業興旺,是解決農村諸多問題的前提。而“芳香產業”在畢節的興起,就是廣州在貴州開展產業扶貧的一個縮影。

今年,在廣州市協作辦消費扶貧專班聯動各方資源的力推下,來自畢節市納雍縣高山上的滾山雞爆紅,一舉打響“黔鳳入粵”的品牌。
在納雍的深山中,放養的土雞成群結隊,因為這樣的自然環境和養殖方式,納雍土雞肉質緊實,香味濃郁。但深山養育了納雍土雞,也困住了納雍土雞。
“當時是88元一只雞,但是后面還有一個數字,郵費40。”廣州市協作辦綜合調研處處長張世學告訴南風窗記者,破解這個“貴”,就必須要用量來解決,土雞要批量地出山。“這個量一大,它的物流成本就降低,解決這個,它才能真正參與市場競爭。”
貴州大山里的一塊石頭,也被充分利用起來。經過提取、研磨、加熱等工序,一塊石頭最終成為日常中使用的塑料袋與包裝紙箱。不同的是,相較于傳統塑料袋,這類石塑包裝袋的生產成本更低,且三個月后開始進入自然降解狀態。
在納雍的深山中,放養的土雞成群結隊,因為這樣的自然環境和養殖方式,納雍土雞肉質緊實,香味濃郁。但深山養育了納雍土雞,也困住了納雍土雞。
2018年,來自廣州番禺的廣州石頭造環保科技公司,將生產環節西遷至貴州都勻經濟開發區,成立石頭造產業基地。這堪稱黔南州自動化程度最高的企業之一,目前共吸納就業300多人,多數為初中學歷,其中9戶為貧困戶。
“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產業扶貧,關鍵是在尊重貧困地區特色和優勢的基礎上,激活當地人們的內生發展動力。產業興旺,才能讓鄉村留住“帶不走的”年輕人,集聚起各種“帶不走的”發展要素,最終實現鄉村振興和徹底脫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