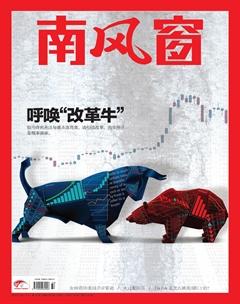中國股市還需要“改革牛”
譚保羅

2015年的“牛市”,上證指數沖向了5200點。而現在的“牛市”,還遠遠沒有突破3500點。顯然,兩次“牛市”都談不上真正的“牛”,前者早已被定論為“杠桿牛”,而后者還有待觀察。
這次的股市上漲,至少有三個背景:首先是房地產調控不斷走向深化,資金進入房地產受阻;其次,中美貿易博弈依然充滿不確定性,資本的跨境流出受到嚴格監管;此外,社會融資規模在上半年的急速攀升也不容忽略,而它和股市變動一直都有密切關系。
但股市上漲總歸會帶來一些“利好”。它會讓部分上市公司在疫情的沖擊之下,獲得新的股權融資,有利于實體經濟的自我調整和修復。更重要的是,也會給資本市場的制度建設留出一定的空間。
當然,在股市躁動的時點,中小投資者更需理性投資,而不是盲目相信自己會是“概率贏家”。
一直都是錢的問題
“牛市”是貨幣現象嗎?這是一個恒久流傳的股市之問。觀察一只超級明星股,便可以窺豹一斑。
7月16日,廣受矚目的中芯國際正式登陸科創板,發行價為27.46元/股,開盤競價后,竟然上漲了246%。到收盤后,仍報82.92元/股,上漲了202.0%,而市值也達到了6000億之巨。
在中美“芯片博弈”的時點,作為中國大陸最大的芯片制造商,中芯國際在上市過程中得到了諸多“眷顧”。同時,其超500億元的募資規模也創造了A股近10年的紀錄。上市之后,它自然成為科創板“一哥”,萬千寵愛于一身。一家證券公司的研報甚至在說,中芯國際比貴州茅臺還要“珍貴”。
由于中芯國際采用了“A+H”的上市模式,所以也在港股上市,但在港股,它的運氣卻沒那么好。當天,中芯國際的港股大跌20%以上。看好中芯國際的分析師分析說,H股的估值壓力很大,所以這個股價走勢并不意外。
不可否認,中芯國際的確在中美貿易戰中扮演著極為重要的符號角色,但從A股和H股的不同表現來看,外界也很容易發現,A股的高估值背后,的確有一定的貨幣因素。
香港為資本自由港,境內外資本流動的管制較少,香港本土資本、從內地南下資本或者從歐美進入香港的資本,它們投資H股和美股的難度并沒有太大區別—最大的區別是時差。但A股的投資者就完全不一樣,他們的可選項并不多,再加上“芯片自主”概念的加持,在A股上漲200%是可以理解的。
流動性的充裕必然會影響到股市,這在任何國家都一樣。道瓊斯指數從2月份的2.9萬點跌到了3月下旬的1.9萬點,但現在又漲回了2.7萬點。期間,美聯儲推出新一輪QE,為市場釋放了大量的流動性同樣功不可沒。
在疫情暴發后,即2020年的上半年,中國的銀行系統也放松了流動性的閘門,各種針對實體企業的“定向寬松”陸續出臺,向市場投放了大量的資金。統計數據顯示,2020年上半年,我國社會融資規模增量累計為20.83萬億元,比上年同期多6.22萬億元,這個增幅不可謂不高。
社會融資規模是指實體經濟(境內非金融企業和住戶)從金融體系獲得的資金。在分析師看來,它是一個偏正向的指標,既反映了金融系統對實體經濟的融資欲望,也反映了實體經濟對資金的需要,背后是企業對擴大再生產的信心。
但A股的投資者就完全不一樣,他們的可選項并不多,再加上“芯片自主”概念的加持,在A股上漲200%是可以理解的。
2020年上半年,中國金融系統的積極行動的確挽救了一大批面臨資金流斷裂風險的企業,對穩定經濟、穩定就業起到了關鍵作用。但客觀地說,社會融資規模和股市的上漲即使沒有因果關系,那么也一定有一些相關性。而且,在實體經濟尚未完全復蘇的時候,資金進入實體經濟的過程中,也難免出現某種“分流”,這是資金的逐利本性決定的。
此外,房地產的調控一直在持續,而且諸如地產熱門城市深圳、南京等,還在近期推出了專門針對假離婚的新政。比如,深圳限購追溯3年內離婚記錄,而南京為2年。房地產熱門城市的調控加碼,顯然會把一部分原本要進入樓市的資金擠出,而股市無疑是一個優先級的可選項。
股價的上漲都是由資金推動的,“牛市”也必然是一個“資金市”,但“壞的牛市”源于短期炒作資金的助推,它是“杠桿牛”。而“好的牛市”則源于更多長期資金的買入和持有,即“大錢”進入,它是“健康牛”和“改革牛”。
上證指數從6月底突然突破3000點,這到底是“杠桿牛”,還是“健康牛”“改革牛”,這是留給投資者的問題,也將最終由他們承擔或受惠。但回顧近年的A股歷史,一些改革的確在不斷落實,比如退市制度。
A股有了好開始
7月21日,A股著名的“妖股”樂視網被終止上市交易,正式摘牌。樂視網最終的股價收報于0.18元,總市值7.18億元,而樂視網在最高峰時,其市值是1700億元。換句話說,這家公司的市值蒸發99%,股民損失到“窒息”。
兩年來,A股的退市制度開始顯現出威力。2019年,A股通過多種渠道實現退市18家,其中,強制退市9家、主動退市1家,以重組出清資產方式退市8家。全年的退市家數創近年之最。
退市制度的落實,在中國股市有著非凡的意義。曾任中國證監會主席的肖鋼曾撰文評價過退市制度,并且用語犀利,他認為,長期以來,我國的資本市場監管者對退市制度的執行“失之過寬”,導致上市公司能夠輕而易舉地避開暫停上市和終止上市的標準。一些明顯符合退市標準的股票,最終也未被強制退出,而是繼續交易,甚至還被不斷炒高。
顯然,退市是對劣勢上市公司的懲罰,這些被強制退市的公司多半有著兩大原因,一是嚴重的財務造假,讓股民損失慘重,因此被強制退市;二是經營不善,連續虧損,達到了退市標準。但除了懲罰意義之外,退市落實更重要的意義在于風險教育,它會逐漸顛覆中小投資者對股市的理解。
正如肖鋼指出的,監管部門對退市制度執行有些寬松,但原因是什么,他卻沒有過多評論。在一些分析看來,嚴格執行退市會“傷害”兩部分人的利益。一部分是上市公司股東的利益,這很容易理解,而另一部分則是炒作這些公司的中小投資者的利益。
一些中小投資者之所以更愿意炒作ST公司,很大程度在于相信退市制度的形同虛設,在股價極低,有可能退市的時候買入,但ST公司最后其實并無退市之憂,所以最終又會被炒起來,股價上去之后,將獲益不菲。因此,如果監管嚴格執行退市制度,那么這部分炒作ST的中小投資者也會“受傷”。
在過去,甚至有一些人拋出嚴格執行退市制度將“傷害股民”的觀點。實際上,這是一種本末倒置。首先,背景深厚的炒家和大股東才是ST炒作的最大贏家,他們是在“吃肉”,中小投資者不過是“喝湯”。更重要的是,退市制度形同虛設摧毀了股市健康的“價值基礎”。
因為一些中小投資者會認為,ST公司不退市,是因為有“制度兜底”,監管會顧忌中小投資者的利益,所以不會讓企業退市。換句話說,不嚴格執行退市制度導致了A股從來都沒有真正的風險教育,對中小投資者炒作垃圾股票起到了逆向激勵,同時也鼓勵了“金融大鱷”在垃圾股票伏擊中小投資者。
按照不完全統計,A股開市近30年以來,退市的上市公司大約為 110 家。這一退市率在全球屬于極低水平,橫向對比美國納斯達克,按照最近10年的統計,大約每年有超過300家公司退市。甚至經常有同一時段,退市公司數量超過IPO公司數量的情況。
總之,退市的嚴格執行至少有著兩重價值:一是懲罰劣質公司,重建了對大股東的正向激勵;二是對中小投資者進行了最好的風險教育,讓他們認識到劣質公司的股票根本就沒有“制度兜底”。在這兩點的基礎上,A股的殼資源將急速貶值,這是資本市場制度構建的良好開始。
不嚴格執行退市制度導致了A股從來都沒有真正的風險教育,對中小投資者炒作垃圾股票起到了逆向激勵,同時也鼓勵了“金融大鱷”在垃圾股票伏擊中小投資者。
亟需“改革牛”
近期,一些被認為是“好公司”的企業紛紛登錄A股或宣布會登陸A股。比如螞蟻集團(曾經的螞蟻金服)就宣布將采用“A+H”模式上市,消息一出,“螞蟻概念股”大漲。這從側面說明,螞蟻金團的確不愧為傳說中的“獨角獸老大”,被資本追捧的程度無人能出其右。
但換個角度看,熱門科技公司不再選擇在美上市,而選擇A股,一定程度也是“外力”作用的結果,中美貿易博弈的不確定性依然存在,再疊加瑞幸造假事件的影響,中概股在美國的估值將可能面臨某種“折扣”。當然,更重要的是由于對跨境資本流動的嚴管,以及內部流動性充裕的原因,A股更能帶來超級高估值。
此外,這些科技公司的外資股東也需要退出,而且希望在資本自由港退出,所以在看中A股高估值的優勢之外,也會選擇同時在H股上市。香港是資本自由港,而且實行聯系匯率制度,這意味著在港股實現投資退出拿到港幣,也等于拿到了美元。
因此,對科技公司紛紛選擇A股應該理性看待,并不能盲目樂觀地認為,“回歸A股”完全是因為A股的制度改革取得巨大成就的原因。實際上,改革依然需要不斷推進,而且阻力不小。
比如,新修改并于2020年3月1日實施的《證券法》確立了“代表人訴訟”。根據《證券法》,投資者提起虛假陳述等證券民事賠償訴訟時,訴訟標的是同一種類,且當事人一方人數眾多的,可以依法推選代表人進行訴訟。這被業界認為是美國集體訴訟制度的“中國版”。不過,美國集體訴訟制度的精髓并非推選代表人進行訴訟這一“形式”,而是訴訟利益歸屬于誰這一“實質”。
美國集體訴訟的立法思想是,為了鼓勵積極訴訟,震懾資本市場的違法者,法律首先規定了違法者必須進行巨額的賠償。其次,是將訴訟利益這一“蛋糕”切出一大塊給小股東和訴訟律師。于是,很多小股東和律師如同禿鷲一般,專門尋找資本市場的違法行為進行訴訟,某種意義上講,他們是比美國證監會還要敏銳和積極的“監管者”。

但在A股,情況有點不一樣。實際上,在我國的《公司法》中早已規定了股東代表訴訟,早已具備了美國集體訴訟的“形式”,但問題在于,股東代表訴訟的利益直接歸于公司,而公司主要是大股東控制的。所以這就造成一個邏輯怪圈—大股東違法損害公司利益,小股東花費巨額成本進行訴訟,最后的訴訟收益卻重新歸于大股東。這種情況下,誰還愿意訴訟?
一些專家指出,《證券法》的修改是一個重要進步,但很多配套的制度還需要完善。以監管執法為例,除了要證券監管部門嚴格執法之外,還必須調動民間力量來“監督”資本市場的違法行為。將“監管責任”下放市場主體,降低中小投資者、機構投資者等民間力量維護自身利益的制度性成本,是所有成熟資本市場最重要的經驗。
將“監管責任”下放市場主體,降低中小投資者、機構投資者等民間力量維護自身利益的制度性成本,是所有成熟資本市場最重要的經驗。
2019年6月,科創板正式開板,目前上市公司超過100家,總市值超1.5萬億。科創板實行注冊制,改變了以前的“核準上市”制度,同時科創板還實行相對嚴格和有門檻的投資者準入制度,一定程度改變了A股其他版塊“散戶市”的特征,這些改變都是不容低估的制度進步。
但改革依然不能停滯。作為直接融資市場,股市本質上是投資者和融資者的自由契約,過去,融資者時常利用股市的制度漏洞侵害投資者的利益,實現財富的轉移效應。但另一方面,由于某些特殊和客觀的原因,監管卻時常失之過寬,難以維護投資者的利益。于是,投資者的信心經常遭受打擊。
因此,要汲取這種過去的教訓,就必須為投資者自我維權提供制度保證,降低其維權成本,這應該是未來改革最大的出發點。讓市場回歸市場,“改革牛”才是“健康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