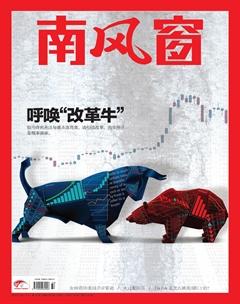一夜間成為“城里人”的農民們
何國勝

3年來,韓彬沒在縣城里的樓房住過一天。
那套92平的房子到手只花了1萬多元,這是易地扶貧搬遷帶來的巨大“優惠”,代價則是拆掉農村的老宅,宅基地復耕。
這本是白紙黑字寫明的事,但韓彬們一直對此無法釋懷。
“做了個錯事”
韓彬老宅被拆的那天,一些畫面依然很清晰。
兩根從正房拆下來的巨大梁柱交叉躺在地上,周圍是一片混亂的碎瓦亂石。
他和妻子帶著兩個不滿7歲的孩子搬運滿地的碎磚塊。藍色大門放在一邊,院子中間的牡丹花開得正艷。
西邊一堵殘墻上還貼著“幸福美滿”4個字,那曾是他和妻子的婚房。
韓彬是甘肅省臨夏縣韓集鎮某村的建檔立卡戶,今年26歲。2017年他們配合了該地的易地扶貧搬遷政策,這意味著放棄農村老宅,進城生活,住了幾代人的老宅將會被平整成耕地。
3年前,村干部告知他,政府有一個面向貧困戶的易地搬遷項目,他們只需交1萬元錢,就可以在縣城擁有一套住房。考慮到孩子以后的教育和出于對城市生活的好奇,他們家欣然接受了這套房子。
“當時沒有人告訴我們要了這套房子后農村的老家會被拆除”,韓彬告訴南風窗,這是辦完手續后才被告知的,此時的說法也是無法確定拆不拆房。
韓彬沒當回事,總以為住了幾代人的房子怎么可能說拆就拆。等到房子被拆時,他忽然意識到“這算干了個壞事”。
同樣想法的還有同村的宋強,他家是該村另一建檔立卡戶。跟韓彬不一樣的是,他家在縣城的樓房是2015年他自己貸款買的商品房。
當時兒子要結婚,女方要求必須在縣城有房,為了兒子,宋強想盡辦法買了那套房。但還沒等到交房,兒子就離婚了。
“2016年2月份的時候,村干部把我叫去說有件好事,說像我們這樣經濟困難的家庭,國家免費在縣城給一套房子。”宋強說,當時他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他把自己買的房子變更成了易地扶貧搬遷項目的房屋。“當時他們沒有提任何要拆除老家房子的事,到了2017年就有人開始傳會拆房子的話。”
之后村里開會的時候,村干部依然告訴他們目前無法確定房子到底會不會被拆。“當時我們還有人問他們,拆不拆給我們一個實話,真要拆的話我們把房子或錢退回去,沒有人希望自己老家被拆。”
2020年5月,宋強的房子被拆除,他背著家人偷偷哭了一場,但對整個拆房過程都異常配合。
吳平當初也是考慮到兒子以后的婚事而接受了縣城的住房。他家距縣城有20多公里,起初并沒打算要這套房子,但母親說:“你有兩個兒子,以后還要面臨分家和結婚的事,你沒個房子怎么辦?”
吳平接受了這套住房,但房屋被拆后母親卻后悔不已:“要是早知道老家會被拆,我寧愿被砸死也不愿意要那套房子。”
吳平的母親今年84歲,在老房子里住了大半輩子。“她看著難受,不愿意呆在家里。”吳平說,拆房子那幾天,母親總是躲到離家比較遠的地方,很晚了才回來。
“當時沒有人告訴我們要了這套房子后農村的老家會被拆除”,韓彬告訴南風窗,這是辦完手續后才被告知的,此時的說法也是無法確定拆不拆房。
其實,老人家最難受的不是拆房那幾天,而是接到通知等待拆房的那段日子。“自從來了通知,我每天都很焦急,老怕他們第二天就來。到了后來,我就盼著他們早點來,早點把這房子拆了,讓我少受點煎熬。”

“咋可能讓你白白得一套房”
項目實施時,拆不拆房子說法模糊,這是搬遷的貧困戶們的心結。
此外,還有不少人反映,剛開始政府承諾會給搬遷戶留2~3間生產用房,最后卻全部拆除,讓農戶們覺得自己受了欺騙。
宋強的大哥告訴南風窗,他從一開始就看穿了這件事。“免費給你房子,那肯定有別的打算,咋可能讓你白白得一套房?我當時就覺得肯定會拆老家的房子,所以我沒要。”
他說,當初他兄弟和其他人決定要縣城的房子時,是簽了宅基地復耕協議的,協議上面寫明了參與易地扶貧搬遷項目后,在老家的宅基地要復耕。
然而韓彬稱自己基本屬于文盲,根本不懂什么是復耕協議。而包括宋強和吳平在內的更多人其實也看到了復耕協議,但在從眾心理和僥幸心理的作用下簽了名。
臨夏縣韓集鎮分管易地扶貧搬遷工作的副鎮長韓國強告訴南風窗, 2017年開始,在項目實施過程中,一直都是跟群眾面對面地講明了“拆舊復耕”的情況。通過大量的談話和解釋,參與該項目的貧困戶都簽署了“拆舊復耕”協議,不存在群眾所反映的模糊回答和不兌現承諾問題。
但他也表示,不排除有的村干部在工作中存在不細致和不到位的情況。
關于先期承諾留2~3間生產用房的說法,韓國強予以否認。“按照‘拆舊復耕協議和國家相關政策,留下2~3間生產用房既不符合規定,又無法達標。”
韓國強坦言,在整個“拆舊”過程中,他們必須做到“全拆”,但也堅決沒有強拆。“十三五”以來,韓集鎮共搬遷貧困戶98戶,目前已拆除60戶,另外38戶抵觸情緒較重,目前仍在做思想工作。
宋強的情況比較特殊,韓國強說,按照國家扶貧工作規定,貧困戶的債務負擔每月不能超2500元。宋強這樣的通過按揭貸款購房的貧困戶,超出了這個債務負擔紅線,為了減輕他們的負擔,政府將其住房轉為安置房。
房子拆掉后
老家被拆除后,韓彬在同村租了幾間屋子。雖然在縣城有房,但他們不愿意住進去。最大的困難來自母親。
韓彬父親在5年前去世,母親是個聾啞人,精神上也有一些問題,基本處于一種半自理的狀態。如果搬去縣城的話,等韓彬夫婦出去務工,不僅兩個孩子無人照料,韓彬母親也無法自理生活。
因為她根本無法使用樓房里的現代化廚具,帶電的東西也不敢讓她碰。若要去縣城生活,韓彬妻子只能全職在家照顧老人。“這樣的話,我一個人的收入維持不了在縣城的開支。”

城里處處都要錢:一年1000多元的物業費、2000多元的采暖費……甚至他們每天吃的面和饃也要花錢購買,而在農村,都是自給自足。
韓彬在老家還種了幾畝地,現在房子拆掉了,地卻扔不掉。縣城離韓彬老家近十里地,“住在縣城照看莊稼很難,而且等夏收的時候,莊稼都不知道收到哪里去”。
“自從來了通知,我每天都很焦急,老怕他們第二天就來。到了后來,我就盼著他們早點來,早點把這房子拆了,讓我少受點煎熬。”
他曾懇求村委會允許他建兩間彩鋼房便于務農,但村里沒有同意。“我當時還賭氣說,到時候我收了糧食就晾在你們村委會的院子里。”
宋強面臨著同樣的難題。搬進縣城后,一邊是開支增加,一邊是收入減少。
兒子離婚后不久,宋強就中風了,左半身的僵硬,他們家原有的兩個勞動力變成了一個,兒子外出務工所得成了他們最主要的收入來源。
宋強更擔心的事情是在將來。 “我們去了那里,就像是頭上被敲了一錘子,感覺頭暈、悶得不行。現在兒子還沒結婚,將來結婚后住在一起,他們要是嫌我們臟,我們還能去哪?”
宋強說,如果給他們留幾間屋子,他跟妻子住在農村,讓兒子他們住在縣城,這樣就能避免一家人因擠在一個狹小的空間里而產生的矛盾。
跟韓彬一樣,宋強也種了幾畝地,還養了兩頭牛。為了務農和養牛方便,房子被拆后他把牛寄養在兄弟家的牛棚,自己和妻子住在牛棚旁邊一間狹小的守棚屋中。
舍不得的莊稼
搬去縣城后,住所和耕地的兩地分離是扶貧搬遷的農戶們目前面臨的最突出的難題。
這些被遷移的農戶,大多來自離縣城較遠的山村。韓彬和宋強家是離縣城最近的遷移戶,但也有5.3公里,而吳平家距縣城有20公里。

韓彬和宋強回村干活兒,可以坐公交到附近,再走過去,單趟半小時左右。吳平回家則沒有公交車,逢集才有直達的車,其余時候就要繞行,單趟至少需要1個小時,并花費最少7元的交通費。
吳平家在老家搭了帳篷,妻子、母親和小兒子住在帳篷里,負責照料莊稼,吳平和大兒子平日里外出打工。這兩天因為夏收,吳平從外地回來,跟妻子和母親等一起擠在帳篷里。
夏收時節容易出現冰雹等強對流天氣,熟透的小麥會因被打落穗頭而造成減產災害。這種時候待在縣城讓他們無法安心,而吳平母親的不安比他們都強烈。
在兒子還沒回來的時候,84歲的她按捺不住焦慮,自己跑去割了半天小麥,近傍晚的時候遇上雷陣雨,回家時早已淋了個透。
為此,吳平和孫子批評了她一番,但她只回了一句:“莊稼熟了,我能坐得住嗎?”
搬去縣城了為什么還要種地?吳平說:“農民不種地那還叫農民嗎?”
跟吳平同村的小伙何艷兵認為,種地能減少他們在縣城生活的開支。“你在家里種幾畝地,最起碼你不用買面、買油和土豆,平時還可以種點菜。”
何艷兵說,他們家里還種著12畝左右的田,今年光小麥就種了6畝,其他還有油菜、土豆和玉米等。
城里處處都要錢:一年1000多元的物業費、2000多元的采暖費……甚至他們每天吃的面和饃也要花錢購買,而在農村,都是自給自足。
何艷兵平常也在外務工,這兩天因為夏收回了家。自從他們老家拆除后,他和父親外出,妻子在縣城一個餐廳當服務員,母親帶著孫子住在老家搭的帳篷里,偶爾也去他妹妹家住,爺爺住在縣城。
跟他母親不一樣,他爺爺喜歡住在縣城,因為在那里他不用每天喂豬、干農活兒,每天出去遛彎、看看其他人打牌就覺得很舒服。他很適應縣城的生活,雖然以往的炕換成了床,但他不覺得有什么不適。

但何艷兵的母親對無法繼續養豬的事不能釋懷,因為“不養豬后,我們家的收入就減少了”。而不能再養豬,迫使母親更加堅定了要堅持種田的想法。“收入已經減少了,不能再增加開支。”
額外的擔心
當種田有了額外的意義和功能后,何艷兵母親反而多了一份擔心。
她害怕過段時間,不讓他們種田了怎么辦?因為她聽到有人在議論,易地搬遷戶的農田將被收回。
跟同村別的婦女坐到一起時,她總會問大家:“明年還讓不讓種了?讓種的話今年要把地犁了,不讓種的話就不費那個辛苦了。”
沒人能答得上來,大家只說同一句“再不知道(誰知道呢)”。
出于異地務農的不便和對老家的留戀,何艷兵希望政府允許他們在老家建幾間生產用房,既方便務農也好讓他們有進有退,在城市生活不下去時,還可以退守農村。
何艷兵的母親也想有幾間生產用房,她更喜歡生活了幾十年的農村。“如果能有幾間房,我還是愿意住在農村。”她告訴南風窗,雖然政府在縣城給了他們一套房,但因為沒有房產證,她覺得那房子并不是屬于他們的,她擔心有一天突然不讓住了,又該去哪里?
離了根的他們,總有些不安感,以至于有些流言開始在扶貧搬遷群體中傳播開來:搬到此地的貧困戶以后會被遷移到新疆、酒泉等人煙稀少的地方。
何艷兵母親相信有這種可能性,一是因為房子沒有產權,二是她記得當初交房子的時候政府工作人員曾告訴他們,不要把房子裝修得太好,她覺得這是個暗示,暗示他們不會在這住太久。
“搬得出,穩得住”
“搬得出,穩得住。”這是易地扶貧搬遷的關鍵所在。“搬得出”容易實現,而“穩得住”卻是一件難事。
貧困戶進城,必然要面對陌生的環境和更大的生活壓力及額外的開支。此時,促進他們融入新的集體和解決就業問題,就是緊急任務。
之所以有很多像韓彬、吳平一樣的貧困戶在自己的老家被拆除后,仍然以各種方式留在農村,根本原因還在于他們沒有一直在城市生活下去的底氣。
記者在臨夏縣扶貧搬遷安置小區惠民嘉苑了解到,當地政府為了增加小區的集體認同和歸屬感,先后舉辦了文藝晚會、拔河比賽和流動觀影等一系列活動。
2020年7月18日晚,記者來到惠民嘉苑附近,看到惠民嘉苑一期和二期的主干道兩邊全是擺好的地攤,擺賣著各種小物件和生活用品,路上擠滿了人,一幅市井氣和煙火氣十足的畫卷沿著主干道由北向南鋪展下去。
記者隨機詢問了幾個攤主,有兩個恰好是剛搬來的貧困戶,他們告訴南風窗,這個夜市攤是由政府劃定給他們的,每個人都有固定的位置,主要面向搬來此地的貧困戶家庭,是為了增加他們的收入而采取的措施。
此外,韓集鎮副鎮長韓國強告訴南風窗,政府方面目前正在統計宅基地復耕和貧困戶搬遷的資料,針對他們的就業保障問題,已經計劃了分配蔬菜大棚和提供100余輛免費出租車的方案。
韓彬、吳平和何艷兵等也表示確有此事,但他們都不以為然。
核桃、果樹、杏子樹都結了很多果,今年是個豐收季。何艷兵看了看滿樹的果實,隨口說了一句:“老家都沒了,果實結得好有什么用?”
韓彬告訴南風窗,計劃給他們分配的蔬菜大棚在距離縣城37公里的另外一個鄉鎮,他覺得這有些荒唐,距離相差那么遠,平日的種植和維護怎么進行?
吳平一家也覺得不現實。“要是家里沒老人孩子還能考慮,不然你跑那么遠種菜,家里面誰管?”
對于提供免費出租車的措施,何艷兵覺得這跟去幾十公里外種蔬菜大棚一樣不現實。“雙城(縣城所在地)那么小,還沒多少人,哪有人坐出租車?”
臨夏縣縣城所在地雙城原是一個村子,后來因縣址遷移而成了縣城。經過近6年的建設,城區整體形態已基本完備,但整個城區面積不足5平方公里,南北不足2公里,東西2.3公里左右,常住人口不足2萬。城區內沒有環行的公交車,只有兩條開往市區路過城區的公交線路。
韓國強說,雖然目前規劃的蔬菜大棚的確距離較遠,但也有靈活措施:有條件去經營的群眾可以自己獨立經營,沒有條件經營的群眾可以申請托管經營,然后自己領取分紅便可。
韓國強還建議,苦于異地務農的群眾可以將自己在農村的土地流轉,從而收取租金。
另外,關于房子產權問題,韓國強表示貧困戶所住房屋性質為廉租房,貧困戶擁有70%的產權。經過幾年發展后,如果貧困戶經濟能力允許,可以購回剩余30%的產權。但具體的操作細節和時間問題還要等縣上做統一安排。
根據臨夏縣政府網站介紹,臨夏縣是國家六盤山片區集中連片特困縣和“三區三州”政策扶持重點縣之一,全縣共有建檔立卡貧困村116個(省級深度貧困村67個)、建檔立卡人口29760戶13.73萬人、貧困發生率為38.95%。經過幾年的扶貧工作,剩余貧困村19個、貧困人口2699戶8011人。韓彬、宋強、吳平和何艷兵他們,就是這串數字的一部分。
這幾年臨夏縣有2329戶11321人通過易地扶貧搬遷項目離開農村進入城市,這也意味著有2300多戶老宅被拆。
7月19日下午3時許,在何艷兵老家采訪,他帶記者去摘他們自家的杏子。核桃、果樹、杏子樹都結了很多果,今年是個豐收季。
何艷兵看了看滿樹的果實,隨口說了一句:“老家都沒了,果實結得好有什么用?”
(文中受訪的農戶均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