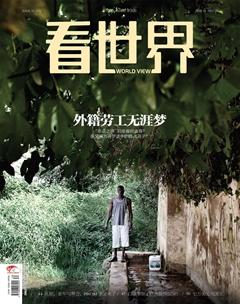印尼移工:英雄還是棄子?
卡莫

經過數十年的發展,印尼的“移工輸出鏈”已經相當成熟,每年都輸出上萬名移工到世界各地
2018年夏天,我到雅加達短居,住在一間名為“巷尾”的餐廳后方。那里實際上是一間歸國移工的庇護所,由Lina和她老公一起經營。“巷尾”餐廳的收入,是為了支持兩人生活以及庇護所的開銷。Lina的老公有時也會出去跑Gojek(摩的)貼補家用。
Lina說,庇護所一年服務超過百位歸國移工,有人被積欠薪資或“資遣費”、有人遇到職災,也有人罹患重大疾病。Lina會四處奔走,為他們向印尼政府爭取權益。
一開始我不太理解,為什么Lina會特別關注歸國移工?后來,我在她的生命史里找到了線索—十多年前Lina高中畢業后,為了撐起家中生計,曾經到中國臺灣當移工。
外匯英雄
因為許多復雜的歷史、地緣與政治因素,東南亞地區在全球產業經濟鏈中,至今大多仍處于“半邊陲”地帶。對這些國家而言,輸出勞動力不只是舒緩了國內就業機會不足、低薪的壓力,更得以藉由移工匯回海外的薪資賺取外匯,成為維系國內經濟的快捷方式。
菲律賓的勞動力輸出經驗,可以說是東南亞國家中的濫觴與翹楚。1960年代,美國出現護士荒,而菲律賓得利于受美國殖民的經驗,開始輸出大量具有語言優勢的護士到美國工作。菲律賓政府在此次經驗中嘗到了甜頭,于是在1974年開始大力推行輸出勞動力的政策,先是往波斯灣國家輸送建筑工和船員,接著將家務工送到中國香港和中國臺灣。
勞動力輸出政策發展數十年后,海外移工對菲律賓經濟來說,已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2003年,時任菲律賓總統阿羅約造訪美國時說:“我不只是一個對8000萬人口負責的國家元首,我還是全球800萬菲律賓海外移工企業的執行長,他們生活、工作在海外,并且每年為我們的國家創造數十億美元的收入。”
在菲律賓媒體的聚光燈下,當地社會逐漸將海外移工視為“英雄”。他們的海外收入不只貢獻于家中,也同時貢獻于國家經濟。無獨有偶,自1970年代末期開始,印尼也嘗試以輸出勞動力解決失業與貧窮問題,并且在1997年的金融風暴后,更加積極地推行此政策。
到了2019年,印尼的海外移工人數突破370萬,而同年度,菲律賓官方統計的海外移工人數為230萬。印尼的海外移工人數已遠超菲律賓,而印尼移工賺進的外匯超過110億美元,約占印尼GDP的1%。
2011年時,印尼總統蘇西洛曾發表談話:“我們在印尼,稱呼移工是‘外匯英雄。他們努力工作,將自己獻給家人。”這個“英雄稱號”有一段時間,還被裝飾在蘇卡諾-卡塔爾機場的大型廣告牌上,用來迎接歸國的印尼移工。
幾十年來,印尼政府有計劃地推動國人成為“外匯英雄”,而年輕時候的Lina,也就是在這樣的歷史脈絡,以及貧窮的現實逼迫下,踏上了她的“英雄之路”。
英雄之路
其實,Lina的故事算不上太特別,畢竟大部分藍領移工出國工作的軌跡都是類似的。他們同樣面臨貧窮、低薪、失業,或是餓不死卻也吃不飽的生活;上有父母,下有嬰孩嗷嗷待哺;家徒四壁,甚至墻上早已出現大量裂縫、搖搖欲墜。對國家來說,送人民出國工作是調節經濟的工具,然而對人民來說,出國工作卻往往是迫于現實、無從選擇下的選擇。
經過數十年的發展,印尼的“移工輸出鏈”已經相當成熟,每年都輸出上萬名移工到世界各地,而目前有最多印尼移工的地方是馬來西亞、沙特阿拉伯、中國臺灣和中國香港。
在那些有大量人口到海外工作的村落,一旦你起心動念要出國工作,并隨口向家人、鄰居一提,沒多久便會有“牛頭”前來敲門,進一步告訴你到海外工作可以賺多少錢、蓋多大的房子、讓小孩上到高中甚至大學。

20世紀60年代,美國出現護士荒,而菲律賓得利于受美國殖民的經驗,開始輸出大量具有語言優勢的護士到美國工作
到了2019年,印尼的海外移工人數突破370萬,已遠超菲律賓。
“牛頭”位處移工輸出鏈的底層,卻是帶動大量移工出國工作的“催化劑”。
“牛頭”位處移工輸出鏈的底層,卻是帶動大量移工出國工作的“催化劑”。他們負責在鄉間找尋有意愿出國工作的人,并透過各種慫恿的話術,讓其下定決心成為“移工候選人”。甚至若對方有心出國,而錢不夠的話,有的牛頭還會提供借貸的服務。
大部分的“牛頭”都和特定中介公司有合作關系,他們將招攬到的“移工候選人”帶到中介公司后,便可以從中介公司得到一筆傭金。而在這之前,“牛頭”也會向“移工候選人”收取一筆500萬印尼盾(約合人民幣2400元)的“報名費”,才會將“移工候選人”帶到中介公司。
我對“牛頭”的角色感到非常疑惑:為什么想出國工作的人,不能直接去中介公司?
“不知道怎么去。”“大家都這樣,我們村子的人都是跟那個牛頭。”“牛頭都開很好的車、住很大的房子,看起來很成功,會不由自主地相信他。”答案不一而足。
后來,已經出國工作三次的Wanto跟我說:“就算你不透過牛頭,自己跑去中介公司,還是會被收那筆‘報名費,因為中介公司里幫你辦件的那個人,就會變成你的‘牛頭。”
雖然500萬印尼盾對一般印尼人來說,已經不是一筆小錢,但跟親友借借也許還夠。不過想出國工作,代價絕對不只是如此。中介公司會依不同的目的地、工種而開出不同的“中介費”價碼,薪資愈高、勞動保障愈充足的地方,價碼自然愈高。
雖然印尼政府早就對“中介費”進行規范,但是殺頭生意都有人做,何況印尼政府從未嚴格取締,以至于“超收”的情況一直都存在。中介公司漫天喊價,移工為了出國工作也只能照單全收。
例如,Wanto申請到中國臺灣的工廠工作,必須先給中介公司4500萬印尼盾(約合人民幣2.2萬元)的現金,這部分完全是“超收”的。而Wanto還必須簽下一紙約1800萬印尼盾(約合人民幣8800元)的貸款,開始工作之后分月攤還,這部分才是印尼政府規定中介公司可收的費用。至于像Lina一樣申請擔任家庭看護工的人,因為薪資較低,所以不必“被超收”,但是仍然得在開始工作后每月償還“貸款”。
猶如棄子
Wanto是沒有那么多錢可以交上中介費的。即便到了今日,印尼基本工資最低的省份僅有170萬印尼盾(約合人民幣825元),基本工資最高的雅加達也只有420萬印尼盾(約合人民幣2040元)。
在Wanto第一次出國工作的10年前,若有能力一下掏出4500萬印尼盾的人,可能也無意成為“移工候選人”。所以,Wanto當時不只跟親戚借了一圈錢,還把家中耕作的田當了,就為了換取一個出國工作的機會。
Wanto的“牛頭”告訴他,繳了錢之后幾個禮拜就能出發,之后工作、還錢、存錢、蓋新房,但Wanto在中介公司的宿舍待了5個月,卻連個面試機會也沒有。Wanto漸漸感到不安,而且在宿舍也很不舒服。他住進去的第一天就發現,房間里有大量“臭蟲”,咬得所有人奇癢無比。后來大伙兒只好撿了紙箱,移到院子里睡覺;至于雨天,只能索性不睡。
在宿舍的日子漫長且無聊,Wanto說雖然有體能訓練跟中文課,但都是“聊備一格”。尤其是中文課,只要在臺灣或香港工作10個月就能回來當中文老師,結果他跟老師學了之后,到臺灣卻發現很多都是錯的。“我覺得這些課程,只是為了讓他們有借口不給我們工作,因為他們都會說我中文還不夠好所以才沒有工作。”
最讓Wanto受不了的,是中介公司規定他們不得外出。如果想吃點別的東西、喝杯咖啡,只能隔著墻請對面餐廳的人送過來,“就好像在坐牢”。有好幾次,Wanto覺得再等下去不是辦法,想干脆放棄回家種田,但中介公司卻說:“你如果要離開,錢不會還你,而且還要罰錢才會把證件、文件還給你。”也許Wanto并不是真在坐牢,但他卻扎扎實實地被“套牢”了。

被馬來西亞驅逐出境的印度尼西亞移工
第六個月,Wanto總算有面試機會,用視訊的方式接受兩間工廠面試。再下個月,中介公司通知Wanto被錄取了,但工作合約上的雇主,卻不是他曾面試過的工廠。“我已經放棄爭論什么了,我只要有工作就好。”
Lina在印尼的那一段過程沒那么坎坷,因為輸入移工的地區對看護工的需求甚高,所以Lina取得工作的成本較小、等待時間較短。但Lina在臺灣待了一年,其中卻有10個月被監禁在收容所內。
Lina簽的是看護工合約,但到臺灣之后卻被“中介”帶到工廠工作,而且薪資遠低于在印尼說好的價格。輸入地的“中介”是整條移工輸出鏈的最后一環,也往往和“牛頭”“母國中介公司”一樣問題叢生。因為移工初來乍到,中介便有許多可以介入、從中獲利的空間。
在工廠工作一個月后,Lina身體不堪負荷、求助中介卻無響應,她毅然決定離開這個工作,成為法外的“黑工”。后來,她在一家餐館找到打工機會,但是工作不過一個月,Lina就因為想跟雇主要回被扣的護照而起了爭執,雇主一氣之下報警舉報了Lina。接下來的10個月,Lina只能待在收容所內,等待被遣返。
雖然Wanto后來順利到臺灣工作,也存了一點錢,但談起那段過往,他神情依然凝重。當他說到一些聽起來很魔幻的片段時(例如像在坐牢),我因為覺得荒謬而笑了出來,Wanto有點無奈地說:“你現在聽覺得好笑,但我那時候真的好痛苦。”
無論是Wanto“受困”在中介公司,還是Lina最終的鎩羽而歸,在他們這些痛苦的經驗中,得利于移工經濟的母國,卻未曾在場。他們都不是,或還未成為國家口中的“外匯英雄”,反倒成了未被眷顧的“棄子”。
聽完他們的故事,我總覺得國家贊揚英雄的同時,也刻意不告訴這些奔向海外的人們—若當不成英雄,后果請自負。
編輯郵箱 jw@nfcmag.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