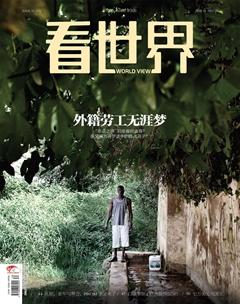白俄羅斯:歐洲最慘國家?
何任遠

白俄羅斯首都明斯克
一個民族國家的天職是什么?當然是維護本國主體民族的語言、文化和民族傳統。然而在相當一部分白俄羅斯人眼中,白俄羅斯政府卻并不熱衷于此。
根據2018年的一項統計,只有13%的白俄羅斯學生在學校接受白俄羅斯語教育,提供白俄羅斯語教育的幼兒園屈指可數,而大學也沒有相關課程。提供白俄羅斯語教育的學校大部分只集中在首都明斯克,而農村教壇多數被俄語老師占據。
自盧卡申科1994年擔任白俄羅斯總統以來,白俄羅斯語在該國的公共教育系統里一直衰落。盧卡申科這位一直執政了26年的強人,本身也不大會講白俄羅斯語。
繼續維持白俄羅斯語言和文化傳統的傳承,成為了該國民間組織的重要活動。白俄羅斯民族主義者更加與國內反對派聯合,在眾多議題上對總統發難。直到烏克蘭危機爆發,白俄羅斯才勉強把“振興本國民族文化”提上議程。
地處歐洲和亞歐大陸邊界,白俄羅斯被視為一個“邊界國家”,存在感相當弱。到底是什么原因讓這個東歐國家好像影子般存在?它能不能最終走出強鄰的陰影?
其歷史離不開立陶宛和波蘭
在白俄羅斯民族主義者的集會游行隊伍中,總能見到白騎士徽章旗幟。紅色的盾牌里,一名騎著白馬的白色鎧甲騎士舉起佩劍,向左邊砍去。實際上,這源自立陶宛大公國的徽章。白俄羅斯民族主義者為何要采用立陶宛大公國的徽章呢?
公元12世紀,歐洲最后一個信仰異教的民族—立陶宛,以強勢姿態在波羅的海沿岸崛起,先后擊潰了往東進犯的條頓騎士團和佩劍騎士團,更加聯合東部的各個斯拉夫部落,擊退了蒙古帝國勢力,大舉占領了今天屬于白俄羅斯和烏克蘭西部的地域。
立陶宛和波蘭的史料,把那些臣服于立陶宛大公國的斯拉夫部落稱為“羅塞尼亞”。羅塞尼亞人講的古斯拉夫語,與當時莫斯科附近的語言有所不同,然而他們也信仰東正教。歷史學家們認為,這些羅塞尼亞人講的古老語言,就是白俄羅斯語的雛形。
1569年,面對莫斯科大公國的崛起,連續挫敗的立陶宛大公國選擇和波蘭王國締結聯盟,組成波蘭-立陶宛聯合王國。立陶宛日益被波蘭天主教同化,部分羅塞尼亞貴族受到波蘭的壓力也改信天主教,卻保留了承襲自拜占庭的東方儀式。因此,羅塞尼亞成為了“東儀天主教”的重要活躍地盤。

白俄羅斯總統盧卡申科
盧卡申科這位一直執政了26年的強人,本身也不大會講白俄羅斯語。
羅塞尼亞的地盤,也成為了波蘭-立陶宛聯合王國抵擋莫斯科大公國軍事壓迫的前沿陣地。在這片毫無自然屏障的土地上,韃靼人、土耳其人、瑞典人和莫斯科大公國的勢力此消彼長。如果說,歐洲民族的現代化進程主要是通過市鎮實現的話,那么白俄羅斯的不幸在于,受阻于連年戰事,與歐洲通商的機會微乎其微,因而長久停留在農村的層面。
白俄羅斯貴族士紳們效忠的是立陶宛,語言和習俗更加傾向于波蘭,外交和法律文獻多使用波蘭語,對母語幾乎毫無感情。也因此,白俄羅斯語成為了鄉間佃戶之間使用的語言,至今不少白俄羅斯官方人士看不上這種農民語言。
進入18世紀,波蘭-立陶宛聯合王國陷于弱勢,步步緊逼的俄羅斯在1794年與普魯士和奧地利聯手把波蘭徹底瓜分。今天白俄羅斯和烏克蘭的這片土地相繼落入沙俄手中,波蘭天主教文化對白俄羅斯士紳的影響終于被掐滅。
然而在沙俄的視野范圍內,白俄羅斯作為一個與俄羅斯不同的民族并不存在。白俄羅斯的東儀天主教教會在1839年被沙俄強制取消,白俄羅斯的民族現代化再次被腰斬,完全被東斯拉夫的“兄弟民族”吸收。
對白俄羅斯民族文化和語言的執念,始終流傳在這一帶的知識分子圈。在1848年觸發的東歐民族主義蘇醒,也在白俄羅斯的土地上產生回響。然而,相比起轟烈的波蘭和匈牙利民族運動,白俄羅斯的民族覺醒可以說是茶杯中的風暴。
往昔波蘭-立陶宛聯合王國的影子猶在,試圖掙脫沙俄統治的白俄羅斯知識分子,參與的是波蘭人發動的民族革命。在昔日聯合王國的故土上,民族關系混亂不清。日后成為波蘭民族詩人的亞當·密茨凱維奇的出生地是今天的白俄羅斯,然而他卻用波蘭語寫作。他寫下偉大的波蘭民族史詩《塔杜施先生》,第一句卻是:“立陶宛!我的祖國!”在今天,密茨凱維奇幾乎成為了波蘭、立陶宛和白俄羅斯共享的大文豪。
20世紀歐洲災難的化身
一戰的爆發,把歐洲東部的地緣政治秩序徹底摧毀。一馬平川的白俄羅斯,再次成為兵家必爭之地。

20世紀初的明斯克街頭
有人說,白俄羅斯國旗“上紅下綠”的顏色應該調轉過來,變成下紅上綠—畢竟這片土地在20世紀是名副其實的血液流淌之地。白俄羅斯的每一條村,每一個鎮,每一座城市,幾乎都有紀念各種戰事的陣亡人員紀念碑。
1920年,波蘭軍政府領導人畢蘇斯基踏上了征服白俄羅斯的道路,試圖恢復波蘭-立陶宛聯合王國當年的宏大版圖。波蘭軍隊與蘇聯紅軍爆發沖突后,波、蘇雙方在第二年達成協議,瓜分了今天屬于白俄羅斯的土地:波蘭第二共和國東部三省和白俄羅斯蘇維埃共和國。
希特勒1941年發動的“巴巴羅薩”計劃,更加把刺刀深深扎進了白俄羅斯的土地。納粹德國除了屠殺這里的猶太人,對白俄羅斯人也毫不留情。德軍摧毀了大量的白俄羅斯村莊,在占領時期共殺死了幾乎100萬白俄羅斯人,并且把明斯克徹底夷為平地。不少白俄羅斯老人見證了德國人在明斯克街上大肆射殺無辜白俄羅斯少女,把整條街染成紅色。
白俄羅斯幾乎每一個家庭都有衛國戰爭時期的死難者。在今天,白俄羅斯政府把紀念衛國戰爭列為最隆重的日子。新冠疫情肆虐的同時,盧卡申科當局依然我行我素舉行大閱兵。不少參加觀禮的老兵都說:“既然經歷過槍林彈雨,一點疫情算不了什么。”
歷史對白俄羅斯民族的傷害不僅來自西邊,也來自東邊。1988年在明斯克郊區的一片森林里,人們發現了一個大型萬人坑,里面有3萬多具尸骨。經過鑒定頭顱彈孔,當地歷史學者總結,這是斯大林時期白俄羅斯大清洗的受難者。萬人坑的發現,讓白俄羅斯社會大受震動。
同時,烏克蘭北部切爾諾貝利核電站的核輻射,隨著北風向白俄羅斯方向擴散,使白俄羅斯成為切爾諾貝利事件的最大受害者。白俄羅斯南部歷史悠久的可耕地化為烏有,村莊丟空,不少國民患上絕癥。80年代末發生的這兩件事情,直接刺激了白俄羅斯人的民族主義情緒,成為蘇聯解體前夕的重要事件。
也難怪有人總結,20世紀歐洲屢次發生的危機和災難都不是白俄羅斯引起的,卻一定要讓白俄羅斯吃下苦果。
白俄羅斯官方從1994年到2014年一直強調蘇聯傳統在該國的延續性。

切爾諾貝利事件的受害兒童
從親俄到重新向西
東歐民族國家在形成的過程中,或多或少都會參考西方的議會制度。即使是長期受沙俄帝國和蘇聯統治的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和立陶宛,也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實行過長達近30年的議會選舉模式。
在蘇聯解體后,波羅的海三國撿起被壓制的民族國家法統,并不是難事。而白俄羅斯和摩爾多瓦這些更加邊緣化的加盟共和國,卻從來沒有這樣的現成國家制度藍本。
明斯克被納粹德國摧毀后,沒有受到華沙那樣的重建資助,作為國都的建筑,除了蘇式風格外沒有任何民族特色。白俄羅斯蘇維埃共和國是蘇軍重兵把守的咽喉要道;明斯克空軍基地的蘇聯戰略轟炸機,能夠把西歐所有國家在瞬間化為火海。這些也讓明斯克在冷戰時期成為西方戰略武器瞄準的重要目標。
蘇聯解體后,白俄羅斯建設國家的藍本,唯一參考的標準就是蘇聯留下的一套管治制度。白俄羅斯的國徽、軍隊制服、軍徽等,都保留了鮮明的蘇聯特色,從首都到各個鄉鎮遍布列寧雕像。與民間的民族主義熱情相反,白俄羅斯官方從1994年到2014年一直強調蘇聯傳統在該國的延續性。
完全沿襲蘇聯計劃經濟的白俄羅斯在獨立后,嚴重依賴俄羅斯。盡管有完備的工業基礎,白俄羅斯與西歐幾乎毫無經濟交往,能源命脈也被俄羅斯牢牢掌控。盧卡申科在90年代甚至與葉利欽領導的俄羅斯簽訂“統一協議”,讓兩國最終重新統一。然而根據協議,白俄羅斯總統和俄羅斯總統將輪流領導新的統一聯邦,這讓俄羅斯方面感到盧卡申科“以小吃大”的野心。在普京上臺后,這份協議就被塵封了多年。
因為特殊的地緣政治因素,白俄羅斯不得不在西方和俄羅斯之間走微妙的平衡路線。
2019年是白俄羅斯和俄羅斯的“統一協議”簽署20周年。塵封多年后,俄羅斯突然對這個“小弟弟”重新提起了這份協議。普京和盧卡申科舉行了長達7個小時的閉門會談,兩人的解讀卻很不一樣。隨著普京爭取2024年繼續擔任總統,盧卡申科嗅到了致命的危險:為了爭取民間支持,普京也許會把白俄羅斯視作下一個獵物。盧卡申科也許吃不下俄羅斯,卻會被俄羅斯吃掉。
于是,白俄羅斯語課程被重新提上日程,盧卡申科爭取到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到訪,一起談論白俄羅斯的能源問題。這位執政多年的強人也罕見地用白俄羅斯語發表演說,甚至罕見地提及立陶宛大公國的歷史。有反對派人士批評,傍了俄羅斯多年的盧卡申科,試圖把自己包裝成唯一能保證白俄羅斯不會被鄰國吞并的捍衛者。
白俄羅斯國會也通過了新的國徽法案,國徽上的地球原本只露出了白俄羅斯、俄羅斯和東歐地區,而新的版本卻變成了白俄羅斯和整個歐洲版圖,乃至大西洋都被囊括其中。或許這也是白俄羅斯急于擺脫“老大哥”的一種微妙姿態。經常被電視鏡頭捕捉到眉頭緊鎖的盧卡申科,作為白俄羅斯這樣脆弱國家的領導,也許真的沒有多少高興的時候。
責任編輯謝奕秋 xyq@nfcmag.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