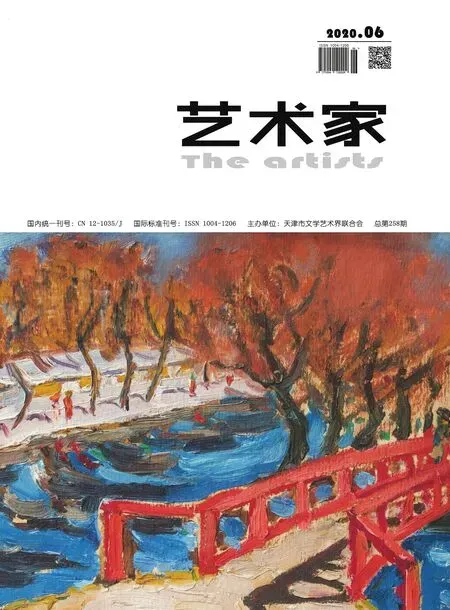當文物遇上二次元文化
——關于文物擬人游戲化的思考
□姜雨孜 四川大學
近年來,隨著黨和政府對美育的號召,《我在故宮修文物》《如果國寶會說話》《國家寶藏》等節目的播出,各種文創產品的大力宣傳等,文物以越來越重要的身份逐步走進公眾視野。與此同時,二次元文化正方興未艾。早在2017年,《光明日報》就報道稱二次元文化正“從小眾走向大眾”。隨之,“文物+二次元”這兩種文化奇妙地碰撞在了一起,生動有趣的文物擬人開始出現。未來這種新興的文化形態將如何發展,如何更有效地實現“二次元美育”便成了急需思考的問題。
一、文物擬人的發展現狀
大眾普遍認為,二次元文化是由動畫(Animation)、漫畫(Comic) 和電子游戲(Game,更準確的英文詞匯是 Electronic Game或Video Game) 這三種媒介類型混合發展而來的所謂的“ACG文化”。在二次元文化中,“擬人化”即以某物為原型,通過動漫人物形象的方式表現出來。它們奉行“萬物皆可擬人”的真理,不論高校、建筑、食物、文字等都可以作為擬人的對象。一些“擬人化”的企劃活動,推動了這種形式的傳播與發展。文物擬人大致出現于2011年,但真正開始流行卻是在2018年,當時《國家寶藏》推出了“讓國寶活起來——國寶擬人化”活動,《如果國寶會說話》也同B站共同推出了“國寶復‘活’”計劃。文物擬人是“文物熱”與二次元文化相遇的最直接的表現形式,即在這些形象中融進了文物元素,使得其也煥發出新鮮的創造力。熱衷于文物擬人的大多是青少年,他們更樂于接受二次元這種新興文化。在一定的程度上,這種形式加強了對文物的傳播效力,讓更多的人以這種趣味性的方式了解到文物。在2020年3月Myethos聯合《國家寶藏》欄目組推出了葡萄花鳥紋銀香囊擬人化手辦(見圖1),在網絡上大受好評。在筆者看來,如果能使這種擬人化的形態“動”起來,成為游戲,則不僅僅能提高文物形象本身的曝光度,更能通過文物故事來弘揚優秀的中國傳統文化。
二、文物擬人游戲化的關鍵
事實上,在2018年就出現了首個文物擬人的戰斗冒險類手游《億次元》,這款游戲雖然對文物進行了擬人化處理,但游戲在細節處理上和普通的戰斗冒險類手游無異,并未很好地突出文物擬人的優勢。毋庸置疑,文物擬人的核心在于讓大眾通過二次元來了解中國傳統文博文化。因此,筆者認為文物擬人化游戲應注意以下幾方面。
(1)以文物故事為核心:每一件文物背后都有其自己的故事,讓文物“活”起來,不僅要對形象進行再創造,更要讓文物故事“活”起來。正如數字媒體技術在博物館所作的那樣,并不是為了展示科技水平的高超,而是提供一種更有效地使觀者了解文物故事的途徑。文物擬人可以第一人的視覺道出自己的前世今生,可以讓用戶通過解鎖主線或支線劇情,了解文物背后的故事。
(2)緊緊扣住文物的特點:值得注意的是,用戶關注的并不僅是“擬人化形象”本身,而是根據文物的特有屬性與游戲巧妙地結合,更便捷地獲取知識及游戲體驗。如將考古地點與游戲地圖/卡池相結合,當玩家到了“二里頭遺址”就能獲得相關青銅器擬人的卡牌;加入“文物修復”等環節,待文物修復完畢,才可獲得完整的卡牌;將文物與館藏結合起來,與各大博物館進行合作,并推出相應的卡池、關卡或劇情等。游戲在展示擬人形象的同時,也最好將文物原圖片展示出來,如此一來,用戶對文物的印象就不只是擬人的,而是基于原文物的“活”起來的形象。
(3)朝著多元化方向持續發展:文物擬人游戲可以通過企劃擬人設定活動,號召更多的人在參與企劃的同時學習文物知識,還能與各大博物館聯名推出擬人化形象的相關周邊游戲。這樣看來,文物擬人游戲化有著較為廣闊的市場前景。
“文物+二次元”的發展必定是大勢所趨,“二次元美育”也將作為新的美育形態步入大眾視野。誠然,在“互聯網+”與多元文化并存的新時代,人們選擇各種方式去了解傳統、了解文化。然而,對于認識文物來說,不論是文物擬人游戲還是其他任何形式,都無法替代人們真正地去博物館近距離地感受文物古老的氣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