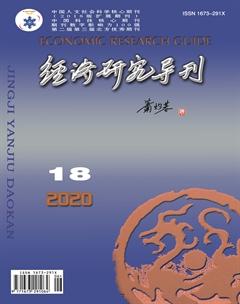我國文化產業政策工具選擇:價值取向與邏輯機理
湯佳樂 羅章 譚祝


摘 要:適當的政策工具是政策目標得以實現的必要條件,政策績效水平的提高也依賴于恰當的政策工具選擇。針對我國的文化產業發展需要如何進行工具選擇,以東中西部六個代表城市為研究樣本,在文本分析的基礎上,綜合運用歐文·修斯與麥克唐納爾和艾莫爾的政策分類標準來識別政策偏好,并挖掘政策偏好與產業目標間的關系。研究發現,六個城市政策工具選擇都體現出“目標”與“環境”相協同的邏輯,有效的文化產業政策工具都表現出了對政策目標的“回應性”和對環境的“適應性”。
關鍵詞:文化產業;政策工具;城市競爭力;政策環境
中圖分類號:G124? ? ? ? 文獻標志碼:A? ? ? 文章編號:1673-291X(2020)18-0055-03
一、問題的提出
近年來,文化產業已逐漸成為衡量一個國家、一個地區綜合實力和競爭優勢的重要標準之一,對整個國民經濟發展具有不可忽視的影響。從黨的十七大報告提出“文化產業占國民經濟比重明顯提高”,到黨的十八大報告強化了“推動文化產業成為國民經濟支柱性產業”的發展目標,文化產業發展的重要性日益凸顯,各城市也將發展文化產業作為提升城市綜合競爭力的重要抓手,我國的文化產業迎來了歷史性的發展機遇。
中國文化產業的最大特色是政府在其發展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文化產業政策是政府介入文化產業發展的集中體現,對文化產業的發展起到引導、管理、扶持和調控的作用[1]。而在文化產業政策中,政策目標一旦確定,政策工具的選擇就成為焦點——政策執行過程本質上就是政策工具選擇的過程,政策工具選擇是決定政策成敗的關鍵[2]。依此觀之,要有效推動中國文化產業的發展,需要以政府為核心的公共部門選擇和運用適當的政策工具。可以說,政策工具選擇及運用是實現文化產業長足發展的關鍵變量。
但學界對文化產業政策工具的選擇與運用問題還缺乏關注,鮮有學者從政策工具視角對文化產業問題進行深度挖掘。因此,在全國乃至全世界文化產業的政策實踐遍地開花、成果斐然的背景下,將文化產業政策實踐作為研究素材,以政策工具的運用為觀測點,探討我國文化產業政策工具的使用邏輯能夠回應迫切的現實需求。
二、文獻綜述
20世紀80年代,公共行政領域開始研究“政策工具”問題。胡德將“政策工具”定義為,政府為了實現一定的目標而采用的治理工具,并認為政策工具研究的核心是如何將政策意圖轉變成行動,將政策理想轉變為現實。文化產業政策工具是指政府為推動文化產業發展、達到某一預定政策目標而采用的手段或方法。當下,對文化產業政策工具的研究集中在兩個方面。
1.對文化產業政策工具的區域性差異的研究。文化資源稟賦和經濟發展水平差異加大了文化產業發展的區域性差異,東部文化產業蓬勃發展,依靠的是市場類工具;西部憑借自身特有的文化資源,多采用行政類工具;中部地區促進文化產業發展的工具兼容性更強[3]。王鳳榮等通過分析政策數量與政策時效,發現文化產業政策的空間分布凸顯東中西部三者的區域性差異并顯示出差異有效性。
2.產業政策工具的應用現狀研究。王春城、耿偉華認為,政策工具的有效性應該是政策工具選擇的出發點。但作為案例的石家莊的文化產業政策工具,在運用中存在著管制不靈、補貼效果較差等問題。郝大偉、湛冰、王凱珍結合X維度和Y維度分析指出,我國體育產業政策工具的運用存在環境型政策工具“強勢”、功績型政策工具“弱勢”、需求型政策工具“缺席”等問題。
相關研究表明,區域的差異性與產業的差異性不僅明顯影響到政策工具的選擇,還導致產業政策工具在使用類型上出現不均衡的問題。其中,需要特別注意純粹的“工具主義”或者“過程主義與備用主義”對政策工具選擇的影響。基于上述研究,本文利用“目標—工具—環境”的分析框架來辯析我國文化產業政策工具選擇的邏輯。
三、“目標”與“行為”協同的政策工具分類框架
在梳理國內外相關研究的基礎上發現,在政策工具類型劃分方面的成果頗為豐富,在學術上有代表性和影響力的學者胡德、歐文·休斯、霍萊特、拉梅什、戴維·奧斯本等都是享譽學界的大家,其成果為國內外學者的研究奠定了深厚的理論基礎。國內的學者(陳振明、張成福等)結合中國具體國情及案例分析,在現有理論基礎上對政策工具提出了新的分類框架,豐富了政策工具分類的知識體系。但是,政府工具的無限創生性使得涵蓋所有政策工具的分類成為困難。因此,現有的政策工具分類未能對現實工具對象進行清晰的區別和界定,類型也缺乏具體描述,且不同分類的工具類型之間尚存在交叉、重疊。正如陳振明所說:“在我國,政策工具的研究雖已起步,但仍存在大量問題需要進一步研究,如政策工具的分類、選擇、評價標準以及在政策與管理過程中扮演何種角色等等,因而該方面研究遠未成熟,仍有很長的路要走。”[4]
根據政府行為方式,歐文·休斯以政府干預經濟的手段為標準,將政策工具劃分為供應、補貼、生產、管制四類。通過整理歐文·休斯對政策工具劃分的思想,不難發現:首先,政府的行為必須通過合法的政策工具才能正當化,即行為合法依賴于工具合法。其次,政府與市場這雙“看得見的手”和“看不見的手”,在功能上是相輔相成、互相補充的。最后,市場是存在一定缺陷的,政策工具的選擇受市場發育程度的影響。基于以上三點,歐文·休斯的工具劃分回答了“誰來支付”“作用于誰”和“提供了何種產品”三個問題。麥克唐納爾和艾莫爾根據工具所要獲得的目標,將政策工具分為命令性工具、激勵性工具、能力建設工具和系統變化工具四類。本文將歐文·休斯和麥克唐納爾、艾莫爾對政策工具的分類進行十字交叉組合,既關注政策工具運用主體(政府)的行為,又關注政策工具的目標指向。
四、我國文化產業政策工具的選擇邏輯分析
東中西部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市場發育程度、文化資源稟賦等文化產業發展要素的不同,深刻影響政策工具的選擇。根據經濟發展的梯級理論,本文在東部地區選擇杭州、深圳,中部地區選擇武漢、長沙,西部地區選擇成都、西安,將上述六城市作為研究樣本。這些城市的文化產業在當地GDP中的占比均超過5%,已成為經濟發展的“支柱型產業”。
基于政府部門網站和中國文化產業政策庫,本研究集中搜集了2013—2018年5年間6個樣本城市文化產業發展的97份政策文本作為分析語料。采用政策文本分析方法,以政策工具為觀察點,結合政策的語義對政策工具概括分類,研究得出區域性文化產業政策工具的偏好與邏輯。
1.東部偏好:市場主導,政府服務。東部城市傾向于以政府補貼的方式引導文化產業市場的發展,目標指向是激勵文化產品的市場性生產主體(企業及消費者),重視其能力建設。首先,東部運用了大量依托市場運作的激勵工具籌集文化產業的發展資金。例如,杭州設立文化創意產業融資風險補償基金;深圳鼓勵上市企業發行企業債券等,將民間資本、社會資本吸納到文化產業的投融資體系中。其次,東部重視文化產業市場能力建設,強調技術研發及文化產業專業人才的培養。例如,杭州鼓勵文化產業人才參加實務培訓;深圳注重構建產業支撐平臺(建設教學、科研和培訓基地等)以鼓勵政策研究、技術研發。最后,東部強調以保護(正向管制)和服務為主,為文化產業的發展營造良好的競爭環境。例如,杭州提倡數字版權保護、網絡保護;深圳提供糾紛調解、法律援助服務等。綜合來看,東部運用了大量依托市場活性的政策工具,體現了偏市場的邏輯,主要集中在市場運作環節。
2.中部邏輯:政府服務,市場參與。中部城市既強調政府推動,又注重市場運作,運用的政策工具涉及到機關單位、國有企業、市場等全方位的文化產業主體,主要以供應方式建設文化產業發展的基礎設施,并以補貼的方式激勵企業進行文化產品生產。首先,中部運用了較多“偏政府”的專項資金推動文化產業的基礎設施建設,并開始運用“偏市場”的激勵工具整合社會分散資源。例如,武漢、長沙都強調利用文化產業發展資金的引導來推動產業基地建設。與此同時,這兩個城市都開始運用鼓勵風險投資、抵押貸款等市場型激勵工具,拓寬文化產業的融資渠道,實現了分散資源的有效整合。其次,中部重視以政府的能力培養來提高文化產業發展質量。武漢和長沙都注重政府內部管理人才的培養,并主動開放部門數據庫、搭建公共服務平臺以服務文化產業發展。最后,中部對市場的管制體現了“打擊”(負向管制)與“保護”(正向管制)雙管齊下的邏輯。例如,武漢強調監督和整治(負向管制),而長沙強調知識產權保護等。總體看來,中部的政策工具選用體現了政府服務、市場參與的傾向,呈現出政府推動、放權市場的邏輯。
3.西部選擇:政府主導,政府推動。西部城市運用的政策工具數量較少,缺乏創新性且多為政府主導型;政府主要以“供應”和“管制”行為介入文化產業的發展。首先,西部傾向于通過政府扶持資金和優惠制度建設來推動文化產業發展。例如,成都通過財政出資、設立文化產業專項資金來推動園區等基礎設施建設。西安注重以優惠制度(稅收優惠、土地優惠等)吸引文化企業。其次,西部主推政府管理人才和文化產業服務平臺兩方面的建設,體現了政府自身對服務文化產業的重視。例如,成都通過部門內部管理人員的培訓和任用制度創新,增強公務員的業務能力;西安通過交流平臺、文化產業發展平臺、服務平臺的搭建,拓寬政府服務文化產業市場的途徑。最后,從命令性工具來看,西部強調文化市場行政執法的作用,重視市場管制(負向管制)。例如,成都和西安都注重對文化市場進行監督管理。綜合來看,西部的文化市場發育程度還較低,政策工具選用體現出其文化產業發展還處于政府主導、政府推動的階段。
4.總結。研究表明,我國各地政府在推動文化產業發展中所使用的政策工具從結構上看大同小異,均包含供應、生產、補貼、管制四大類,在使用目標上涵蓋命令、激勵、能力建設、系統變化四大塊;但在具體政策工具的數量及作用目標的側重點上則呈現出明顯差異。綜合看來,各地文化產業政策工具群的選擇差異所呈現的邏輯(如下頁表所示)。
該表反映出我國文化產業政策工具的使用,在東中西部存在三個較為明顯的區域性差異。東部(杭州、深圳)的市場激勵型政策工具占主導地位,政府主要承擔“服務者”的角色。創新性市場激勵工具紛紛出現且更具針對性,并以正向激勵為主,引導的性質更為明顯。中部(武漢、長沙)政府的推動力量開始減弱,并逐步轉向政府服務。中部城市既有政府制定戰略、規劃、興建文化產業基礎設施等舉措,又開始運用依賴市場運作的各項融資措施、擔保服務等工具。但總體來看,中部“政府—市場”兩者的關系尚未厘清,市場激勵型政策獨立性較差。西部(成都、西安)以政府推動為主,行政指令、負向管制運用較多,政策工具運用沒有鮮明的地方特征,多是對中央指導思想的回應。政策工具缺乏創新且大部分為命令型,市場機制沒有得到很好的發揮,市場激勵型政策工具的運用較少或尚停留在政策層面,未能有效落實。
五、政策工具與“目標”“環境”的協同機理
起初,政策工具選擇是基于嚴格的工具理性,認為政策工具只是達成政策目標的手段。因此,選擇一種政策工具,在于分析其政策工具的內在特征和績效,看其政策目標是否具有一致性。之后,公共政策之父哈羅德·拉斯韋爾強調對政策所處時間與空間保持敏感。他曾表示研究的意圖不在于尋找歷史規律,而是“使政策分析家及決策者能夠處理身處其中的復雜環境”。拉斯韋爾將環境變量引入了政策工具的選擇之中,強調政策工具的選擇會隨環境的變化而變化,重要的是要尋求與具體環境相“匹配”的政策工具。這無疑是對政策工具選擇的一種重大矯正。隨后,“新公共管理”的理論先驅胡德認為:“要保證政策工具選擇的有效性,不僅應考慮目的本身,還應理解政府工具與環境之間的關系。政策工具具有高度的政治和倫理相關性,會隨著政治目標的不同而轉變,同時不同情境下特定工具的表現也會有優劣之分。”
結合產業發展的規律來看,文化產業發展要經歷由稚弱到成熟的發展階段,并且在產業發展的稚弱期與成熟期,政府與市場的功能是有差別的[5]。文化產業發達國家的經驗表明,政府在推動文化產業發展中的作用是全方位的,但主要是在戰略層面上的領導。政府只是在為產業和企業的發展提供服務,包括提供公平、透明的競爭環境。由于文化產業是經濟和文化的聯姻,具有與一般產業不同的屬性,所以,政府在推動文化產業發展中不是也不應當是產業發展的主體或最終決定者,而應是產業和企業發展的服務提供者。再者,我國文化產業發展本身具有區域不均衡的特點,因此政府在促進文化產業發展的過程中應因地制宜,尤其是政策工具的運用應符合德瑚(R.H.DeHoog)提出的適應性和回應性標準[6]。具體來說,文化產業的“政策工具”與“目標”構成回應性標準,“政策工具”與“環境”構成適應性標準。回應性標準關注政策工具的選擇能否回應政策目標,即應回歸政策工具本身的特性及功能,預測政策工具的運用能否達到預期的政策效果。適應性標準關注政策工具的選擇與已有的政策環境及資源環境、市場環境的適配度。高適配性的工具在運用中可能遇到的阻力較小,能充分調動已有的資源,有利于政策工具效用的發揮及政策目標的實現。鑒于此,本文提出文化產業政策工具的選擇應包含“目標—工具—環境”的邏輯,即合適的文化產業政策工具應與目標具有高度回應性、與環境具備高匹配度。
本文從文化產業政策工具的選擇實踐來分析文化產業政策工具的差異化選擇,得出以下結論:一是文化產業區域性差異發展的背后存在政策工具的差異化組合。二是文化產業不存在固定不變的政策工具選擇模式,根據不同的業態發育和地區優勢,適合的便是最優的。三是“目標”與“環境”是文化產業政策工具選擇的兩個維度,適合的工具應具備對目標的高度回應性、對環境的高度匹配性。四是只有發現和有效處理不同環境的差異與敏感點,才能利用好資源,選擇更合適的政策工具。
參考文獻:
[1]? 解學芳.文化產業政策的比較機理研究——以長江三角洲地區為例[J].上海行政學院學報,2008,(5):65-72.
[2]? 陳振明.政策科學——公共政策分析導論[M].北京:北京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193.
[3]? 梁君,陳顯軍.我國區域間文化產業發展差異研究[J].經濟縱橫,2012,(4):63-67.
[4]? 陳振明.政府工具研究與政府管理方式改進:論作為公共管理學新分支的政府工具研究的興起、主題和意義[J].中國行政管理,2004,(6).
[5]? 王亞川.論政府在推動文化產業發展中的角色[J].理論研究,2007,(1).
[6]? Ruth H.DeHoog.“Citizen Satisfaction With Local Government Services:A Test of Individual,Jurisdictional,and City Specific Explanations[J].Journal of Politics,1990,(8):807-837.
[責任編輯 晨 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