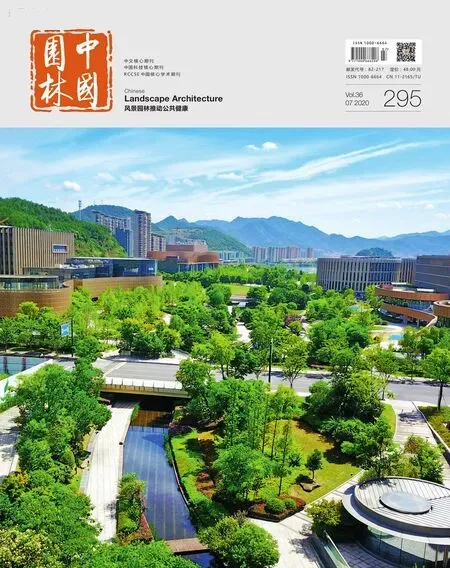由當今疫情出發思考未來風景園林
馬曉暐
在人類近代城市建設發展的歷史長河中,通過改善人居環境來因應流行病事件的努力占據著一席之地。歷史上,每次公共衛生與環境事件的爆發都會帶來人們價值觀的轉變和對人居公共環境建設的反思,并會引發對風景園林行業發展新風向的思考與探討。
1 近代公共園林在城市公共環境問題下應運而生
早在3 000年以前,人類開始在城市中聚居,對于解決城市公共安全、衛生環境問題也做出了初步嘗試。2 000年前古羅馬的城市龐貝的雨污管理體系便已初具規模。然而,人類聚居地城鎮化的過程帶來了不可調和的人居環境衛生與健康問題。19世紀的歐洲城市衛生系統已完全跟不上城市擴張的速度,甚至排泄物被隨意傾瀉于街道、護城河等行為在類似巴黎這樣的歐洲著名都市成了普遍現象。在中國,北京的大部分街區也是到了20世紀初才開始實施路面硬質化與鋪設污水管道。這種令人堪憂的公共衛生環境無論是在歐美還是中國,都曾引發多次大規模流行病和公共環境污染事件。
公共園林的興起與城市環境的惡化、瘟疫的流行所引發的公眾訴求有著緊密的聯系。19世紀的英國就曾飽受工業革命后公共環境污染的困擾。空氣污染、城市人口聚集、城市公共衛生體系尚不完善,這些問題都促使了霍亂細菌的滋生和傳播。英國城市公共衛生體系由此開始改革,基于關注底層人民惡劣的生活環境,以及滿足公眾對于回歸自然的向往,議會通過“私人法令”明確提出城鎮中絕大多數的納稅人擁有享受公共綠色開放空間的權力。英國政府據此允許城鎮使用稅收建設城市公園。由皇家園藝師約瑟夫·帕克斯頓(Joseph Paxton,1803—1865)設計的利物浦伯肯海德公園(Birkenhead Park)成為世界造園史上第一座真正意義上的城市公園。在此影響下,西方國家出現了公園建設的熱潮,近代公共園林的序幕就此拉開[1]。可以說,公共園林伴隨著公共衛生事件后人們對改善人居公共環境的需求應運而生,而風景園林行業則隨著每一次城市公共衛生與環境問題的爆發而不斷反思、轉變與發展。

圖1 民國老明信片描繪了人們在漢口中山公園中散步和跳廣場舞的場景(作者提供)
2 中國近代公共園林是改善人居環境的先驅和典范
早在秦漢時期我國就已經開始營建公共衛生設施系統,但由于人口規模不斷擴張,尤其是到了清代乾隆時期人口數量成倍增長,城市難堪重負。直至民國初年,中國城市的衛生環境面臨了嚴重的問題。
民國時期,當今受疫情影響最大的城市武漢正是中國近代城市中通過建設漢口中山公園改善城市環境的典范。近代的武漢九省通衢,在民族工業興辦高潮的帶動下大量人口涌入城市,而城市的基礎建設卻嚴重滯后,生活環境雜亂骯臟,街頭巷尾的野糞隨處可見,郊外甚至有數以萬計的浮棺被隨意棄置,造成了嚴重的公共衛生隱患。與此同時,當時正值百姓“抽鴉片、打牌、白天睡覺,沒有公園、樹木,百姓甚至春、夏、秋、冬都不曉得”[2],人們深受鴉片禍害,生理和心理的健康問題嚴重。因此,建設面向所有市民的康身健體公共場所和吸引人們重振自我、自強救國的精神家園成了有識之士對于公共環境建設的主要訴求。1928年,從英國留學回來的工程師吳國柄響應李宗仁“建設新湖北、新武漢”的號召,毛遂自薦,立志讓武漢的城市環境和生活風貌有一個全新的面貌。吳國柄對于倫敦市區的城市基礎設施整改和大公園印象深刻,認為這些對于改善市民的身心健康起到了非常正面的作用。在這種思想的帶領下,他開始著手清理浮棺,并開始組織漢口中山公園的建設[3]。
作為中國首批自建的近代城市公園,武漢中山公園與傳統園林最大的差別就在于以改變市民健康狀況、提升人民精神意志與民族競爭力為目的,以康體健身、自強自律為設計主題,將體育場作為整個公園的重點進行布局。公園的整體架構以原有的中式山水園林西園為基礎,結合西式幾何規則式景觀和標準化運動場地,形成了獨特的混合式布局[4]。武漢中山公園開園首日便涌入了5萬人進入參觀,市民們紛紛來到公園散步、活動(圖1),在當時引起了全國性的轟動,甚至吸引了蔣介石夫婦入園參觀。其一度成為公共園林建設的效仿對象,武漢的城市環境也因此邁上了一個新的臺階。同一時期,上海虹口公園、北京中山公園、廈門中山公園等一系列新建公園在建設主旨上與武漢中山公園皆如出一轍[2]。
新中國城市環境得到了翻天覆地的提升和改善,特別是在過去20年的快速城市化進程中,城市公園建設的成果爍然,而隨之轉變的是人們的價值觀、生活方式。尤其在當今世界級衛生事件的推動下,人們身心健康的意識和對人居環境的需求已發生了巨大的轉變。我們應當意識到如今的多數城市公園在提供基礎的健身器材之外卻忽略了當今人們身心需求的轉變,風景園林行業應當再一次開始重視人們新的生活方式和與之息息相關的環境需求。
3 當今由疫情推動的人居環境需求轉變
當今新冠疫情的規模、持續性,以及全球性的影響力都遠遠超出了人們的預估,足以在大范圍內改變人們的價值觀和人生觀。隨著隔離生活的體驗,遠距離社交的普及和遠程辦公的推進,人們對城市、郊區的需求同樣也發生了一定程度的轉變,甚至開始出現逆城市化的呼聲。現階段我國大中城市并不缺乏公共綠地的數量,但點狀布局的公園參與性較差,公園之間缺乏人車分流的連接系統。大城市周邊的郊區雖然有相當數量的獨棟別墅區,但布局零散、配套設施嚴重缺乏、自然綠地被道路分割,幾乎不能稱之為真正意義上的郊區。城市與近郊的紐帶雖然開始出現綠道系統,但仍然功能單一,缺乏與生態系統、交通系統及公共參與性活動的充分整合。在人們生活需求質變的當下,我國城郊綠地系統的定位面臨著進行重大調整的機遇與挑戰。風景園林的專業定位也亟須做出相應的轉變。
在疫情推動之下,人們對于城市人居公共環境有了新的與公共衛生健康相關的需求,并更加關注在自然環境中進行身心健育的重要性。隨著越來越多的人渴望通過戶外的運動來提升自身的免疫力,人們迫切需要公共綠地提供多元化、高質量的參與性場所與脫離城市、怡神靜心的世外桃源。向公眾免費開放的大型運動場地、無障礙設計、多元化、為多種年齡段人群提供的可參與性活動場地、避雨連廊公交換乘體系、寵物公園,以及引發人們共鳴與記憶的景致等都將成為城市公共綠地里的基本要素。此外,社會也更加需要城市公共環境提供可作為應急留白空間的場所。英國海德公園和紐約中央公園等公共園林就是城市公共綠地的典型案例。它們以人行系統和自然系統優先,均設計提供了大量多功能綠地空間和復合型的連續運動環線,在滿足人們康體健身需求的同時,還提供了緊急應災的城市留白空間,如近日疫情嚴重的紐約市便將中央公園的草地變為臨時性方艙醫院[5](圖2)。它們不僅良好地應對了當時城市公共衛生與環境問題所引發的市民生活需求,還為城市加強了城市應急防災安全系統。這些都為提高我國城市公園綠地的綜合性功能水平提供了有益、可借鑒的先例。
同時,此次疫情進一步引發了人們對于在郊區生活的思考與選擇。過去的20年不僅僅是我國城市化迅猛發展的時期,同時也是美國經歷大城市人口回流熱潮的時期,而這次疫情恰恰充分暴露出了人口密集的大都市更易成為流行病爆發地的問題。疫情之下我們看到世界各地均出現大量人口逃離大都市的現象。郊區成了避疫熱點,居家云辦公的迅速推進讓郊區化成為未來生活模式的一種可能。因此,建設滿足高質生活需求的配套服務設施與更加親近自然、環境良好的低密度郊區生活將成為郊區人居環境設計的焦點。然而,我國的郊區尚未成形,對于獨棟住宅生活不便的偏見使得中國城市的郊區呈現與市區差異較大的人口密度。在此背景之下,對于郊區的再思考應當提上議事日程。目前散落在農業用地的獨棟住宅區應連成完整的區塊,配套設施如醫院、學校、大型超市和生態綠地系統等應加速跟進,讓已經投入的建設資本真正發揮作用。此外,我國的住房建設以高層住宅為主,而高層住宅的不可更新性是未來城市的潛藏問題。即便是日本這類人均耕地面積比中國少的國家,郊區也是以獨棟住宅為主要形態。未來郊區低密度住宅的規劃設計應以住宅的可更新、可再投入作為基礎條件,使業主的持續投入變為拉動經濟的動力。同時,以家庭投資為基礎單位的小地塊開發也應開始嘗試實施。

圖2 紐約中央公園的方艙醫院[5]
隨著可預見的大量人口將轉向城市近郊生活,建設城郊紐帶以提供安全低碳的通勤方式、每日行走,以及生活于山水草木間的天然之趣也必然成為人們對人居公共環境的需求之一,尤其是在公共衛生事件發生后要求人們保持安全距離的當下。參考早已發展郊區化生活模式的歐美城鎮,郊區化會引起每日車行通勤導致的嚴重城市交通問題。同時郊區的人們依賴公交和軌道交通,上下班高峰期人滿為患,在傳染病流行等特殊時期會帶來巨大的安全威脅。相對而言,以自行車為主體的綠道體系能夠保證低密度的人口安全距離,并能夠結合綠地營造生態怡人的環境,是值得提倡的安全低碳的通勤方式。以自行車為主體的新型低碳通勤方式正在歐美國家形成潮流。德國建成了“自行車高速公路”。英國倫敦規劃了7條步行網絡由市中心向外輻射,以期方便民眾綠色出行,緩解城市擁堵環境[6]。國內的城市如廈門、北京也積極做出了嘗試。北歐的一些國家甚至提出了到2030年建成無車化城市的目標[7]。我國近年來也經歷了城郊紐帶由早期的帶狀綠地、楔形綠地到如火如荼的綠道系統建設的過程。在這些優秀先例的基礎之上,未來的人居公共環境應當把人行系統、自然系統放在首位,取代原本車行系統為主導的結構,加強多樣化的參與性功能的植入,復合式串聯出滿足多元化需求的網絡狀景觀系統。
4 未來風景園林達成人居環境第一系統的轉型
建設什么樣的人居環境一直是包括風景園林在內的所有相關專業一直面對的課題,隨著人們對生活環境需求的變化,風景園林專業應該開始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爭取更大的話語權。錢學森先生的山水城市理念自1990年正式提出至今已有30年,其目的即在于追求人與自然之間的和諧關系,使人“離開自然又返回自然”[8-9]。馮紀忠先生在20世紀50年代初的上海都市計劃中就曾提出城市是一個有機體,與當時國際盛行的小沙里寧的有機疏散理念相呼應,認為城市的擴展應當保留原先的自然地形,街道之間會有小河,住宅區之間保留高低不平的自然坡地,每片街道都將具有自己明晰的地理形態和可追溯的微觀地理歷史[10]。我們今天看到的國內大部分城市與郊區建設往往完全抹去了原有的山水骨架和自然肌理,到處是強加于自然的機械呆板的路網結構;車行系統優先,行人居于次要和附屬的地位,帶狀生態系統因被道路切割缺乏生態效益而成為擺設,千城一面難以扭轉;同時還存在著將城市里并不成功的基礎設施建設手段簡單復制到山地郊區的危險措施。由風景園林人主導的城市基礎設施系統應該而且必須成為未來城郊建設的主流途徑,以風景園林的綜合性統籌城市與郊區系統的規劃,從本質上促成人居環境結構的根本性轉變。
未來穿行城市與郊區的人行體系應當與自然體系結合而上升為超越車行道路的人居環境第一體系(圖3)。景觀不再只是基礎設施,而應成為主導性構架。在人居環境第一系統理念下,未來每個自然主義城市核心都將由景觀體系主導。人居環境第一系統下的景觀體系將是一個網絡狀系統,由空中廊道、廣場、城市公園、綠地、郊野綠道體系、郊區公園體系、生態廊道及河道體系共同構成。如美國明尼阿波利斯市的2層空中廊道和新加坡的室內廊道;日本東京六本木商業區聯系整個區域的步行系統;上海的陸家嘴金融區和徐家匯商圈覆蓋在車行系統之上的人行系統;巴黎拉德芳斯新區分流車行系統并建于其上的巨大人行平臺;英國倫敦國王十字車站邊濱河綠道和公共場所的結合(圖4);新加坡連接了屋頂空間和地下空間的全人車分流廊道;以及香港中環的空中連廊等都是第一體系在城市密集區域里實施的成功范例。第一體系不但是交通體系,也是城市與城市近郊生態鏈條的重要組成部分。除此之外,體系中的綠地必須采用明匯水的設計方法,在保留和利用原有地形的同時蓄留雨水、強化生態多樣性,形成交通廊道和藍綠廊道并存、參與性內容合理且豐富的復合型網絡體系。

圖3 把人行、自然系統作為城市第一系統(作者攝)

圖4 英國倫敦國王十字車站大臺階(作者攝)
人居環境第一系統理念的提出是對當代人居環境發展模式進一步的反思,明確了在未來規劃結構中景觀體系將從附屬性的角色反客為主而成為主導性力量。這是對以往的規劃中人與人、人與自然關系的扭曲而提出的思路改變,力圖使人居環境回歸到以人的尺度和活動習性為依據、以自然生態體系為基礎的和諧發展途徑。這樣的城市和郊區會和18世紀工業革命所催生的現代人居模式產生根本性的差異,我們可以將其稱之為新自然主義模式。而要真正落實以人行、自然系統作為第一系統的訴求,改變車行系統優先的規劃現狀,需要由風景園林專業來主導多專業的整合。打造綜合效益、覓因成果彰顯地宜一直是孟兆禎先生所強調的風景園林的首要任務之一[11]。風景園林不應再如以往一般作為建設流程的最后一環,而需要介入土地前期策劃、規劃、水利、市政、運營和建筑設計的全流程,與其他專業齊頭并進,甚至在地形復雜、生態條件敏感的地域擔當起多專業整合者的責任。作為一個身處城市規劃和園林設計專業之外的學者,錢學森先生曾明確提出要利用皇家園林的手法建設山水城市,這便是整合各種專業的途徑。傳統皇家園林(如承德避暑山莊)與江南私家園林的最大差別在于其具有更加巨大的用地規模和多種工種交叉的復雜性。今天如果開發避暑山莊一類的項目必定要經過總規、修規、市政、水利、建筑、景觀和室內設計等各個環節,而在古代這一切都屬于造園的范疇。由此可見多種專業的整合一直是中國傳統造園的根本特征。西方風景園林師們直到20世紀末才正式以景觀都市主義的名稱提出了多專業整合相關的思考:多學科融合[12]。由此可見,傳統中國園林并不是束縛我們手腳的障礙,問題出在當代的風景園林人身上。實際上從20世紀30年代風景園林師就已經融合到了美國的高速路系統的規劃設計工作中。Hideo Sasaki先生也早在20世紀中葉就提出和實踐了跨專業整合的理念,帶動了美國的風景園林專業實現了質的飛越。時至今天我們與國際領先水平的差距并未縮小,實際上還在被拉大。如今在國內難以找到一個全明匯水體系的城市,甚至難以找到一個全明匯水體系的園林。當代中國的風景園林從業人員應當時刻意識到這樣的差距,保持警醒的專業眼光和能力,以防陷入對于一些套路化裝飾手段的自滿與安逸之中。
多專業整合是風景園林的核心方法,而豎向整合設計則是核心技術。需要通過豎向知識指出套路化城市規劃的不合理性并找出營造城市第一系統的場地條件;需要控制市政標高來達成市政路上跨或下穿以實現連貫的人行系統;需要與水利部門討論多種水位與堤岸標高的防洪需求和濱水空間參與性之間的矛盾;通過豎向整合設計來與建筑師充分合作以使其建筑進一步發揮和利用場地所蘊藏的機遇。只有在豎向條件上說服了其他專業,風景園林人才能夠在專業整合上扮演一個主導性的角色。豎向整合設計在這個過程中扮演著最重要的角色。筆者團隊在眾多的國內市政綜合性項目中一直致力于以豎向整合設計為核心技術的跨專業整合設計實踐,最近建成的浙江桐廬高鐵站(圖5)和千島湖高鐵站完全打破了傳統高鐵站場千站一面的狀況,將綠道和人行作為第一系統,并結合換乘、服務及周邊城區的帶動,以實踐驗證了風景園林專業在統合多專業協作過程中的可行性。

圖5 浙江桐廬高鐵站(作者攝)
5 風景園林行業的未來轉變
近幾月,疫情所帶來的社會變動推動了風景園林行業對于專業當今挑戰和未來轉變的思考。有學者提出人與健康的需求,行業應當推進與之對應的城市綠地設計相關研究與實踐[13]。更有學者結合當今科技的發展總結并暢想了智慧城市、信息技術等新科技將對未來城市環境和風景園林行業帶來的促進與改變[14]。其實,這次疫情是風景園林行業的一次契機,促使著全行業借此機會整體審視目前普遍存在的問題,尋求根本性的解決方法。
無人化是當今中國風景園林普遍存在的問題,從大量無人的設計效果圖上可以看到與國外同行業巨大的反差。在國內多數已建成綠地的場地照片中所展現的幾乎都是門可羅雀的場景。缺乏以人為本的設計、缺乏人性化的關懷理念是風景園林行業的普遍問題。以靜態唯美照片論長短的評價體系顯然存在著問題,相對寬泛的以人為本的設計規范也亟待更新和提高。令人欣喜的是一些地方性法規正在跟上國際化標準,如北京市在去年底開始要求所有住宅項目都必須滿足無障礙設計標準。我們應該借鑒美國的ADA建立起高水準人性化設計的國家級標準,并且高參與性活動的植入更應成為疫情后新建項目的標志性特征。
與專業無人化并存的是專業泛化的問題。在全國城鎮建設迅猛發展的大環境下,風景園林的專業范疇也在不斷擴張,已經開始廣泛地介入國土規劃、國家公園、美麗鄉村、特色小鎮、棕地利用、遺產保護、海綿城市和文化旅游等各個領域之中。同時,我們必須思考風景園林專業的核心到底是什么?專業的核心思想、核心價值觀與核心技術是什么?我們在建設領域中應該扮演的角色是什么?風景園林亟待面對去無人化、去泛化與去空心化的挑戰,重新梳理專業的核心定位,以確保面對疫情過后的世界轉變健康發展。
當下仍未止歇的疫情是對過去20年世界全球一體化趨勢的重大挑戰,逆全球化的再思考已經成為各個國家人民直面的課題。這種思考必將引發人們對于自我與天人關系,以及對自身文化和價值觀的再審視。尤瓦爾·赫拉利就在不久前發表長文呼吁各國應當實行一個全球性計劃來抵抗疫情,鑒于當下各國采取了閉關的鼓勵措施。而其實這些被稱為“nationalist isolation”(民族主義孤立)的現象,恰恰證明了人類文明存在不同文明與價值觀的必然性[15]。福山在《歷史的終結與最后的人》中曾提出文明終結的論點[16],雖然10年后他承認了當時觀點的錯誤,但是人類文明進程與各個文明之間的關系,以及各個文明與國家對自己發展道路的選擇上仍然缺乏明確的理論支撐體系。作為以天人合一為追求目標,集哲學、藝術、工程、生態和生活等要素為一體的風景園林專業理應能夠回答人類走向的問題,并給出具體的答案。“天人合一”經常被稱作風景園林專業的核心追求。它是風景園林的核心思想,但是“天人合一”僅僅是指人類與自然環境的和諧嗎?古代“天人合一”觀的“天”并非指自然,“人”也并非指人類。中國傳統園林的“人”代表著個體,而“天”則是宇宙萬物的總稱。以“天人合一”為風景園林專業的總綱是完全正確的,但是“天人合一”觀不應僅僅在中國文化自身體系中審視,而應以跨文化人類學的視角用文化比較的方法加以研究和闡述,才能建立起與其他文明溝通的平臺,避免走入自說自話的窠臼,或者使其淪為一句空洞的口號。
疫情當下幾乎足不出戶的生活,給人們帶來了大量的時間去感受與思考。人們的生活方式、消費方式、交往方式和工作方式都在發生著快速的改變。在虛擬社交、遠程辦公、云購物成為日常的宅居式云生活中,人們擁有了難得的機會去思考一直在回避的人與自我、人與社會、人與自然的基本關系,重新回答“我是誰?我從哪里來?我到哪里去?”的人生三問。疫情到來的當下正是人工智能開始走入人們生活的時候。假如人們仍然不能回答這些最基本的問題,人工智能在未來造成的麻煩甚至災難會比這次疫情難處理百倍千倍。無論疫情是否到來,人類都無可避免地走入了實體世界與虛擬世界共存的時代。筆者曾在1年前的一次演講中預估10年后的設計行業,認為那時至少有一半以上的業務不再是實體環境的營造,而是以虛擬環境營造為主要經營方向。如今這次疫情極有可能會讓這個時間大大提前。而中國傳統園林的一大特征正是在于打造由實體世界延伸出的虛擬體驗,這樣的傳統在未來的世界中必然能帶來更多的機遇。
6 結語與展望
這次的疫情為人類敲響了警鐘。無論是在過去還是當下,流行病的發生和蔓延都進一步促使了社會價值觀與人們生活方式的反思。歷史上的幾次公共衛生與環境事件讓當時的城市設計者開始重新反思城市與自然的關系,思考室外公共空間對于密集人口居住大都市的重要性。當今新冠病毒肺炎疫情推動人們對于以人行、自然系統為城市第一系統的需求。面對這些轉變,風景園林需要迎接疫情帶來的挑戰,直面未來行業需求與當今行業問題,轉危為機,構建以“天人合一”為總綱,以人的物質與精神需求為主要服務對象,以豎向設計為核心技術進行多專業整合設計的風景園林核心體系。風景園林師必須統籌思考社會變化所帶來的世界逆全球化、個體天人關系等前瞻性問題,促使未來城市結構的健康轉變,在未來社會發展中承擔起風景園林專業應該承擔的歷史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