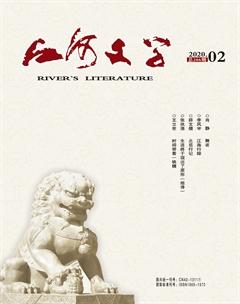屈原小學
周凌云
我來到屈原小學時,正是課間操時間,學生們并沒有做體操,而是在操場上集體朗誦《橘頌》,約七、八十個孩子,一半站在操場,一半站在操場和教學樓之間的階梯上。孩子們沒有校服,穿戴不一,但色彩斑斕。一個學生拿著話筒,站在臺階上的旗桿下,領誦。這個孩子在同齡人中長得稍高點,形象帥氣。
我站在屈原小學的教學樓上遠眺,屈原廟和那棵高大的黃楝樹清晰可見,陽光撒在一面坡上,明亮、神圣而又溫暖,感覺詩和遠方都在那里,一個偉大的詩人誕生于這個村子,讓我們感到自豪。
一九九四年的屈原小學,還是土房子,四百多名學生。一個偶然的機緣,學校徹底變樣了。葛洲壩電廠要在全國援建三所希望小學,其中一所就定在屈原的家鄉。這是一份文化情懷,是對這片土地的厚愛。于是,幾棟歪歪扭扭的土房子建成了高大洋氣的樓房。還配備了現代化的教學資源:辦公桌椅、書桌和文具、學生食堂不銹鋼餐桌、電腦信息室、圖書室、閱覽室,圖書,樣樣俱全,學校還設立了學習成績獎和園丁教學獎等。
學校的食堂,窗明幾凈,清清爽爽。食堂每天每頓都將挑撿菜樣貯存,以備有關部門檢驗,是否合乎衛生標準。餐廳柜子里,學生們的餐具擺放有序。
學生宿舍,被子疊成四方,毛巾色彩各異,一條一條,排列垂掛。一年級和學前班的孩子做得稍差一點。清潔衛生和一切整理都由學生自己來做,老師只來檢查。這種整齊化一,也許只在軍隊才會看到。我真羨慕現在的孩子,生活在一個好時代。我小時候上學,沒有這般幸運,每天早早起床,去學校要跑一個小時山路,中午也沒有午餐,課堂上常常餓得無精打采,讀書沒有正式課本,學習的東西零零碎碎。
良好的習慣是嚴格教育和訓練出來的。我認識學校保育員易素文,五十多歲了,瘦瘦的。她的工作是教孩子們學會洗臉、洗澡、刷牙,學穿衣脫衣疊被子,教孩子們把鞋子放整齊,把毛巾掛好。易素文做保育員已十八年了,當年哭哭鬧鬧的孩子,現在已經長大成人,他們回到村里,最想看望的是易老師,這是他們心中永遠抹不去的形象,是他們共同的媽媽。一個孩子在最需要愛的時候,是她給了溫暖。
寄宿制,是偏僻山村特有的辦學模式。以前,村村有小學,現在農村孩子減少了,幾個村才有一個中心小學。也有的一個鎮才有一到兩所小學。交通不便,上學又遠,只能讓學生寄宿,對于學校和學生來說,都是無奈的選擇。
有的家長把學生放到學校寄宿,并不放心,怕委屈了孩子,把山上的家什搬下山,租房陪讀,為孩子做飯、洗衣、陪住,讓孩子感覺有家庭的溫馨。
我向校長提出想去圖書室和閱覽室看看。
圖書室共有六千多冊,有些散亂,好像正在清理。各類書都有,但是關于屈原文化方面的少。全校學生不多,圖書卻汗牛充棟。只要愿讀,有的是書。不知孩子們是否常常來借。
學校的課外活動也曾搞得紅紅火火。在各年級中開設過“楚辭”課,讓低年級背名句、中年級背名段、高年級背名篇,讓每個學生會講屈原的故事,把屈原的詩改成課本劇,孩子們都爭著扮演屈原。老校長譚國粹能作詩會寫文章,他編屈原的故事,徐宏沂書法底子好,負責寫字,郝光舉畫畫不錯,做插圖……把屈原的事跡和詩句制成一幅幅掛圖,為了長久使用,不致損壞,將掛圖又覆上薄膜,然后將這些張掛圖連綴成長卷。每當課外活動,老師們將長卷抬出來,在校園墻面上鋪排開去,一節課時間剛好從頭講到尾。孩子們都喜歡這樣的課。了解了屈原、理解了詩句。每個班每周也輪流去屈原廟聽騷壇詩人徐正端講課。徐正端在屈原小學教過書,退休后就一直呆在屈原廟,研究屈原,寫詩。
老師們也帶孩子們去參觀照面井、讀書洞和玉米三丘。村里的每個景點,都有屈原的傳說,在現場老師們稍加引導,學生們就能把故事銘記在心。譚國粹還將全體老師和學生帶往葛洲壩電廠參觀,與電廠子弟學校一起開展教學活動,讓農村和城里的孩子手拉手,農村的孩子講屈原的故事、背屈原的詩句,講農村生活的艱難,城里的孩子講城里的見聞,說一些讓農村孩子感到新奇的事情,相互都學到了東西。
譚國粹的父親曾是這所學生的老師,父親教了三十多年的書,退休那年,譚國粹便走進了屈原小學,接過了父親的粉筆頭兒。如今,譚國粹快到退休年齡,從校長的位置上退下已有幾年了,只教一門課,一天也只講一節課,感到輕松,也有了讀書的時間。他說,他研究戰國的歷史,也把《楚辭》放在手邊,讀讀背背,對于屈原和那個時代研究不深,但要盡多的掌握一些,多學一點,就能多向學生灌輸一些。
我翻了翻他的讀書筆記,紅墨水、藍墨水抄錄得滿滿的,都是關于屈原以及詩詞格律等有關的知識。他還參照別人翻譯《楚辭》的內容,把艱深的屈原翻譯成通俗易懂的詩句。
其中有一首他寫的詩:
端陽小雨綿綿降
故里溪流嘩嘩響
詩人墨客皆拭淚
悼念戰國好棟梁
詩讀起來平平,但表達的感情深深。
我離開學校的時候,學生們稚嫩的聲音,朗誦《橘頌》的詩句,還留在我耳邊。
責任編輯:邱紅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