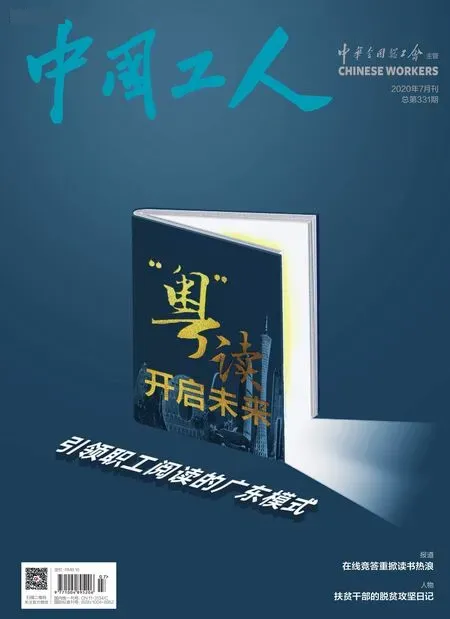我當年的“干糧”
前段時間,女兒的超長寒假終于結束,要回到千里之外的學校上學。出發前,我的父母悄悄地把一大堆零食塞進行李箱,沒想到還是被孫女發現了。這個少帶點,那個不帶,望著他們“討價還價”的樣子,我想起了自己當年開學時的情形。
當年,我開學的前幾天家里最熱鬧,像置辦年貨一樣,忙著為我準備一個學期的干糧。干糧是用鍋巴加工而成,是家里的存貨以及從鄉親那兒淘換來的。
開學前幾天,奶奶會挑個晴天,讓我和哥哥把存放鍋巴的草席簍子抬到院子里,攤開“出風”。奶奶搬個小竹椅子,戴上老花鏡,把焦糊的渣子挑出來,放在小碗里,留著給小雞加餐。她經常是揀著揀著就睡著了,你要是說讓她到床上睡,準會挨罵:“瞎講!誰睡著了?!找打吧!”奶奶說著揚起手就要打人,惹得我們捂嘴偷笑。
晾曬到傍晚時分,我們把鍋巴攏成兩堆,奶奶站在院子中間,給大家分工派活兒,誰去搗石窩,誰去篩篩子,家里十來口人,個個被使喚得團團轉。

搗石窩是體力活兒,最累,要用石臼把鍋巴搗碎,我爸爸和我哥力氣大,那些年都是他倆承包的。我媽和我姐過篩子,我姐把搗碎的鍋巴從石臼里舀出來放到篩子上,我媽負責篩。那時候,還沒有細鹽,食用鹽都是指甲蓋大小的粗鹽粒子,爺爺和我叔他們要先把鹽粒放在鍋里炒一會兒,再用小石臼把鹽粒搗碎。我領著弟弟妹妹們給眾人打下手,哪邊需要搭把手,哪邊需要取個碗拿個盆,保證隨叫隨到,跑前忙后不停歇。
奶奶沒有具體的活兒,卻比誰都忙。她老人家身兼數職,既抓全局,又要顧質量細節,還得監督,看有沒有偷工減料,屋里屋外來回穿梭。爺爺性子慢,做起事來慢條斯理,急脾氣的奶奶嫌爺爺“磨嘰”,爺爺挨批評的次數自然也就最多。爺爺為息事寧人,不吭聲,偶爾辯解兩聲,只要奶奶喊一聲“想造反?”便低頭不語。不過,有外人在場的話,奶奶絕對給爺爺面子,爺爺的話就是“圣旨”,奶奶說話也是低聲細語,爺爺常說他盼著家里天天來客人。
最后一道工序是加鹽和裝袋。也是奶奶親自上陣,要忙上一個多小時,先用大桿秤把鍋巴面分成3堆,再拿小桿秤稱好鹽。放入鹽攪拌均勻,然后再裝進布口袋里。后來,奶奶又創新出加芝麻和糖的“香甜味”,一咸一甜兩種味道,工作量也翻了一倍。
我上學時有一個專用的小竹扁擔,一頭挑著行李,另一頭則是一大袋鍋巴面。那時,我十七八歲,吃得多餓得快,還沒到飯點肚子就咕咕叫,就得靠鍋巴面來墊肚子。特別是下晚自習時,舀上半碗放在大搪瓷茶缸里,澆上開水,舍友們便聞香而至。
僧多粥少,一大袋鍋巴面不到一個月便見底了,舍友們慫恿我寫信回家報告。半個月后,父親來開會,用扁擔挑來兩大袋。聽家人說,奶奶和爺爺推著獨輪車跑了兩個村子,用米換人家的鍋巴,還央求人家把鍋巴留著,他們還要來換。
后來,晚上沖鍋巴面成了我們宿舍的幸福時光,一直保留到我們畢業離校。直到現在同學聚會時,大伙還饞著那個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