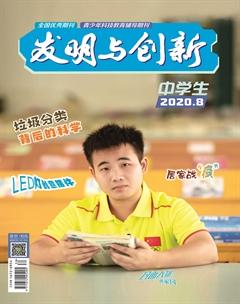揭開河洛古國的面紗
位于黃河與洛河交匯流域的河洛地區,古有“居天下之中”的說法,向來被視為中華文明的腹心地帶。經過連續多年的考古發掘,5月7日,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公布了位于河南省鞏義市河洛鎮的雙槐樹古國時代都邑遺址階段性重大考古成果,確認其是距今5 300年前后的仰韶文化中晚期巨型聚落遺址,專家建議將其命名為“河洛古國”。
雙槐樹遺址位于黃河南岸以南2公里、伊洛河以東4公里,處于河洛文化中心區,遺址面積達117萬平方米,發現有仰韶文化中晚階段三重大型環壕、封閉式排狀布局的大型中心居址、三處經過嚴格規劃的大型公共墓地、三處夯土祭祀臺遺跡等,并出土了一大批仰韶文化時期的文化遺物。
以往國內大部分學者雖然肯定中原地區在中華文明起源中的地位和作用,但認為中原的中心地位是從夏代才開始形成的,并不贊同更早的時候也具有中心地位,河洛古國的發現可能改變這一認知。
“雙槐樹遺址發掘的意義在于,實證了在距今5 300年前后這一中華文明起源的黃金階段,河洛地區是當時最具代表性和影響力的文明中心。”中國考古學會理事長王巍表示,在這一階段,中國的文化已經形成雛形,以雙槐樹遺址為中心的仰韶文化中晚期文明是黃河文化之根,堪稱“早期中華文明的胚胎”。
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長顧萬發曾三次擔任雙槐樹遺址發掘領隊,他一直注重對天文、祭祀、宗教、禮制等“形而上”遺跡現象的研究。
在雙槐樹遺址的中心居址區內,有一處用九個陶罐擺放成北斗星形狀的天文遺跡。陶罐被埋在土中,只露出一小部分,考古人員逐一貼上了數字標號。
“北斗九星遺跡有政治禮儀功能,主人借此神化自己,表達自己是呼應天上中心的地下王者,也表明當時人們已經具有相對成熟的‘天象授時觀,用以觀察節氣、指導農業。”顧萬發概括道。
遺址的中心居址區可以理解為貴族居住的區域,在居址區的南部,兩道370多米長的圍墻與北部內壕合圍形成了一個18 000多平方米的半月形結構,尤其是圍墻東端的造型,被專家視為中國最早甕城的雛形。
甕城是古代城市的主要防御設施之一,通常是在城門外或內側修建的半圓形或方形的護門小城。河洛古國的中心居址區已有典型的甕城建筑結構,可見居住者的地位非同一般。
在河洛古國遺址,考古人員還發現了中國最早的骨質蠶雕藝術品。這件藝術品長6.4厘米,寬不足1厘米,厚0.1厘米,用野豬獠牙雕刻而成,是一條正在吐絲的家蠶形象。它與青臺遺址等周邊同時期遺址出土的絲綢實物一起,證實了5 300年前后黃河中游地區的先民們已經養蠶繅絲。
“絲綢和玉都是中華文明的高端代表,關于玉的研究和發現有很多,絲綢卻較少有人關注。”顧萬發說,絲綢這種“高科技”產物的產生,一定有相應的社會理念和人力、物力、財力做支撐,背后肯定有更高端的文明存在,如果找到了,所謂“中原文明洼地”的問題就解決了。
正是在這種理念的驅使下,自2013年起,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聯合中國絲綢博物館開展了“尋找中國絲綢之源——鄭州地區仰韶時代中晚期考古學文化面貌與文明起源問題研究”考古發掘項目,對鄭州周邊相關遺址進行全面的調查勘探與考古發掘工作。
隨著河南滎陽的汪溝遺址、青臺遺址,鄭州西南郊區的黃崗寺遺址,鞏義雙槐樹遺址等一系列仰韶文化城址被發現,一個具有早期城市群性質的大型聚落集團的面貌逐漸清晰,形成了黃帝時期中華文明起源的重要核心地區。(據《中央紀委國家監委機關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