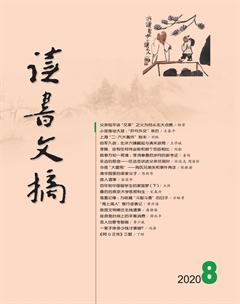編后
歐陽文清
《宋書·索虜傳》曾記載:索頭虜姓托跋(拓跋)氏,其先漢將李陵后也。陵降匈奴,有數百千種,各立名號,索頭亦其一也。2009年,《北京青年報》曾有過一篇文章,其中說到:公元648年,一支來自唐朝西北數千里、今俄羅斯葉尼塞河上游地區的黠戛斯朝貢團,他們自稱是李陵的后裔,與唐朝皇帝同宗,是來“認親”的。這些記載與“李陵事件”一樣,要厘清其中歷史的迷霧實在不易,值當是枯燥中使人生津的甜梅罷。不過,李陵卻不曾想到,他會在某種程度上被后人視為民族融合的文化符號。
有一點是肯定的,那就是漢武帝對待“叛將”李陵的態度,直至最后舉家抄斬!漢武光耀歷史,向來褒多于貶。可硬幣皆有兩面,空前集權,罷黜百家,漢武一朝,特權二字展現得淋漓盡致。普天之下,莫非皇土,遑談一個小小的臣子!
特權像一個不知生年的娃娃,同時又是個沒有卒年的老人,只要人類繼續繁衍,生活中無時無刻你都能感受到它的存在。有些人醫院不用排隊掛號,有些人搖車號、搖學位一搖就中,皆是特權在時下的詮釋。但我實不愿將它看作貶義,更偏向于把它認作一個中性詞語。亞里士多德在他的著作《政治學》中,強烈支持那些支撐著社會不平等的各種基本的社會制度,他不僅捍衛私有財產制度,甚至支持奴隸制。亞氏觀點自有其歷史局限性,但每個人能力有大小,在社會中肩負著不同的社會責任,那么責任大的被賦予一些特權,進而便于創造更大的社會效益,為更多人服務不是很正常的嗎?只是特權絕不應濫用,雖然這個度十分難以把握。
今年武漢經歷新冠疫情初期,曾有一則報道是關于一輛掛著公車號牌的車輛,從武漢市紅十字會倉庫領走了一箱當時連醫務工作者都急缺的“N95口罩”。可時至今日,這一十分需要公開化、透明化的特權行事,卻始終不見詳細的、讓人信服的說法,那些被領走的口罩最終也不知到底遮掩了誰的口鼻?
更早些時還有一位“空姐”,開車進入故宮,在太和門廣場各種自拍,而后自豪曬圖;行使了連前法國總統奧朗德都不曾擁有的特權,一夜成名。同樣,大眾沒有得到任何關于處理這則事件相關責任人的說明,女主人公“人間蒸發”,隨著她一同“蒸發”的還有根本就不曾露面的賦予她特權的人。當特權被濫用,相關監管部門絕不能與濫用者沆瀣一氣,我始終相信正義僅僅是遲到而已,絕不會“蒸發”!
《百年前中國留學生的家國夢》中的話令我印象深刻:庚款留學生深知自己在異國的吃穿用度皆民脂民膏,如不……學到更先進的知識,實在有愧于國家和同胞。心中真真十分感奮,在那個年代,那批留學生是擁有“特權”的,而他們很好地利用了它,毫無浪費,最終轉化為報國之力。
最后我想說個酸酸的故事,聊備諸君一笑。疫情甫一襲來時,各行各業多少有些無措,菜籃子曾有過短暫的失控:我買過六元一個的土豆,十二元七八個的青椒;后來解禁,我于某局級單位家屬院內,親眼所見被整個扔在垃圾桶的足有一米左右的冬瓜和整編織袋的土豆,據說這些都是之前地市縣的兄弟單位對口援助處于困境中的“老大哥”的。這個特權即使顯得有些委屈和被動,卻還是讓人覺得十分不公。我想,在“特殊時期”見到的這件事會停留在我的記憶中,許多年都不會忘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