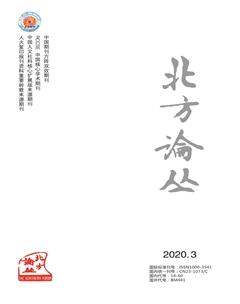歷史責任、歷史理性與史學職業化
尉佩云
[關鍵詞]歷史責任 歷史理性 歷史正義 歷史倫理
一、歷史責任與職業化
歷史職業化研究已經一個多世紀的今天,我們的研究和寫作是在一套完全規范和技藝性的評價體系中進行的。甚至,歷史學家也不再強調倫理責任,而是像馬克斯·韋伯所說的“價值無涉”——我們僅僅能夠提供的是關于人類過去的知識。這些知識的可靠性和敘事的美學價值成為評價和核心標準。因而,在實踐的歷史研究領域,對歷史研究關于過去的“真相”的追尋,對史料的可靠性、文本的敘事結構更加強調,如敘事主義歷史哲學所呈現給我們的那樣。正如德國史學理論家約恩·呂森所言,歷史研究是一門遠遠比尋求真相要復雜的學科,甚至歷史學的重要成就往往是在“事實”和“虛構”的二分法之外而產生的,因為“尋求真相”那不過是“傳統的有限的實證論”而已。
像呂森提示我們的,我們作為歷史學家不能夠后發地像法官一樣地決定過去的價值和倫理責任。在命運的因果性鏈條之中,我們承擔著過去、我們的行動將決定著未來,所有歷史的張力都集中在“現在的我們”的身上。現今歷史研究的趨勢使得,一套完整的、具有相當美學價值的敘事體系成為歷史學家成功的標志。材料的編制、語言的結構、敘事的風格的運用之精巧純熟,是歷史學家必備的功能——但是我們現在似乎對這些隱性因素的成分放在前所未有的高度。不過歷史地來看,歷史的審美化和話語體系的生產造就了歷史學家的封閉性,我們對真實的過往歷史慘痛之真切、我們對與我們生活息息相關的時代性、我們所肩負的對未來后輩人的倫理責任都統統喪失了,將自己封閉在時代性和歷史性之外不斷制造著關于過去的話語體系。當然,就我們的時代性而言,像呂森所言是過于沉悶而又保守的,這是歷史審美化和技藝性導向的一個促成因素。
阿爾貝·加繆在1957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他在名為《寫作的光榮》的致辭中說:“今天的作家不應為制造歷史的人服務,而要為承受歷史的人服務;否則,他將形影相吊,遠離真正的藝術。”這句話所表達的意思在歷史學家身上也是適用的:今天的歷史學家不應為制造歷史的人服務,而要為承受歷史的人服務;否則,他將形影相吊,遠離真正的歷史。那些在過去和現在為超出個人應有承受界限的歷史的重負而努力過和正在努力的人,那些歷史中隨黃土淹沒的人,那些無辜的殉葬者,我們縱然不能留下每個傳記,也應當像朗茲曼所說的要留下一個“永遠不會除去的名”。
在今天的歷史研究中,設立“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的道德責任是困難的,甚至有淪為堂吉訶德的危險。每個時代總有一些堅硬的文字,就像陳寅恪所道出的“吾儕所學關天意”“文章存佚關興廢”。這樣,我們才能為我們的研究工作尋得一個深層意義的“根”。這個“根”伸展到過去,延伸到未來,這個文化和意義之“根”作為我們精神結構和歷史意識的一部分重新連接在歷史中。我們所做的,就是期望經由這個“根”長出的未來之樹能為我們的后輩人遮陰避雨,我們由此也延伸到了未來。
“現在的我們”在邏輯上永遠是緊張的、吃力的、具有重負的,因為“沉重的過去”已經成為“歷史”肩負在我們身上,而未來時間的導向走向何方也是緊系在“現在的我們”手中。所以,不論事實經驗地還是倫理地來看,“我們”是永遠處于過去與未來之間的張力中。因而,一方面,我們為過去所塑造;另一方面,我們被未來所期待。在過去、現在、未來的關系中,時間、事件、事實、經驗、精神、意識等所有的一切綜合體橫亙在其中,這使得過去可以被認識,未來可以被期待,這個溝通過去、現在、未來的時間三維的形而上的扭結被呂森稱為“精神軀干”。“精神軀干”是呂森是描述代際關系時所使用的一個詞,在更廣的意義上和他所使用的“精神通道”并無二致。“精神軀干”可以被視為呂森所謂的“跨主體性”的歷史思考的凝結物——跨主體性在代際關系中的擴展就是一個形而上的“精神軀干”的形成和外化。呂森認為,“精神軀干”具有超時間的特性而存在,這也是代際責任倫理和歷史責任倫理形成的先決條件。我們做進一步思考,不管是邏輯地還是經驗事實地看,“精神軀干”所承擔的一切負擔最后都負載在“現在的我們”身上——邏輯地看,“現在的我們”具有的歷史意識識別、認知、范疇化地將自己定位為過去和未來的承接點,這是一切歷史思考的基礎,甚至是歷史存在的基礎;事實經驗地看,只有“現在的我們”才有歷史認同和集體認同的生存需求。過去不復存在,未來還未到來,只有“現在的我們”將自身詮釋為“歷史的”,將自己的生活詮釋為過去的時間在我們身上的延續。甚至,樸素地,我們能夠想象我們“持據”著時間從源頭到現在的韁繩——這根“時間之韁”讓現在的我們總是精神緊張、惴惴不安而又不知所從。
既然“現在的我們”永遠處在過去和未來之間的張力之中,那么我們如何來看待作為“現在的我們”中一個范疇的歷史學家的責任?歷史寫作在現代社會的倫理機制和文化背景中是不是已經蛻變為一門系統的專業技能要求?我們現在如何處理歷史寫作背后更深層次的倫理意義和承擔的道德責任?
而對于現實經驗的歷史創傷而言,就像納粹大屠殺一樣,上述的這些詰問會如夢幻泡影般破滅。這些沉重的歷史對于接受其群體認同的個體而言,是活生生的、真切的,這些歷史就像一汪清泉或一團烈火,當它流過我們的皮膚,若不是清涼的快感就是灼心的痛徹。這清泉或烈火并不是憑空而來,而是從過去一直流到現在,或者從過去一直灼燒到現在,在“現在的我們”的手中,我們將決定是將清泉留給我們的子孫后代還是讓烈火繼續燃燒。處在時間關聯和代際鏈條中的我們,面對過去、現在和未來時,有些責問是無法回避的:我們該怎么做?由此,歷史學家的責任倫理就產生了。
首先,我們對現在負有責任。英國左翼作家喬治·奧威爾在《1984》中說:“誰掌握現在,誰就掌握過去。”當然這個命題一般被當作一個宏大敘事來解讀。同時也說明,歷史作為現在文化生活導向的一部分,作為現代的歷史學家而言,一旦我們從事研究,我們就要為我們回憶過去的方式(包括到導向性、經驗的真確性、精神傳遞等)和由此而來的現在的文化生活和現狀負責。并且,就作為集體認同的主要手段和個體面對偶然經驗的思想解讀而言,這是就是為何教科書和國民教育在現代民族國家中占有如此重要地位的原因。對過去的詮釋、對現在的解讀和對未來的期待在歷史思想的理解中成為歷史認同的主要手段,歷史學家將過去的經驗帶到現在、開啟未來視角的過程中,將現在的個體和集體認同保持在一個平衡的關系中。所以,歷史地看,我們選擇成為自己,我們對自己的現在負有責任——所以,個體倫理并沒有伏爾泰所說的雪崩時的雪花一樣輕松。
其次,我們對未來負有責任。在一個世代鏈條中,我們手中持據著的“時間之韁”將決定后輩人的歷史和生活狀況。宿命論地,如果我們將過去視為未來封閉的宿命,以至于未來可能在現有的條件和基礎上悄然而至的話,這就是非責任的,也就脫去了道德重負的外衣。歷史決定論(規律論)或者波普爾意義上的歷史主義論調將過去、現在、未來的時間聯系斬斷,并且,封閉了過去之中還有的未來導向性的潛能。所以脫掉現在的道德責任,我們既脫掉了我們本身的認同,也放棄了未來的開放性可能。這就像呂森所說的:“當然,最不可能出現的情況是未被預想的未來的沉默,這樣將我們的行動從中剔除出去,我們在未來中走向終結。當后來出生的人為了成為他們自己,而與我們詮釋性地發生關聯時,我們的沉默會斷送他們。”
再次,我們對過去負有責任。我們從已發生之事、成為事實和經驗的時間過程中能發現什么呢?對過去負責似乎是不合邏輯的。而呂森則認為,現在的價值體系和過去人類的作為和不作為的價值準則有著內在的聯系。我們為我們的祖先而驕傲,我們保護傳統,這說明在現在的生活形式中過去的價值體系始終被認為是有效的。過去一直延伸到現在的價值體系中,那些在這些價值體系中生活的人們,覺得自己對過去是負有責任的,而過去鮮活地存在于現在的生活中(當然,這個觀點在德國思想史中有長久的淵源。德羅伊森、狄爾泰、胡塞爾都做過詮釋,體現在他們對“生活世界”的強調)。更加明顯的是,呂森在論述歷史意義的“不可預想性”時對這個倫理責任的強調:意義的發生是具有“不可預想性”的,一件歷史事件發生之后它自身的意義會隨之出現,成為現在生活的一部分,歷史意義絕不是像后現代歷史理論家所認為的那樣作為“后見之明”而存在。那么,在呂森的邏輯中,過去并不是僵硬的事實,而是過去的事實贏得了作為現在真實生活的前提因素自我彰顯在現在的生活中——過去是流動的。
當“現在的我們”想關涉探尋過去的倫理責任時,過去就被“激活”,過去的經驗事實被“融化”——過去的事實不再是如硬核般僵硬地存在于無邊無垠的時間荒野中,而是隨著現在的時間之流進入現在,以至于凝結為歷史意義的形式塑造、影響著現在的生活。在這個意義上,呂森的“意義”和魯尼亞的“在場”具有極大的相似性。呂森將這種“流動的過去”更加具體地解釋為:“過去不是固定的事實,因為在過去本身活動的、受難的人類總是將過去置于一個時間運動中。在其中或大或小的代際集體的精神關聯中,這一時間運動一直延伸到我們身上。更具體說:它穿過我們到達我們主體性的深處,它穿過我們直到我們為自己的行動而設定的具有確定意義的未來之中。”
顯然,這是非常黑格爾式的“命運的因果性”的論述。在呂森的“流動”中,不僅過去的經驗事實進入現在,而且相應的倫理價值也進入現在。與此相反的情況是,如果我們將過去以及由過去所決定的現在視為是歷史不可避免的“命運之果”;或者認為,相對于后發的歷史學家的評價,過去本身是沒有意義的。由此,歷史和歷史研究的道德責任就消失了,一方面消失于被切斷的“命運的因果性”之中,另一方面,消失于對過去純粹的事實的堆積中。對于前一種情況,呂森認為我們要借助非歷史主義的思考,“歷史”本身體現著過去到現在的時間的發展,在“歷史”中它將過去的行動和受難與現在的行動和受難聯系在一起,使之統一為一個跨時間的主體性,在時代的變遷中將兩種價值連接成一個規范性和強制性的統一體。由此,過去和現在的“命運因果”重新勾連了起來。對于后一種情況而言,我們必須撥開后發的歷史學家賦予歷史意義的迷霧,從而“將過去還給過去”,將過去的那些行動者和受難者以及他們的價值返還給他們本身,使那些過去的死難者、殉葬者、無辜的人得到尊重。
最后,我們將歷史主義的和非歷史主義的歷史倫理結合起來,在“命運的因果性”和“跨主體性”中,既考慮過去死難者的價值體系,又考慮到現在的價值體系及歷史學家的評判體系,將二者平等對待并使之處于內在動態的聯系之中——這樣,我們就能給過去的死難者一個“永遠不會除去的名”,也能夠從現在出發來克服過去的錯誤和災難,或者像呂森所說的“治療”或者“治愈”歷史的創傷。
二、歷史理性與歷史正義
齊格蒙·鮑曼在其《現代性與大屠殺》中將納粹大屠殺定義為現代性本身的產物:科學理性的計算精神、技術的道德中立地位、社會管理的工程化趨勢——在集中營中毒氣室每小時能殺多少人,每天火車能夠運來多少人,而又能處理多少尸體都是經過精密的計算和衡量的。而這導致的結果是,在大屠殺結束后那些甚至在集中營中的納粹軍官聲稱自己并不為這些死難者負責,因為自己只是一個技術官僚和命令的執行者。人類理性精神乘著現代性的列車加速前進,甚至在種族滅絕中可以道德中立地將理性精神展現得淋漓盡致。所以后現代主義在面對現代性時,反思理性和批判理性也成為一個主要的理論標的。
但是,在另一方面,康德所謂的啟蒙就是“脫離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狀態。不成熟狀態就是不經別人的引導,就對運用自己的理智無能為力”。隨著啟蒙運動的進行,人類開始脫離不成熟狀態,能夠自由自主地運用自己的理智。而且隨著啟蒙而來的人類精神財富——人文主義的傳統中,理性一直居于中心的地位。理性的覺醒對人的本身價值的強調、對人生幸福的追求、對平等的捍衛、對于人類受難的關懷、對普世性的人類受難的同情和理解等都是“人之為人”的本質所在。甚至,在理性遭遇大屠殺等極端割裂性經驗的挑戰之后,呂森等歷史哲學家為何還一再強調理性的重要性?這樣來看豈不是人類精神的分裂癥?
人類的理性精神一方面成就了大屠殺,另一方面,我們還需要理性。特別是呂森對歷史理性的強調,是因為它在我們面對人類歷史上的極端的歷史經驗時,無論在個人情感層面,還是在學術研究層面,抑或是在整個人類的反思與歷史進程層面,我們都需要理性地面對過去,治愈個體性或集體性的歷史或心理創傷。另外,歷史理性與歷史連續性和歷史意義緊密聯系在一起,歷史理性是歷史連續性和歷史意義的思想源泉,而歷史連續性和歷史意義以及歷史人文關懷的主要實現方式——我們將那些慘烈的故事通過歷史敘事、時間順序的排布,將其講述為一個連續性的人類故事,使那些斷裂的、創傷的歷史經驗成為具有歷史意義攜帶的故事形式。
或許我們認為這種理性的兩面性帶來的人類精神分離是關于不同的“理性”概念本身的內涵的爭論——在納粹大屠殺中的理性和人文主義中的理性概念范疇的界定是不一樣的。對于人類思想史或者人類思想發展本身而言,“別開生面”地將理性剝離開來,一方面用于納粹大屠殺等負面經驗,另一方面,用于人的價值和尊嚴等正面經驗的情況,是不可能也不合邏輯的。本質上來看,理性的精神分離的爭論其實不是關于“理性”這個概念本身內涵的爭論,而是人類運用理性的訴求和限度。如果我們一直糾纏于理性概念本身的討論,一方面我們只會陷入“唯名論”的陷阱;另一方面,我們放棄了問題的本質,即理性概念背后人類真實的活動和相應的后果,而這才是理性問題的價值本源。所以,對于理性的爭論本質上是關于人類理性的訴求導向性和理性限度的爭論。我們不能將作為人類本質特征的理性和智性運用于“惡”的方面,造就“罪惡”的歷史,就像納粹大屠殺等負面經驗中的理性一樣;而是將其導向“善”的方面,造就人類未來關于人性榮光的歷史。當然,這不是一種單純幼稚的人類歷史樂觀進步論的展現,而正是由于理性的兩面性,我們永遠無法單純地投入歷史樂觀進步論的懷抱而罔顧其余。而歷史理性作為人性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們也不可能將它從我們自身中分離出去。所以,可能人類步人自由王國和理性的“最后一幕”永遠不會上演,而關于人類理性和人類的思想解放事業是一場世世代代都要重新開始的戰斗。
對于寫作的歷史學家而言,歷史寫作本身包含倫理道德的維度,譬如,“一字之褒,榮于華袞;一字之貶,嚴于斧鉞”“誅奸諛于既死,發潛德之幽光”的至高水準。歷史學家用自身的道德價值體系和過去的道德價值體系結合起來,既給予過去死去的人以其應有的價值尊重,也對過去那些不該發生的罹難者用后發的價值標準來進行校正,為其正名。在更大的范疇中,寫作的歷史學家將斷裂的、危機的、非連續的歷史事件通過歷史敘事將其排布起來,形成歷史的連續性,從而講述一個雋永的人類故事。在歷史意義喪失其原始信任之后,元理性的統一體也隨之坍塌,歷史文化概念興起。歷史文化將歷史和歷史研究整體性地置于一個現代社會的文化系統中來考察其文化價值和關聯性。那么,歷史寫作所形成的雋永的人類故事就成為現代歷史意義的替代性方案,由此歷史寫作成為現代社會文化資源的重要構成。在此基礎上,一方面歷史成為構建集體認同和歷史認同的主要手段;另一方面,那些在時間長河中其他的人類受難經歷和無辜的死難者的經歷,在作為文化資源的歷史中總能找到慰藉,或者說找到一個對于受難經歷的詮釋性的“文化借口”。
這個歷史的詮釋性的“文化借口”讓人類的受難經驗和悲慘故事具有了文化的“合理性”解釋——我們不能辨別這種“合理性”是來自文化系統本身的價值還是歷史親歷者在自我的精神結構和意識構圖中后發地“自我關聯”上去,抑或二者皆有。由此使人類的那些荒涼的、無垠的、散漫的、無以名狀的、被壓制的、屈辱的經歷有了一個文化的“出口”或“出路”,這個文化“出路”將人類悲傷和被壓抑的情緒宣泄出來,個體或者集體地找到了一個方向感和歸屬感。比如,對于納粹大屠殺中的猶太人而言,站在個體的歷時性的生活經歷角度來看,他們根本不明白為何會被趕上火車、會被推進毒氣室、會成為人類現代帝國迷夢的陪葬品。幸存下來的猶太人也根本無法面對自己后來的生活,這就是為何在朗茲曼的著名紀錄片《浩劫》中,當朗茲曼請求那些猶太人幸存者講述那一段經歷時,有的人一語不發而眼淚橫流,他在文化上或是現實的生活經歷中無法找到這個事件發生的“合理性解釋”,即使是一個負面的解釋也沒有。所以,猶太詩人奈莉·薩克斯的詩歌才哀悼:“世界啊/不要詢問那些死里逃生的人/他們將前往何處/他們始終向墳墓邁進。”
這種創傷性體驗在文化上是沒有任何的“出路”的——甚至都不能用簡單的“好”與“壞”來評價他們所遭遇的一切。而歷史和歷史研究則將大屠殺置于一個文化網絡之中,盡管大屠殺作為“意義的黑洞”或“文明的斷裂”,我們依然無法將其“正常化”(“意義的黑洞”本身也是一個文化性解釋而存在),但是可以為他們所遭受的無以名狀的痛苦找到文化性解釋。歷史學家將大屠殺解釋為納粹力圖建立起現代德意志帝國的政治手段,將其解釋為歷史上一直存在的以基督教為傳統的歐洲對猶太人的敵視,將其解釋為現代性和理性變異的產物(齊格蒙·鮑曼便是如此)。所有的這些文化性解釋將納粹大屠殺變得可以理解、可以在文化上找到一個位置,甚至我們將其作為學術研究的對象而進行詮釋也是其中的一個方式。在歷史學家關乎未來的文化中,他們將納粹大屠殺描述為恐怖的人類經驗,從深層的文化中剖析其形成機制和文化元素,從而盡力避免此類事件再次的發生。在未來的文化導向上,德國歷史學家從一開始就在為此做準備,他們在塑造一個民主和和平的文化價值導向以滅絕納粹大屠殺的文化根源。當這種文化導向擴展到公共話語體系中和政治領域的時候,歷史學家的道德責任也就實現了(當他們開始做出這個導向判斷時,個體性的道德價值已經實現)。
這就是為何在德國納粹統治結束后迄今為止的時期里,德國歷史學家在公共話語體系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甚至影響著當代德國政府的政治導向(“歷史學家之爭”和“戈德哈根”之爭在公共話語體系中的影響力就是最好的例證)。德國歷史學家揚·阿斯曼在陳述他為何走向文化記憶的研究時就說:“或許最為重要的原因是,一些事物的終結對我們個體的生存影響極大。當代這些見證了人類歷史上最為恐怖的犯罪和災難(指大屠殺)的一代人正在慢慢消失。”而這些問題是如此之真切,真切到和歷史學家的個體倫理、個體代際關系等現實生活問題聯系在一起。因而,歷史研究在此不僅僅是現代專業的一套思想體系和話語體系研究——從文本到文本,從問題到問題,掌握前沿的研究動態,運用解釋性關聯創造更多的歷史話語。同時,歷史是活生生的,它就在當代社會的文化、政治、道德、教育、宗教、美學等領域中存在。在此,“歷史”和“歷史性”獲得了至高無上的高度和嚴肅性。同時,廣義的人類思想史研究和人類的現實生活也有機關聯了起來。這正如章學誠在《文史通義》中所言:“夫天下豈有離器言道,離形存影者哉?彼舍天下事物、人倫日用,而守六籍以言道,則固不可與言夫道矣。”
三、從歷史倫理到個體倫理
上帝基督為啟蒙運動之前史家的歷史研究提供倫理保障和意義來源,理性和進步為啟蒙運動以來的歷史學術研究提供倫理定位和意義支持。而在現代社會和全球化的時間經驗中,不斷的祛魅化不禁使我們反思,什么能夠為我們今日的職業化歷史研究提供給倫理和意義的確定性呢?
對歷史倫理的思考是在史學家考量歷史意義時必然會涉及的問題,也是史學家工作領域的基礎性部分。作為專業化的史學家,我們在對過往的時間經驗和歷史意義以及歷史理性等基礎性范疇進行思考時,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思想標尺就是歷史倫理。甚至,在呂森看來,倫理準則是歷史思考的根本性準則,如果沒有對人類歷史的倫理尺度的把握和理解,整個現代的歷史思考和歷史研究將在倫理道德范疇沒有棲身之所,這導致作為一門嚴肅的學術研究的歷史研究在現代社會的文化倫理中無法立足。
作為專業的歷史學家的我們,在時空關系中對過往的歷史經驗之紛繁復雜和其中人類行動和受難中的愛恨情仇的處理,都將其置于一個總體性的歷史倫理的思想范疇中。同時,作為具有主體性、存在有限性和理性機制的我們自身而言,我們本身也處于一個時空關系和歷史關系中,那么對于自身倫理的思考和定位也就自然是其中之意了。在現代社會及其思想狀況中,特別是全球化以來的經驗進程告訴我們,必須重新思考并力圖合法化在現代倫理關系中的歷史學科性研究。職業化以后的歷史研究對于職業的史學家而言更多的是一門“技藝”,對于學科規范和寫作言辭結構的強調更勝一籌。然而,在現代社會甚至后現代不斷祛魅的過程中,元理性的缺失成為必然的結果,在沒有理性觀照下的歷史研究本身也昭示著意義的缺失,而意義的缺失的直接結果就是倫理位置的喪失。將這個邏輯置于歷史學家個體層面來看,當我們的工作性質因為元理性的缺失而導致意義災難的時候,我們無法在沒有意義的思想狀況中進行工作。由此,我們工作的倫理性質問題也就凸顯了出來。我們在今天人類全球化的進程中為何依然要研究歷史?我們工作的終極價值何在?我們的研究是在制造話語還是在講述真實的人類故事?
這個過程是一個“行有不得,反求諸己”的過程,也是一個從歷史倫理到個體倫理(自我倫理)思想演化過程。我們將我們研究中的真實的人類問題安放在自己的身上,以此來體察個體自身和歷史研究本身在現代社會的倫理處境。當然,對于這個本身對現代所有史學家都具有思想預設性的問題,并不是所有的職業史家都會關注或愿意去面對,我們可以在故意忽視這個我們工作的思想預設的基礎上繼續從事我們的工作。
而作為歷史哲學或史學理論的研究,其工作本身的一個部分或學科性職能就是不斷重新面對并論證歷史研究在歷時性的社會狀態和時間經驗中的合法性位置。當我們論證了歷史研究的合法性意義之后,歷史倫理自然就得到論證:而歷史倫理的論證也就為歷史學家本身的工作性質提供了思想保證和意義地位,從而使得史家的個體倫理也得到確定性答案。可見,在歷史研究中對歷史倫理的論證本身也是對史家個體倫理的回答:反過來,作為個體的歷史學家的我們,我們自身的真實的生活經歷、思想狀態、精神結構和理性機制為我們論證當時的歷史倫理提供了思想源泉和智力支持。從歷時性來看,歷史學家對個體倫理的論證過程是具有時效性的。不同的時代、不同的社會思想、不同的歷史經驗的供給也會導致不同的歷史倫理合法性的導向需求。總的來說,一是在對歷史倫理論證的同時,也是對歷史學家個體倫理和自我倫理的論證:二是史家的個體倫理與自我倫理的論證為歷史倫理的論證提供了思想來源、促動力和導向性;三是歷史倫理和個體倫理是一個難以割舍的、相互關聯的雙向性思想過程:四是歷史倫理和個體倫理都具有“不同時代的同時代性”的特點,隨著新的時間經驗的出現、社會思想狀態的變化、人類實踐生活和受難的遭遇、人類未來期望的導向性需求,歷史倫理和個體倫理都會呈現出時效性的特點。因而,在上述諸種條件變化以后,歷史倫理和個體倫理需要不斷地重新論證,即“歷史總是需要重寫”。而對于“不同時代”總是需要的“歷史重寫”,通俗地說便是“太陽底下無新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