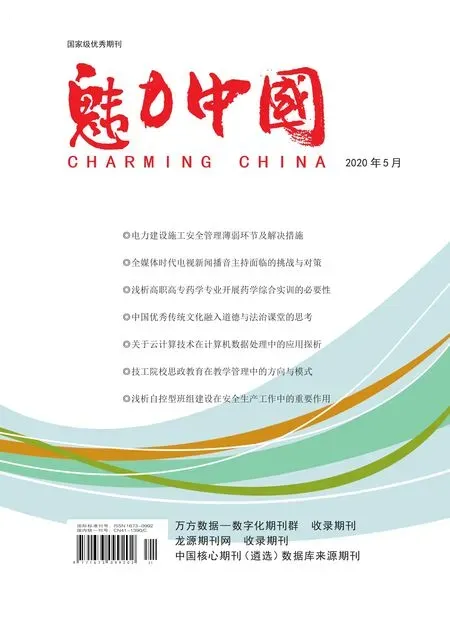譚恩美小說《喜福會》的敘事策略探賾
徐繼英
(鄭州師范學院文學院,河南 鄭州 450044)
譚恩美是一名優秀的華裔女作家,《喜福會》是她的經典之作,曾暢銷于《紐約時報》。整個小說的故事是圍繞喜福會俱樂部展開的,通過對四對母女的情感、思想等的刻畫,讓整個故事栩栩如生,小說凸顯了譚恩美的敘事策略及創作技巧的高超。譚恩美用傳記的形式創作故事,能夠吸引讀者的觀賞,拉近了讀者與作者的心靈距離,獲得大眾的認可。
一、《喜福會》的敘述結構
(一)故事環結構
故事環結構不僅要保證小說每個故事的獨立性,還要保證整本小說的整體性,屬于在長篇和短篇小說之間的獨特文學體裁。故事環結構的小說閱讀性很高,需要在各個小故事中兼顧作品的整體性,給人們帶來文學藝術美感,賦予小說更豐富的內涵。故事環一直是西方文學體裁,而譚恩美作為經驗豐富的專職作家,將中國傳統元素應用在她的作品《喜福會》中,結合故事環結構突出故事內容。譚恩美創新了傳統小說創作和敘述的結構和方式,站在中西文化差異基礎上,改造西方傳統文學體裁,是小說創作的一種新嘗試,利用小說中母女的之間的故事,凸顯中美文化的沖突與融合。譚恩美的《喜福會》中有十六個小故事,每個故事似乎都是獨立的與其他故事并不相干的內容,但通過一個主題思想將多個小故事又相互銜接在一起,構造出一個完整的故事。這種各個環節的小故事似乎相互對立,又貌似相互關聯的敘事結構,就屬于故事環的范疇。喜福會就是本作品核心路線和重要的象征,這里不僅是小說中母親麻將聚會的場所,也是女兒感情喜怒變化的主要地方,聯系著母女兩代人的思想,這里發生的故事體現了過去、現在,以及東西方的差異,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喜福會》中主要人物性格、心理的發展變化在故事環中具有重要作用,例如吳晶妹的情感表達一開始是對母親舊思想和生活方式的厭惡,隨著母女關系的轉變,女兒的感情逐漸轉為理解和接受。
(二)章回體結構
譚恩美在《喜福會》中講述了四位中國母親和四位外籍兒女身上所發生的故事,利用打麻將巧妙地對故事進行編排,這種敘事結構類似中國傳統的章回體結構。譚恩美用傳記的形式突出了中美文化差異,利用章回體結構將故事講述的淋漓盡致,凸顯了創作技巧,并提高了故事表現力。《喜福會》是由十六個獨立的小故事組成的,不同章節的相互聯結,又構成了一部完整的故事體系,類似打麻將一樣的將每個主人公的性格、情感表達都在不同在章節中凸顯出來,這也是譚恩美創作技巧的展現。在小說中利用打麻將這個情節,將不同人物聯系起來,利用小說中出牌的順序,進而引出了四位女兒敘事的順序,在小說章節中吳晶妹有這樣的描述“林阿姨是東風,我是北風,最后出牌,映阿姨是南風,安阿姨是西風。”這一敘述對應了接下來敘事的內容。《喜福會》采用章回體結構的敘述結構,能夠層層遞進女兒與母親之間的關系,她們之間不同的理念、行為等,展示了兩代人之間的分歧,同時能夠從故事結構中明確難以割舍的母女關系。譚恩美在《喜福會》中逆轉了章回體小說的閱讀規范,通過故事主體部分內容的展現,吸引讀者去欣賞和閱讀,凸顯了譚恩美的一種敘事策略。
二、《喜福會》的敘
譚恩美巧妙地處理了敘述視角問題,在《喜福會》中采用第一人稱的敘述方法進行講述,使得讀者能夠更深刻地去感受敘述者的所思、所作,自然引導讀者進入故事情境中。一部小說故事的著眼點可以說就是敘述視角,是創作者想讀者傳達故事的一種方式和角度,《喜福會》以第一視角讓讀者跟隨作者去感受其中的故事和感情,能夠讓故事所表達的內容升溫。譚恩美利用第一人稱回顧性敘述方法,提高了《喜福會》的閱讀性,通過對“我”往事的追憶以及被追憶的同時“我”在經歷的事情,產生兩種眼光的相互交融,表達了在不同時期下對于事件的不同看法。第一人稱的回顧性敘述法,可向讀者傳達兩種價值觀念,也是了解真相與蒙在鼓里、幼稚與成熟的鮮明對比,比如小說在描述中秋節熒熒四歲游太湖的時候落水的事件,就采用了追憶的眼光,通過第一人稱追憶的視角能夠更清楚地對事件進行觀察。《喜福會》小說整體的敘述方式采用了第一人稱的視角,可以將主人公所處環境、心情狀態更直觀的表達出來,營造良好的敘事環境,通過追憶的視角能夠為人物后期發展做鋪墊,更容易理解“我”的心里路程。
《喜福會》大部分敘述視角都是第一人稱,由于第一人稱有時會限制敘述空間、時間,在小說中也有第二人稱的穿插使用,可以有效的提升敘述效果。通過“你”視角的表達,可以引導情感傾向,讓讀者更清晰地了解到故事的核心,深入到敘述者的故事講述中。譚恩美在小說中利用“你們”、“她們”等來指代不同的人群,例如“在我身上,她們看到了她們自己的女兒,同樣地無知,同樣地無視于她們帶來的所有的真理和希望。”這種敘事方法跳出了第一人稱,可以將敘述者想要表達的思想感情更深刻的表現出來,能夠突出母親對女兒不理解自己的畏懼情感。譚恩美在《喜福會》中除了使用第一人稱的敘述,還融入了其他視角的表達方法,這種人稱上的變換,可以起到故事美化的作用,就像是一直在變換的鏡頭一樣,給讀者帶來更生動的畫面感。譚恩美將中國傳統寫作手法與現代敘述技巧有效結合,讓讀者在《喜福會》中獲得了全新的體驗,這不小說具有較強的文學研究價值,突破了敘述方法的限制。小說在以“我”為核心的故事結構中,不斷變換著空間構架,讓讀者能夠從閱讀中感受到母女兩代人的思想文化理念,更多地滲透了中西方文化的對比,具有民族自醒的價值作用。
三、《喜福會》的敘事方式
(一)女性視角的敘述方式
譚恩美細膩的解讀了女性生活和情感思維,在《喜福會》創作中更多的是自身經歷的所感所想,作為一名具有雙重身份的族裔,能夠站在女性的視角創作出與男性作家不同的優秀作品。譚恩美在男性社會環境下勇于突破和創新,尋找限制以外真實地女性視角所呈現的思想內容,在作品敘事中改寫傳統男性獨有的講述方式,以女性為核心的創新敘述結構使人眼前一亮。《喜福會》主要通過女兒及其母親為主要人物,站在女性視角講述主人公的經歷和思想變化,并利用第一人稱不斷強調“我”的存在,就是對女性獨立體的一種尊重,向廣大讀者傳達了女性的氣質,體會到女性融入家庭的溫情和真實的情感,不僅是對女性的一種解讀,也提高了小說的藝術感染力。譚恩美通過《喜福會》將女性立場通過故事性傳達出來,對傳統男性敘述結構發起挑戰,這是一種全新的敘述模式,突破了當時社會的主流而選擇女性生命鏈條下的自然生命形態,利用母親與女兒之間的關系鏈條完成了一部展現母系思想、關系的佳作。
(二)順序型的集體性敘述
《喜福會》主要是通過母女關系展開的故事敘述,故事發展過程具有順序性,這是一種順序型的集體性敘述方式,給讀者帶來未曾有過的體驗。譚恩美精巧的利用打麻將把敘事人物都集中起來,可以對不同女性穿插著講述各自的故事情感,每個主人公的故事既是獨立的又是具有章法可尋的,為小說增添色彩讓讀者體驗到交響樂似的敘述聲音。《喜福會》中所展現出來的故事通過三位母親將主要內容“集結”起來,體現了集體性的敘述方法,每個敘述者之間都是孤立的,也保持著距離體現了順序型的敘述手法。小說通過母女之間發生的事情和心理、情感活動,體現了歷史中復雜的人物發展歷程,更多角度的折射出華裔文學作品的優秀。譚恩美在《喜福會》中表現了自身對女性深刻的認知,在當時時代背景下具有突破性意義,作者將鮮明的書面語經過自己風格的轉變使其變得模糊,在口頭語與書面語的模糊界限中,能夠感受到母親想要拉近母女關系的心理。
綜上,《喜福會》是譚恩美的經典作品,它深刻探討了中西方文化的差異,突破了傳統敘事手法,站在女性思想上展現人物關系及發展路線。小說采用第一人稱敘述方式,利用多視角敘述聲音及女性敘事對傳統主流霸權做出挑戰,將中國傳統文化與現代寫作手法相結合,豐富了故事內涵的表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