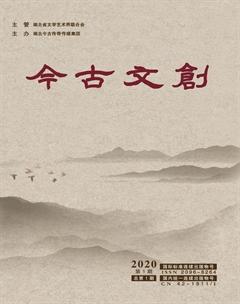重復的意義
鄒金濤
摘 要: 作為一個行文力求簡潔的作家,海明威在《白象似的群山》中運用看似多余的重復手法,自有特殊考量。根據重復內容的不同,本文將《白象似的群山》中的重復概括為四類:特定數詞、動作行為、特殊意象和話語內容的重復,分析這些重復之處呈現的特殊敘事效果,追尋其意義與價值。同時,本文還從具象分析上升到抽象理論層面,從辯證的角度概括出敘事性文學作品中重復手法的客觀效果,以冀見微知著。
關鍵詞:《 白象似的群山》;重復;敘事效果
中圖分類號: I206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2096-8264(2020)01-0023-05
一、引言
《白象似的群山》是海明威著名的短篇小說,堪稱“冰山理論”寫作風格的典范,這也是研究者歷來關注的重點。但海明威在小說文本中也設置了許多“重復”,如意象“白象”、數詞“二”(two)、動作“看”(look)、酒名、珠簾及短語“非常簡單”(perfectly simple)等。作為一個行文力求簡潔的作家,海明威在小說中運用看似多余的“重復”手法,應有特殊考量。
對文學作品“重復”敘事的研究由來已久,弗洛伊德的有關學說可被看作重復理論史上的一個重要轉折點①。重復最早是修辭學術語,指“依靠重復某一詞或詞組來達到特定效果的修辭手法” ②。重復是詩歌最基本的修辭原則,也是小說敘事的重要手段。
正如米蘭·昆德拉在評述《城堡》中部分詞語重復的現象時所言:“靠這種種的重復,作者在他的作品中引入一個具有關鍵定義、具有觀念特征的詞。假如作者從這個詞出發,展開一番長久的思索,那么從語義學和邏輯學的觀點來看,這同一個詞的重復就是必要的。”③當然,不是所有的“重復”都是有意義的—— “什克洛夫斯基曾認為,那些僅僅是為了正確、完整傳達語句信息而重復的字詞語句等,是不能算作重復的”“對于文本來說,往往在傳達信息上恰恰顯得‘多余的重復現象,才更具有詩性意義”④,這種“詩性意義”往往存在于具體文本中,我們很難推衍出具有普遍性的“詩學意義”。
J.希利斯·米勒在《小說與重復》的開篇指出:“無論什么樣的讀者,他們對小說那樣的大部頭作品的解釋,在一定程度上得通過這一途徑來實現:識別作品中那些重復出現的現象,并進而理解由這一現象衍生的意義。”⑤這一觀點所提倡的解讀方法與本文分析《白象似的群山》所采用的方式不謀而合,但本文并不著意于運用以米勒為代表的結構主義批評學派的方法,而是立足具體文本,發掘顯性的和隱蔽的重復現象,分析這些重復之處的“詩學意義”,以期對海明威的創作風格有進一步的理解。
當然,從某種意義上說,并不存在絕對的“重復”,因為“無論一個事件怎樣準確地重復了先前發生的一個事件,它們中間仍然隔著時間、環境等因素……這些重復其實是有差別的重復”⑥。而本文要做的,就是探尋這些“相似”重復各自特殊的意義。正如米勒所言:“在一部小說中,兩次或更多次提到的東西也許并不真實,但讀者完全可以心安理得地假定它是有意義的。”⑦《白象似的群山》中的種種重復若有深意,或如下文所述。
二、《白象似的群山》重復現象探微
《白象似的群山》中的“重復”現象劃分為四類,即特定數詞、動作、意象和話語內容的重復,在具體論述時會有部分重合。為貼近原文,本文將立足于英文文本、輔以必要的中文譯文,對這些重復現象進行闡釋,分析其特殊敘事效果,追尋其意義與價值。
(一)特定數詞的重復
《白象似的群山》中,有一個數詞重復出現的頻率高達8次⑧——即“two(二)”。國內已有研究者注意到這個可以稱上“不尋常”的現象,并認為“二”事實上“和小說兩性關系及‘二人世界主題”有某種程度上的聯系,“它出現的頻率之高間接昭示了選擇結果,暗示了作者意圖,深化了作品主題”⑨。
“two”在文本中的第一次亮相是在第一段的客觀寫景中,即作為故事發生背景的車站旁的“two lines of rails(兩條鐵路線)”。緊接著,敘述者向讀者說明,即將到來的列車會在中轉站停留“two minutes(兩分鐘)”。小說第一段運用了傳統的全知視角,敘述者在簡要交代故事發生的背景后便悄然隱退,承之以海明威獨特的“展示”敘事,文本僅僅呈現人物對話,不見對人物情態的任何描繪與評價。因此,這段環境交代無疑是我們解讀文本的一把鑰匙。
首先,“two lines of rails”很容易讓人聯想到兩條平行的直線,平行意味著永不相交,直線意味著不知起點與終點。聯系小說主題,我們可以合理推測,“two lines of rails”或與男女主角當下的狀態暗合,即二人想法在兩條不同的“軌道”上,兩人的未來也毫無方向、相當迷茫。其次,“two minutes”強調列車停留時間之短暫,這種短暫于面臨重大抉擇的主角而言,無疑會造成無形心理壓力,加劇兩人的矛盾沖突。總之,“想怎樣把字眼兒弄得準確一些”⑩的海明威不會隨意將時間設置為“two minutes”。
此后,“two”還在文中出現了六次,其中四次伴隨著“喝酒”這一行為,其余兩次情況較為特殊,暫且略過不表。“two”的第三次出場是男人向酒店里的一個女人說“Two big ones(兩大杯)”,若這可被看作點酒時的尋常會話,那么“two”又緊跟著連續兩次出現——即“The woman brought two glasses of beer and two felt pads(那女人端來兩大杯啤酒和兩只氈杯墊)”——便“有冗贅之嫌”·。這其實是海明威的敘事策略,即通過反復呈現數詞“two”,不斷強調眼前兩人所構成的“二人世界”。啤酒和氈杯墊的承接者是男女主角,二人世界的現狀經此酒杯和杯墊的數量得以從側面印證和強調。“服務員端酒給他們的場景就如同在兩人矛盾尚未激發前,一個旁觀者突然擺明觀點:‘瞧,你們仍是兩個人啊!”·
當兩人關于是否要墮胎的矛盾到達頂峰時,酒店里的女人再次出場,“with two glasses of beer(端著兩杯啤酒)”——這是“two”的第七次出現,表面上是再次強調“二人世界”,但讀者已經知道,兩人之間事實上有“第三者”,即胎兒的存在,這個“第三者”無疑對男女主角二人世界的平穩狀態構成威脅。因此,文中穩定和諧的“二人”狀態是流于表面的、不穩定的、隨時可能被打破的。此時,文中所有“two”的重復便可被看作是一種暗示與提醒,與“第三者”的存在相對立,形成反諷的敘事效果。
(二)動作的重復
縱觀全文,動詞“look(看)”一共出現10次,同為“看”的動作,文中僅有一處用“saw”來替換,其作用與“look”等同。也就是說,“看”的動作一共重復了十一次。其中,一至七次“看”的執行者是女主角,后四次的執行者則是男主角。每次“看”的執行者、對象以及語境的差異卻決定了其承載意義的不同。
女主角第一、三、七次“看”的對象均為“hills(群山)”,這與小說的主題意象“白象似的群山”緊密相關,對這三次“看”的分析將被放置到“意象的重復”一節。她第二、第五次“看”的對象是“the bead curtain(珠簾)”。她第一次看珠簾是在男主角反駁她、聲稱自己也許見過白象之后,也是二人矛盾初露端倪之時。她“看”珠簾是為轉移話題、避免加劇沖突。她第二次看珠簾是在男主角初次提及墮胎一事后,面對男主角所言“Thats the only thing that bothers us(使我們煩心的就只有眼下這一件事兒)”,她“looked at the bead curtain, put her hand out and took hold of two of the strings of beads(看著珠簾子,伸手抓起兩串珠子)”,顯得心不在焉。此時“看”珠簾是為回避會話,即以無意識的動作代替直接的言語回應,給自己緩沖的時間。另外,數詞“two”在這里再次出現,聯系前文所述的“二人世界”,這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女主角的潛意識——或許是對自己和男主角美好“二人世界”的懷戀,或許是對兩人岌岌可危的感情的審視。通過兩次“看”珠簾的動作,“curtain(珠簾)”本身也被賦予特殊意義,它可被看作橫亙在主角之間的矛盾與阻礙。女主角目光每向珠簾投去一次,便意味著離男主角更遠了一步,而這種引申意義與珠簾的隔離功用有關。
女主角第四次“look”的對象是“the ground(地面)”,這個動作也具有回避話題的作用。其特殊性在于,“地面”被后置定語“the table legs rested on(承載著桌腿)”所修飾,其承載物體的功用被單拎出來加以強調,突出“地面”作為安全歸宿的象征意義。或許女主角潛意識里尋求的正是“地面”所代表的踏實感與安全感,這是勸說自己墮胎的男主角不能給予的。女主角第六次“saw”的動作出現在繼開篇之后的另一段環境描寫中,不同于開篇客觀的敘述者口吻,這段描寫的鏡頭隨著女主角的目光緩慢推移。她暫時從對話中抽離,開始以全新的目光觀察周遭環境。這次“看”的意義不在于她視野中的具體景物,而在于她說的“And we could have all this(我們本來可以盡情欣賞這一切)”。墮胎一事帶來的煩惱使得她無心欣賞以大自然為代表的美好事物,通過這種對比,“墮胎”給女主角帶來的心理壓力之大可想而知。
在女主角第一次提出中止談話的要求后,男主角“looked at her and at the table(看看她,又看看桌子)”,潛在的敘述者開始把動作描寫的焦點向男主角轉移。在故事的高潮部分,女主角用七次“please”懇求男主角“Stop talking(停止談話)”,男主角的反應是“did not say anything but looked at the bags against the wall of the station(沒吭聲,只是望著車站那邊靠墻堆著的旅行包)”,旅行包上貼著“all the hotels where they had spent nights(他們曾過夜的所有旅館)”的“labels(標簽)”。敘述者輕描淡寫、一筆帶過,不動聲色地將讀者的視線聚焦到“標簽”上,引導讀者對男女主角過往甜蜜的二人生活進行想象,在一定程度上填充了文本的部分空白。男主角的“look”也許只是無意識的一瞥,也許是面對具有紀念意義的標簽,暫時陷入對二人過往生活的回憶。
緊接著,男主角“picked up the two heavy bags(拎起兩只沉重的旅行包)”,此處的“two”再次向讀者強調了“二人世界”的表象。他的目光先后投向“the tracks(鐵軌)”和酒店里閑坐候車的“the people(人)”,前者似乎能夠反映出他在經歷了一場與女主角開誠布公的爭論后渴望逃離的心情,后者則隱隱透露出他對酒店里閑坐無事忙的人的羨慕,或是對平靜閑適的情緒狀態與沒有紛爭的生活的向往。
海明威在小說行將收尾時將動作描寫的筆墨放在男主角身上,筆鋒轉變雖然稍嫌突兀,但也產生了特定敘事效果,即彌補前文對男主角客觀描寫的空白,也避開對女主角情緒爆發后的心理轉變過程的直接描繪,只在結尾附上女主角的一句“I feel fine(我覺得好極了)”,留下新的空白,供閱讀者自行想象。這延續了“冰山理論”的敘事風格,產生虛實相生的審美效果。
(三)意象的重復
論及小說中的意象,最引人注目的是題目中的“white elephant(白象)”,這一意象在文中共出現三次,且都由女主角提及。第一次是兩人剛坐下不久,女主角看向遠處的群山,評價“They look like white elephants(它們看上去像一群白象)”。連綿不斷的白色群山酷似女人孕肚的輪廓,而在英語中,“白象”是昂貴而無用的東西的代名詞。女主角借“白象”意象隱喻“墮胎”,試探男主角反應,是一種心理博弈。“白象”的第二次出現依然伴隨女主角“看”群山的動作。她多次以有意無意的方式暗示不滿,男主角的回應卻敷衍潦草,讓人灰心沮喪。于是她改口道:“They dont really look like white elephants(這些山看上去并不真像一群白象)”,這顯然是松口與讓步,但男主角卻以“Should we have another drink(咱們要不要再喝一杯)”輕巧地轉移話題。這并不代表他不關心“墮胎”一事,他只是無意玩猜字謎的游戲。在發出這句問話后,他單刀直入,直接提及“operation(手術)”。這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二人思維方式及立場的不同。
“白象”第三次出現在二人就是否要做手術一事展開爭論時,女主角質問:“But if I do it, then it will be nice again if I say things are like white elephants, and youll like it?(但是如果我去做了,那么倘使我說某某東西象一群白象,就又會和和順順的,你又會喜歡了?)”她在表達對男主角一再忽視“白象”譬喻的不滿,他忽視“白象”等同于忽視她的個人表達與個人意愿,在是否要做手術這件事上亦是如此。女主角最后一次“look”的對象仍然是先前被她比喻成“白象”的“hills”,但此時“白象”這一喻體卻并未出現。在矛盾充分暴露后,她似乎已經疲于再做這樣的聯想——事實上也沒有必要再如此隱晦。
文中多次出現的還有各種酒名,其中“beer(啤酒)”多次被作為轉移話題、緩和矛盾的調和劑,此外“Anis del Toro(西班牙語,指茴香酒)”和“absinthe(苦艾酒)”也曾在男女主角的對話中出現。故事發生的地點是車站旁的酒吧,對話中包含酒名似乎無可厚非、理所應當,但女主角作為孕婦,本應禁酒,這些酒名背后的深意便值得推敲了。
“Anis del Toro”和“absinthe”共同出現并非偶然。有的中文譯本對“absinthe”作了這樣的解釋:“苦艾酒,一種帶有較苦的茴香味道或甘草味道的高濃度酒……現在苦艾酒因有毒性而在很多國家被禁用”·。也有譯本指出:“1905年,瑞士農夫在喝苦艾酒后殺死了他懷孕的妻子和兩個孩子……這一事件引發了當時對苦艾酒的強烈抨擊……這里可能是姑娘在影射男人要她流產這件事”·。
在苦艾酒遭到普遍抨擊時,“Anis del Toro”因味道類似苦艾酒而成為其替代品,因此文中重點不在“Anis del Toro”,而在它背后的“absinthe”。值得注意的是,小說一開始就交代了男主角是“American(美國人)”——這也是關于主角身份的唯一信息,而美國在20世紀20年代的確曾頒發過禁酒令,這可以解釋為何男主角在女主角提及被禁的“absinthe”時,第一反應是“Oh, cut it out(哦,別說了)”。
(四)話語內容的重復
與上文提及的重復現象相比,小說重復主角對話內容的用意要明顯許多。女主角的談話內容重復之處是意象“white elephant”和小說尾聲的七次“please”。前者我們已作論述,后者需聯系“冰山理論”分析。基于追求省略的“冰山理論”,海明威并未對重復了七次“please”的女主角的語氣、表情等能夠反映其心理感受的外在變化進行描繪,但“please”的多次重復已經基本達到了直接描寫所能達到的敘事效果。其高明之處在于運用重復的詞語刺激讀者的視覺神經,同時給讀者安排不完整的心理空間,促使讀者調動自己的聯想和感受能力進行合理想象、追加相應的內容,小說“言有盡而意無窮”的魅力由此產生。
男主角重復使用的詞語與流產手術直接相關,如重復聲稱手術“perfectly simple(十分簡單)”,重復使用“really”“just”等副詞強調,希望說服女主角接受流產手術。這種重復看似啰嗦,但卻“常被用來表現人物精神上的某種困擾,如心理上始終被一件事所糾纏,不能解脫,致使它在人物對話、思想以至潛意識中重復地出現”·。海明威采用提高敘述頻率的方式來暗示男主角內心的焦慮,“書面語篇中的重復……是話題選擇的結果”·,小說的主題也就在一次次重復中得以強調。
三、重復敘事的意義
海明威不止在《白象似的群山》中使用過重復手法,他作品中的重復“不是人為的技巧(像詩歌中的押韻那樣),而是來自日常生活的口語,來自最天然的言語” ·。國內曾有學者指出,“海明威有時使用單一敘事的反復,即講述若干次發生過若干次的事”“不斷地變換著敘述頻率,求得敘述節奏的豐富性、多變性” ·。戴維·洛奇也曾如此評價海明威1927年發表的《在另一個國度》中的重復手法:“就他早期的作品來說,他創造了一種頗具新意、劃時代的手法”·。
從概念意義傳遞的角度來看,重復極度冗余;但從語用效果來看,重復具有高度的藝術表現力。小說作為書面語篇,具有高度的組織性,而“書面語策略的最高準則是詩性,即語言學所說的修辭原則……書面語篇的作者為了語言表達的詩性和修辭效果,有時會以經濟性、明晰性為代價”·。在海明威所處時代流行的所謂“雅文”中,“重復”是行文的大忌。但“認為‘雅文使經驗顯得虛假不實”21 的海明威寧可犧牲自己所追求的經濟與簡潔,也要力求貼近真實生活,“以實證的、平鋪直敘、剝離哲學思考的視角,來刻畫生命的慘淡”。22
“重復”手法的獨特作用主要在于“使人從誤以為‘熟或自以為是的狀態中醒悟” 23 ,畢竟“相同或相似語句的每一次重復都在意義上達到一次增值”24。
注釋:
① ·殷企平:《重復》,《外國文學》,2003年3月第2期。
②余弦:《重復的詩學——評〈許三觀賣血記〉》《當代作家評論》,1996年第4期。
③米蘭·昆德拉:《被背叛的遺囑》,余中先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3年第1版,第116-117頁。
④趙崇璧:《論重復的詩學功能》,西南大學,2009年4月。
⑤(美)米勒:《小說與重復:七部英國小說》,王宏圖譯,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版,第1頁。
⑥李海紅:《解讀外國文學作品中“重復”結構的敘事意義》,《語文學刊》,2013年2月。
⑦同⑤,第3頁。
⑧統計數據依據版本為:The Oxford Book o f Short Stories by V.S Pritchett. Oxford: Ox 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⑨葉超:《海明威〈白象似的群山〉主題的呈現方式》《淮北煤炭師范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年8月,第26卷第4期,第88頁。
⑩董衡巽:《海明威談創作》,三聯書店出版社,1985年版,第29頁。
· ·同⑨,第89頁。
·[美]歐內斯特·海明威:《重壓下的優雅:海明威中短篇小說精選》,李華山等譯,湖南文藝出版社,2012年第1版,第185頁注③。
·[美]海明威:《蝴蝶與坦克——海明威短篇小說選》,高潔譯,復旦大學出版社,2014年第1版,第32頁注①。
·羅鋼:《敘事學導論》,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56頁。
· ·梁丹丹:《自然話語中的重復現象》,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12年第1版,第126頁。
·同③,第120頁。
·張薇:《海明威小說的敘事藝術》,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5年第1版,第73頁。
2 1 2 2戴維·洛奇,盧麗安譯:《小說的藝術》,上海譯文出版社,2010年第1版,第106頁。
24胡明貴:《漫談小說中的重復敘事詩學》《漳州師范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3期。
參考文獻:
[1]殷企平.重復[J].外國文學,2003, (02):60-65.
[2]余弦.重復的詩學——評《許三觀賣血記》[J].當代作家評論,1996, (04):12-15.
[3][捷克]米蘭·昆德拉.被背叛的遺囑[M].余中先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3.
[4]趙崇璧.論重復的詩學功能[D].西南大學,2009.
[5][美]J·希利斯·米勒著.小說與重復:七部英國小說[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
[6]李海紅.解讀外國文學作品中“重復”結構的敘事意義[J]. 語文學刊,2013, (04):73-75.
[7][美]海明威著,董衡巽編選.海明威談創作[M].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5.
[8]葉超.海明威《白象似的群山》主題的呈現方式[J].淮北煤炭師范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 (04):88-91.
[9][美]海明威.重壓下的優雅·海明威中短篇小說精選[M].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2015.
[10][美]海明威.蝴蝶與坦克·海明威短篇小說選[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4.
[11]羅鋼.敘事學導論[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
[12]梁丹丹.自然話語中的重復現象[M].上海: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12.
[13]張薇.海明威小說的敘事藝術[M].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5.
[14][英]戴維·洛奇.小說的藝術[M].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0.
[15]胡明貴.漫談小說中的重復敘事詩學[J].漳州師范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 (03):99-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