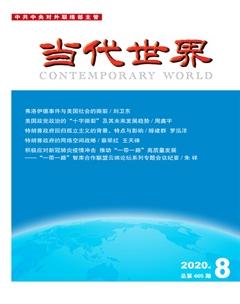弗洛伊德事件與美國社會的撕裂
劉衛東

【關鍵詞】美國社會;特朗普政府;種族沖突;弗洛伊德事件
【DOI】10.19422/j.cnki.ddsj.2020.08.001
2020年5月25日,美國黑人喬治·弗洛伊德因涉嫌使用假幣,被白人警察以“跪頸”方式致死,這一事件引發席卷全美乃至世界多國的示威游行和騷亂。美國政府和民間舉辦了多次祭奠弗洛伊德、推進種族和解的活動。但與此同時,社會上也出現了一系列以反對種族歧視為名進行的力度空前的抗議行為。特朗普政府最初立場模糊,沒有對事件本身的性質做出明確表態,隨后將重點放在對騷亂的譴責上。他在國慶演講中痛批“抹殺價值觀”“詆毀英雄”、完全不容異己的所謂“極左法西斯主義”,表示將堅決與其斗爭到底。客觀來看,弗洛伊德事件與以往黑人被白人警察無端殺害的案例并無本質不同,但在特殊的歷史條件下,引發了更為強烈、復雜和影響更為深遠的后果。從這個角度來說,弗洛伊德事件確實與眾不同。
社會騷亂由多種因素共同促成
弗洛伊德事件在美國各地引發的騷亂引人注目,其播散的范圍和造成的破壞乃歷史罕見。導致這一現象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點。
一是特朗普政府處置不當。弗洛伊德事件發生后,特朗普并未直接針對事件本身發表過有實質內容的表態,而是在推特中將抗議者稱為“暴徒”,并警告稱“當搶劫開始時,射擊就開始了”。他指責一些州長反應過于軟弱,宣稱如需要將派遣軍隊幫助維持秩序,同時在白宮周邊建立隔離墻,并令軍警驅散人群。特朗普回避了核心的種族歧視問題,沒有真誠慰問過弗洛伊德的家人,沒有對施暴警察進行過譴責,沒有認真傾聽示威者的聲音。事發之后他所做的主要工作就是將民眾最關注的種族歧視問題引向止暴治亂,不斷呼吁進行武力鎮壓。由于民眾感受不到政府的有效回應,所以選擇了以暴力方式去吸引關注。
二是自媒體廣泛傳播和刺激。警方致死弗洛伊德的過程確實令人發指,這一場面恰好被路人拍下并發到網上,頓時傳遍全球,給所有的受眾帶來巨大震撼。歷史上美國白人警察隨意施暴并不罕見,但引發嚴重騷亂的不多,正如好萊塢明星威爾·史密斯(Will Smith)所言:“種族主義并未變得更糟糕,只是它們出現在了鏡頭前。”在這個過程中,社交媒體發揮了顯著的信息擴散和社會動員作用,相關視頻在極短時間內傳遍全球,強烈的現場感刺激了大量民眾,使其難以按捺心中的憤怒而沖上街頭。
三是新冠肺炎疫情起到催化作用。弗洛伊德事件發生時,新冠肺炎疫情在美國已經肆虐兩個多月。因受“禁足令”影響,很多人被迫長期待在家里,忍受無法出門帶來的不便和痛苦,以及隨時可能被感染的恐慌,還有很多人因此而失業,他們心中都跳動著無名之火。弗洛伊德之死好比一根導火索,瞬間引燃了美國。可以看到,在示威中出現的一些打砸搶行為,與反對種族歧視毫不相干,他們只是為了發泄情緒或趁機盜取財物。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社會壓抑、人際疏離和經濟壓力在很大程度上成為騷亂的催化劑。
四是政治博弈原則轉型再現。特朗普政府就職以來,一直堅持策動對立、激化矛盾的執政方式,導致美國社會的戾氣越來越重,傳統的溝通協調和相互妥協方式逐步消失,暴力對抗似乎成為解決一切問題的良方。示威者原本是想呼吁政治改革,但迅速轉向對暴力的癡迷。他們的舉動又招致了政府的強硬反擊。特朗普除了嚴厲譴責騷亂分子外,還支持警察沿用壓頸執法手段進行自保。在這種環境下,一旦發生突發事件就很容易導致雙方滑向暴力沖突的深淵。
種族沖突背后的價值與利益之爭
弗洛伊德事件及其引發的騷亂,是以種族沖突為核心的美國社會動蕩的真實寫照。表面看,它是由一些偶發因素促成的,但實際上,美國社會深深的價值裂痕以及黑白族群對社會財富分配和相互地位的認知分歧,才是導致沖突和騷亂的根本原因。
一是自由主義與保守主義的持續較量。保守主義與自由主義都是美國價值觀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們恰如美國DNA中的兩條螺旋,相互纏繞又從不交叉,在地位起伏中共同塑造著美國的意識形態傾向。進入21世紀后,兩者相互交替、各領風騷。小布什政府秉持“富有同情心的保守主義”理念,而在奧巴馬政府任內則是自由主義大行其道,特朗普執政后又大力推進保守主義回歸,在移民、稅改、醫保、同性戀等議題上全面否決了奧巴馬的主張,還任命了兩名保守派大法官。但自由主義力量并未偃旗息鼓,而是迅速展開反擊,在2018年的中期選舉中,史無前例地將大量少數族裔、女性和性少數群體(LGBTQ)成員等非主流人士送入眾議院。弗洛伊德事件發生后,美國國內出現了一種所謂“警醒文化”,即在種族歧視、性別歧視等社會不公問題上保持警醒,并積極參與旨在根除這些不公行為的活動。“警醒文化”認為美國社會存在對有色人種系統性的歧視和壓迫,白人長期以來享受特權,且對這種特權缺乏認識。目前“警醒文化”的一個流行口號是“沉默即暴力”,鼓動并在一定程度上脅迫他人站隊表態甚至道歉辭職,與以往就存在的所謂“取消文化”如出一轍。這是一種極端自由主義思潮的表現,在保守派人士看來,這與極權主義無異。特朗普對此堅決譴責,宣稱這是一場“文化戰爭”。正是由于在意識形態領域始終存在著如此嚴重的對立,美國社會上才會出現持續不斷的抗爭和沖突,而弗洛伊德之死不過是為雙方的較量提供了一個新的導火索。
二是身份政治的對抗愈演愈烈。所謂身份政治是指以個人的種族、膚色、傳統、習慣等自然屬性而非經濟條件和社會地位來確立自身政治立場和心理歸宿的表現。身份政治對于政治地位和種族尊嚴特別敏感,具有一種自然的排他屬性。一些群體可能因為對自我身份的過度偏愛而陷入對其他身份群體的不滿甚至蔑視,從而引發沖突。身份意識始終存在,但在充滿對抗的環境下更容易被激發出來。其一,由于以少數族裔為主的外來移民逐年增多,美國白人總是或多或少懷有一種危機感,即以盎格魯-撒克遜為主體的美利堅合眾國正在被“褐化”,白人有朝一日會轉變成為少數族裔,那時他們所鐘愛的“山巔之城”是否會崩塌,美國傳統是否還能存在,自身的社會地位是否還能維持,這些問題都令其擔心。在這種背景下,白人種族主義會作為一種本能的心理反應,在潛移默化中表現出來。其二,黑人是美國奴隸制的受害者,美國社會一直存在對黑人群體的愧疚感以及對黑人做出國家賠償的呼聲,很多立法也傾向于對黑人做出特殊照顧。在這樣的環境中,黑人的身份特征被放大,一旦出現針對黑人的社會事件,就很容易被提升到種族歧視的高度,黑人也會因此獲得某種意義上的優勢身份,這同時也將民主政治拆解為部落政治,黑白種族之間便被分割為水火不容、難以妥協的政治群體。其三,身份原本只是一種自然屬性,但政治精英看到了對此進行操控可產生的政治收益。因而,他們故意以偏重一方的方式來爭取其忠誠與支持,這樣就人為將黑白兩個群體對立起來,將其置于天平的兩端。一方地位的上升則意味著另一方地位的下降,這種零和關系使得兩者之間始終處于緊張狀態。尤其是特朗普政府上任以來,對白人種族主義采取了默許的態度,在弗洛伊德事件中又故意忽視種族歧視問題,人為激發黑白族群間的矛盾。身份政治本身并不必然導致沖突,可一旦被政客操縱利用,則黑人和白人就都會成為對抗的犧牲品,除了政客之外沒有贏家。
三是在財富分配和社會地位方面的認知分歧催生了騷亂。長期以來美國黑人的經濟地位較低,是一個不爭的事實。研究發現,1968年時典型的黑人中產家庭的財富為6674美元,白人中產家庭的財富為70786美元。2016年時前者達到13024美元,后者達到149703美元,兩者的差距變得更大。據統計,只有高中文化的白人家庭的財富是同樣條件黑人家庭財富的10倍;經常或有時沒有足夠食物的黑人家庭的數量是白人家庭的3倍以上。從20世紀60年代后期開始,黑人的自有住房率幾乎沒有變化,而白人則隨著時間的推移穩步增長,目前僅有44%的黑人家庭擁有私有住房,而白人則有74%。[1]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以來,所有種族中死亡率最高的是黑人、最低的是白人,黑人死亡率是白人死亡率的約2.3倍。黑人在美國總人口中占比是12.4%,但在新冠肺炎病死者中黑人死亡人數占比是23.8%;而白人占美國人口的62.2%,但其死亡人數只占51.5%。[2]受疫情影響,美國的失業率也提升到大蕭條以來的最高點。根據美國勞工部的統計,2020年5月,白人失業率是12.4%,黑人失業率是16.8%。[3]還有調查顯示,63%的白人兒童生活在貧困率低于10%的地區,且父親陪伴的時間超過一半,而能夠滿足這一條件的黑人兒童只有5%。[4]如果從兒時就存在成長條件的顯著差距,則改變命運的前景就會更為渺茫,固化的社會結構會使黑人失去希望。
盡管如此,并非所有白人都認同自己的優勢地位。美國統計局的數據顯示,貧困人口中的42%是非西班牙裔的白人,加上自認為是白人的西班牙裔,則達到了66%。[5]近年來,有色人種的貧困程度基本穩定,但原本貧困的白人變得更加貧困。[6]由于各種政治原因,白人的貧困很少在歷史中被記錄下來。[7]在這種情況下,美國政府還堅持從政策上優待黑人的肯定性行動,允許非法移民轉為合法移民,繼續對穆斯林和中美洲移民敞開大門,引發白人越來越多的不滿,導致反移民、反全球化的民粹主義甚囂塵上。實際上,對現實不滿的并非只有黑人等少數族裔,白人同樣也充滿怨氣,他們認為社會救濟過多被用來滿足少數族裔的需求,美國納稅人的錢被花在了不該花的地方;多年以來照顧黑人權益、符合政治正確的政策使得白人遭遇了大量的“反向歧視”;追求結果平等而不是機會均等將會鼓勵不勞而獲的行為,顯著損害美國的社會活力和發展動力。因此,弗洛伊德事件后出現的騷亂并非只是為黑人權益而戰,同時也反映了部分白人要求改變社會現狀的訴求。由于兩者的認知存在沖突,他們一有機會就會為此而對抗,甚至發展到要用暴力來挑戰社會不公的程度。
種族沖突還是政黨對抗?
弗洛伊德事件之后出現的社會動蕩,席卷了美國50個州超過650個城市,就其規模來說是史無前例的。其根源究竟只是種族沖突,還是另有隱情?
從種族方面看,白人與黑人在種族歧視問題上的分歧正在縮小。在弗洛伊德事件中,大量示威者都是白人,甚至有些是共和黨人和特朗普的支持者,因為他們相信:“當前的問題不是左與右,而是對與錯。”弗洛伊德的死使很多白人反思,自己是否一直享受著某些不該擁有的特權。除了年輕人和自由主義者,一些保守人士也沖到了前面,他們認為自己是正派人士,有義務去匡扶正義。著名白人福音派牧師安迪·斯坦利最近的一句話已經在白人中廣泛傳播:成為一名“非種族主義者”已經不夠了,要成為“反種族主義者”。2020年6月中旬,美聯社與芝加哥大學無黨派客觀研究組織(AP-NORC)民調顯示,分別有54%的白人和92%的黑人相信,警察會使用更致命的手段來對付黑人,而5年前認同于此的白人與黑人的比例分別是39%和85%;認為司法系統對警察過于寬容的白人與黑人分別占比為62%和84%,而5年前的數據分別是32%和71%。[8]這顯示出白人和黑人看待這一問題的鴻溝正在縮小。

弗洛伊德事件之后出現的社會動蕩,席卷了美國50個州超過650個城市,就其規模來說是史無前例的。在華盛頓市長繆里爾·鮑澤的命令下,16街位于白宮前的路段已被命名為“黑人的命也是命廣場”。圖為2020年6月6日,一名男子手舉“停止殺害我們”的標語在美國華盛頓白宮附近的“黑人的命也是命廣場”路牌下參加游行活動。
但與此同時,政黨之間在種族問題上的對抗卻在加劇。美國皮尤中心的調查顯示,1994年時有39%的民主黨人和26%的共和黨人認為,種族歧視是黑人無法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直到21世紀初,兩黨在種族意識上的相似之處仍多于分歧。而奧巴馬的當選和特朗普的崛起則改變了這一點。美國的主流政治價值從溫和保守主義逐漸轉變為極端自由主義,8年后又迅速轉變為極端保守主義,而歷來敏感的種族問題也作為兩黨對抗的核心議題之一,在過山車般政策的刺激下推動雙方選民從包容變得相互對立。近年來民主黨為少數族裔代言的力度越來越大,而共和黨人則在對移民更為排斥的同時,與白人種族主義者越走越近。到2017年時,有64%的民主黨人認為,歧視是黑人無法取得成功的原因,但只有14%的共和黨人認同這一點。在這一議題上兩黨原本只有13個百分點的差異,而現在變成了50個百分點的鴻溝。弗洛伊德離世后的民意測驗也顯示出同樣巨大的兩極分化。共和黨人和民主黨人對抗議活動背后的成因有截然不同的看法。84%的民主黨人認為,長期以來民眾對黑人遭受待遇的不滿是抗議活動的主因,只有45%的共和黨人對此表示認同。82%的共和黨人相信一些人正利用抗議從事犯罪行為,只有39%的民主黨人認同這一點。同時,共和黨人和民主黨人對特朗普種族政策的認識也存在很大分歧。40%的共和黨人表示特朗普使事情變得更好,32%的人表示特朗普曾嘗試過但未能取得進展,13%的人表示特朗普沒有解決這個問題。相比之下,80%的民主黨人表示特朗普使種族關系惡化,8%的人表示特朗普嘗試但失敗了,只有2%的人表示特朗普使情況有所改善。如果以黨派來劃分,91%的民主黨人和有民主黨傾向者支持“黑人生命重要”運動,只有40%的共和黨人和有共和黨傾向者持相同認識。白人內部的黨派差距也很明顯。與白人共和黨人相比,白人民主黨人對這一運動表示某種程度支持的可能性要高55個百分點(92%對37%),其中62%的白人民主黨人特別支持,而只有7%的白人共和黨人特別支持。[9]
由此可見,在種族歧視問題上,美國黑人的認知變化不大,而白人群體則出現了明顯的分化,民主黨白人與黑人的認知更為接近,而共和黨白人則繼續保持右傾。在這一背景下,顯然已經不能再以種族沖突來看待當前的騷亂,因為很多白人已經與黑人團結在一起,共同反對種族歧視。與此同時,黨派已經成為決定種族問題立場的核心要素,民主黨人與共和黨人在幾乎所有涉及種族問題上的認知都存在非常顯著的差異。也可以說,政治因素而不是種族因素,已經成為決定種族問題走向的關鍵。民主、共和兩黨出于各自不同的考慮,分別將少數族裔和白人視為自己必須取悅的對象,并刻意增大兩者之間的對立。當前的騷亂與其說是社會與政府的抗爭,不如說是黑人平權與白人至上兩種運動之間的對抗,而其背后則是兩個政黨在進行推動。可見政黨出于私利的煽動和縱容,才是種族對立的直接誘因。
弗洛伊德事件對美國政治的影響
種族問題在美國極為敏感,歷史上美國發生的唯一一次內戰,起因就是種族問題,而其導致的死亡人數超過了美軍在一戰、二戰、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中的陣亡總和,這也反映出種族問題在美國國內政治中的分量。弗洛伊德事件再次引發了人們對種族問題的關注,但在當前的歷史條件下,這已經演變為一場政治秀,各方都想借其名進行政治營銷,鼓動民意,擴大自身話語權,而非真正銳意改革。因此弗洛伊德之死會在美國歷史上留下一個印記,但不太可能真正改變美國社會。不應把當前的騷亂僅僅理解為黑人的憤怒,實際上,弗洛伊德事件將整個美國社會積聚的各種憤怒都釋放出來,自由派與保守派、黑人與白人、民主黨人和共和黨人,都能從事件本身及其后續事態中找到令自己感到憤怒的理由。不論是否上街游行,他們都會通過自己的行動對美國政治施加影響。
一是在促進社會反思的同時更加劇了社會分裂。事件的爆發,激起了社會大眾對黑人處境的廣泛關注和同情。這對于化解種族隔閡無疑是有益的,更多的白人愿意設身處地為黑人著想,兩者的關系會朝著進一步平等化的方向發展。但是,席卷全國的騷亂、民主黨過度的政治表演、“警醒文化”對人們的道德綁架以及特朗普政府的強硬對抗姿態則使這場以反對種族歧視為名的運動變了味,并引發了更多的社會矛盾。民主黨人極少譴責暴力行為,而是堅定支持公民以示威方式來爭取自己的權益,他們甚至把弗洛伊德塑造成一個反對種族歧視的英雄,而全然忽視了其真實的履歷;特朗普在美國國慶日的講話中,沒有提到種族歧視問題,卻對騷亂行為進行大力抨擊,這種看似符合政治正確但卻選擇性打擊了示威者的舉動,必然會激起后者及其支持者的強烈反對,進而導致美國社會被進一步撕裂。與此同時,黑白兩個種族內部都出現了分裂。民主黨內的白人與共和黨內的白人進一步分道揚鑣;而在黑人內部,精英人士與下層民眾也拉開了距離,前者強調“黑人最大的問題正是我們自己”,[10]相信“膚色不能永遠成為群體的擋箭牌和換取食物券的便利條件”,[11]這恐怕是絕大部分黑人難以接受的。此外,政治正確與個人權利的沖突也愈演愈烈,一些媒體人士因為反對騷亂者損壞公共設施而說了句“建筑也重要”或“派軍隊來吧”,就在強烈的社會壓力下被迫辭職,從而引發了人們對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所保護的人權受到侵犯的擔心。總之,整個美國社會正向著更不包容和更加對抗的方向演變,左翼和右翼都更喜歡訴諸暴力。[12]
二是加大兩黨內部矛盾,影響其未來戰略規劃。弗洛伊德事件發生后,共和黨內部出現嚴重分裂,多名共和黨大佬出面指責特朗普,前總統小布什、前國防部長馬蒂斯、前白宮幕僚長凱利、前參聯會主席穆倫和鄧普西等均對特朗普的應對提出批評,前國務卿鮑威爾甚至直言將會投票支持拜登。國會中一些一貫支持特朗普的議員不再積極表態,現任國防部長也明確反對特朗普出兵的主張。共和黨建制派顯然看到了一個削弱特朗普權威的機會。在共和黨已經被改造為“特朗普黨”的背景下,特朗普對弗洛伊德事件的應對進一步刺激了傳統共和黨精英,甚至引發其考慮特朗普與民主黨究竟哪一方才是更大的挑戰。而在民主黨內情況同樣復雜。2020年6月15日,50多個左翼組織聯合給拜登寫信,宣稱在弗洛伊德事件上他做得遠遠不夠,呼吁拜登支持停止資助警方,或不再給其授權,否則他有可能失去大選。雖然拜登明確拒絕了這些要求,但參眾兩院的民主黨高層在弗洛伊德問題上的姿態都比拜登激進,這同樣給他帶來了不小壓力。民調顯示,拜登現在比今年早些時候的表態更為自由,[13]這也是順應大勢所為。不過拜登戰勝桑德斯的主要原因就是其立場比較溫和,民主黨道路選擇問題在桑德斯退出大選后原本已解決,但在弗洛伊德事件的沖擊下,激進的自由派又看到了重回舞臺中心的機會。由此可見,兩黨內部斗爭的加劇,對維護兩黨的統一及未來的戰略規劃均提出了嚴峻挑戰。
三是對2020年大選會帶來沖擊但具體影響尚難確定。表面看來,特朗普拒絕譴責種族歧視會對其選情不利,但實際情況要更為復雜。一方面,黑人選民原本對民主黨的支持率就維持在90%左右,不管他們如何反對特朗普,在大選中能給拜登增加的新選票也很有限;而特朗普原本就沒有指望取悅黑人,他就是要通過人為制造分裂來強化保守的白人選民對他的忠誠度。另一方面,此次運動中出現了大量激進訴求,包括要求解散警局、呼吁白人下跪反思、強迫修改歷史上已經約定俗成的專有名稱、強拆歷史雕像等,甚至很多商家也看到商機,以“尊重黑人”為名推出一系列匪夷所思的替代產品,這一切都使人感到一個嚴肅的事件已演變為一場鬧劇。這會驅使一些中間派人士右轉,不得不選擇支持他們并不喜歡的特朗普。目前,特朗普在五個搖擺州的民調都落后于拜登,但他仍可以憑借在職優勢、出色的辯論表現、遠超對手的籌款額、選舉人票計票規則等有利條件爭取到連任機會。因此,弗洛伊德事件對2020年大選的最終影響尚難確定,大選結果還要看兩黨的決策和兩位候選人今后的表現。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研究員)
(責任編輯:甘沖)
[1] Heather Long and Andrew Van Dam, “The Black-white Economic Divide is as Wide as It Was in 1968,” The Washington Post, June 4, 2020,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business/2020/06/04/economic-divide-black-households/.
[2] APM Research Lab Staff, “The Color of Coronavirus: COVID-19 Deaths by Race and Ethnicity in the U.S.,” June 24, 2020, https://www.apmresearchlab.org/covid/deaths-by-race.
[3] Charisse Jones, “Black Unemployment 2020: African Americans Bear Brunt of Economic Crisis Sparked by the Coronavirus,” USA Today, June 4, 2020, https://www.usatoday.com/story/money/2020/06/04/black-unemployment-2020-joblessness-compounds-anguish-over-brutality/3138521001/.
[4] Raj Chetty, Nathaniel Hendren, Maggie R Jones, Sonya R Porter, “Race and Economic Opportun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an Intergenerational Perspective,”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135, Issue 2, 2020, https://academic.oup.com/qje/article/135/2/711/5687353.
[5] Ciara ORourke, “About 40% of People Living in Poverty Are Non-Hispanic White,” May 16, 2019, https://www.politifact.com/factchecks/2019/may/16/viral-image/about-40-people-living-poverty-are-non-hispanic-wh/.
[6] Kelly Chen, Michelle Toh, “Included: Poor White Americans Are Getting Poorer; What Diversity Numbers dont Say,” CNN, November 10, 2017, https://money.cnn.com/2017/11/10/news/included-racial-wealth-gap-coke/index.html.
[7] “Poor Whites Have Been Written out of History for a Very Political Reason,” An Interview with Keri Leigh Merritt, August 24, 2019, https://jacobinmag.com/2019/08/poor-whites-have-been-written-out-of-history-for-a-very-political-reason.
[8] Kat Stafford and Hannah Fngerhut, “AP-NORC Poll: Sweeping Change in US Views of Police Violence,” June 18, 2020, https://apnews.com/728b414b8742129329081f7092179d1f.
[9] Kim Parker, Juliana Menasce Horowitz and Monica Anderson, “Amid Protests, Majorities Across Racial and Ethnic Groups Express Support for the Black Lives Matter Movement,” June 12, 2020, https://www.pewsocialtrends.org/2020/06/12/amid-protests-majorities-across-racial-and-ethnic-groups-express-support-for-the-black-lives-matter-movement/.
[10] “Candace Owens: ‘I DO NOT Support George Floyd! & Heres Why!” June 4, 2020, https://www.youtube.com/watch? v=JtPfoEvNJ74.
[11] Richard Ebeling, “Thomas Sowell at 90: Understanding Race Relations Around the World,” June 17, 2020, https://www.heartland.org/news-opinion/news/thomas-sowell-at-90-understanding-race-relations-around-the-world.
[12] 據CNN6月1日報道,聯邦執法官員說,有組織的團體正在利用合法抗議作為掩護,尋求破壞和暴力活動。這些團體包括極右翼極端分子和白人至上主義者,也包括認同反法西斯意識形態的極左翼極端分子。
[13] Cameron Easley, “Voters Increasingly Place Biden Closer to the Ideological Extreme,” July 10, 2020, https://morningconsult.com/2020/07/10/liberal-moderate-conservative-trump-biden-poll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