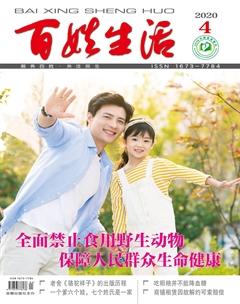老舍《駱駝祥子》的出版歷程
宋強
對于老舍的代表作《駱駝祥子》能否出版,人民文學出版社內部曾爆發了一場激烈的爭論。支持出版的是第一編輯室主任方白,反對者以時任副社長王任叔為主,之后社長馮雪峰、副總編樓適夷都參與了意見。這個爭論牽扯了如此多的人和如此多的意見,在當時是很罕見的。
1952年12月,人民文學出版社第一編輯室主任方白提議出版《駱駝祥子》,但時任副社長王任叔表示反對。1954年7月5日,方白提交了《駱駝祥子》審稿意見。7月7日,王任叔再次表示不同意出版,即使是老舍同意修改也不行,他因此與方白發生了嚴重的意見分歧。僅僅過了一天,方白再次提交他認為可以出版的理由。最后,馮雪峰、樓適夷、王任叔等人經過商量,決定可以出版,但要求老舍必須修改。
關于《駱駝祥子》,方白和王任叔的分歧,主要集中在如下幾個方面。
一、老舍的創作思想和《駱駝祥子》的思想傾向問題。在方白看來,“它暴露了舊社會的黑暗,以及屬于市民階層中個人勞動者在這黑暗中掙扎與被吞沒的悲劇”;“這部長篇可認為作者在1949年前的全部作品中的最高成就。”而王任叔認為,老舍“是以小市民的‘悲天憫人的精神來描寫城市貧民而博得讀者的歡迎的”,“這種‘悲天憫人的精神,或使人消失了是非觀點,或使人消失斗志”。
二、祥子的描寫問題。王任叔認為,老舍并沒有把祥子這個人物寫好,“寫一個勞動人民,一味隨著社會黑暗勢力,往下墮落,一點沒有振作和掙扎的勇氣,這是歪曲勞動人民形象的”。而在方白看來,老舍本人出身市民階層,熟悉小市民,所以他就寫“小市民中個人勞動者”,祥子“不是產業工人,也不是農民隊伍中的一份子,很難走上集體行動的道路也是自然的”。他們關于祥子形象的意見,向老舍提出了修改意見。老舍最終按照出版社的要求,刪去了祥子最終墮落的結尾,讓祥子成為一個正面形象,這也有利于對工農形象的塑造。

1936 年老舍在青島創作《駱駝祥子》時的留影
三、對舊社會的批判和對社會主義思想的態度問題。在《駱駝祥子》原稿里,老舍對社會主義者曹先生和革命者阮明的描寫并非是正面的。王任叔認為,老舍“一方面鞭撻舊社會惡勢力(可是并沒擊中要害),另一方面也譏笑新生的、和舊社會相對抗的思想和勢力”。方白跟老舍溝通如何修后,老舍對兩個地方作了重點修改:一是“把祥子被阮明收買,而又出賣阮明的一段刪去;二是“把某些關于女人的議論刪去,讓這文字更干凈些”。 除了上述地方,老舍還對很多其他地方進行修改,如刪去涉及性方面的描寫。同時,刪去小福子被蹂躪部分的描寫。這方面的處理,讓整個文本變得“潔凈”。1954年8月,出版社再次向老舍提出需要對曹先生、阮明的形象進行修改。根據出版社的意見,老舍把對曹先生并不徹底的革命思想的諷刺之處刪掉,把涉及阮明的地方全部刪除,使阮明這個人物徹底從小說中消失。刪除之后的文本,政治態度明顯溫和很多。
四、《駱駝祥子》的文學史地位問題。方白看來,《駱駝祥子》暴露了舊社會的黑暗,“其意義與巴金的《家》、曹禺的《雷雨》正相似,藝術價值也較之并不遜色”,“作者善于運用口語,在文學語言的創造上是有相當貢獻的”。而王任叔對此并不認同,他認為,“《家》與《雷雨》對舊社會的抗議和控訴是有力的,而‘駱駝祥子這個與世沉浮的人物,卻是很少有這種東西”。
在出版社內部經歷了艱難的爭論之后,《駱駝祥子》最終能夠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不得不說是一個“奇跡”。這一方面要得益于當時相對寬松的環境,另一方面也得益于老舍的政治地位和社會影響。方白在審稿意見中專門提到,“作者政治傾向還是好的,從抗日開始,作者逐漸向進步力量靠近,堅持以職業作家生活下來,并在新中國成立后欣然回國,熱心創作,不計一切,其一貫的正派作風與努力勞動,都是值得肯定的”。對于這一點,也是王任叔不得不考慮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