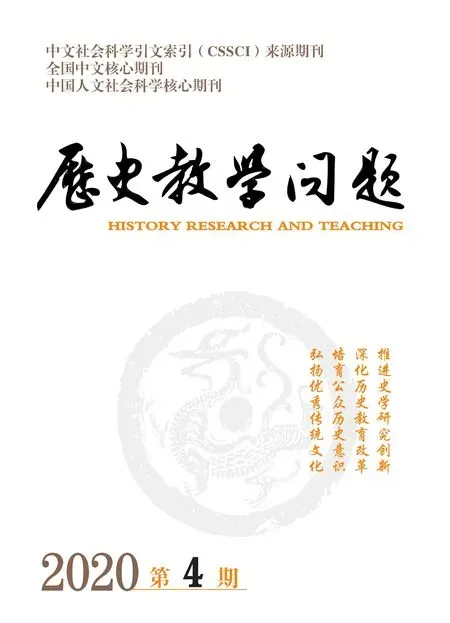澳大利亞早期華人商業的興起及其經營活動評析(1850—1901)
2020-08-31 06:58:24張秋生
歷史教學問題
2020年4期
張 秋 生
澳大利亞華人商業起源于19 世紀中葉淘金熱時期。為滿足淘金者對生活用品和淘金器具的需要,一批華人雜貨店、商號應運而生,其商業經濟活動還帶有自給自足小農經濟的特點。早期華人商業是在澳大利亞城市化發展及人口增加的背景下興起的。19 世紀后半期,華人商業不斷拓展,其主要經營活動表現在:城市華人店鋪、果欄、洗衣店的擴張;水果批發、零售與蔬菜銷售的繁榮;商鋪兼營借款、存匯款多種業務;北澳地區華人商業的出現;以及澳洲華人商業團體的建立和早期華商和澳中貿易的興起。華人商業的發展維持和滿足了早期華人移民對生活必需品的基本需要,維系了華人社會的經濟網絡和經濟生活,顯示了華人獨特的經商能力、經營特點和傳統文化的影響,推動了澳大利亞經濟社會的發展和移民文化的形成。
一、澳大利亞早期華人商業出現的背景
1.滿足淘金者對生活用品和淘金器具的需要
澳大利亞華人商業起源于19 世紀中葉淘金熱時期。“當淘金熱興起時,數百名華人店主就在當地的城鎮建立了自己的生意。其中一些人當時經營的規模都很大。”①Eric Rolls, Citizens: Flowers and the Wide Sea, Queensland: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Press, 1996. p.123.而經營多以雜貨店為主。當時,為滿足淘金者對生活用品和淘金器具的需要,一批雜貨店、商號應運而生。由于親緣、地緣關系,許多店鋪的生意是以縣為基礎進行的,華人也多到本縣業主開設的店鋪購物。另外,這些店鋪不僅維持和滿足了早期華人移民對生活必需品的基本需要,維系了華人社會的經濟網絡和經濟生活,同時,也受到了白人移民的青睞和歡迎。……
登錄APP查看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