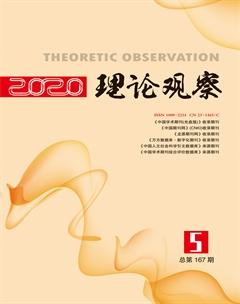網絡虛擬財產繼承規則構想
曾婷
關鍵詞:行網絡虛擬財產; 繼承規則; 網絡運營商
中圖分類號:D923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 — 2234(2020)04 — 0113 — 05
一、問題的提出
現代人離不開各種網絡社交平臺,用QQ處理工作、用微信保持聯系、用微博發泄情緒、用網店發家致富、用游戲放松精神等等,這些在公眾認知里都屬于網絡虛擬財產。互聯網的快速發展改變著人們的生活方式,人們在網絡上消耗越來越多的時間和金錢,精心經營著自己的“虛擬財產”。但人死后這些網絡上的東西要怎么處理呢?2011年,湖南省的王某不幸因車禍去世后,其妻為了留念,想保存丈夫的QQ賬號以及存在QQ郵箱里的信件和照片,但騰訊公司卻拒絕提供QQ密碼,理由是根據QQ用戶協議,QQ賬號所有權屬于騰訊,用戶擁有的只是使用權,不屬于用戶的遺產范圍。此報道一出來引起社會熱烈討論,人們不禁對虛擬財產在我國的地位及其保護方式產生懷疑。其實早在2003年就引發過虛擬財產糾紛問題。網絡游戲玩家李宏晨發現自己游戲賬號中的稀有的游戲裝備被莫名刪除,要求公安機關立案調查,但公安機關卻以網絡虛擬財產無法估價為由拒絕立案。一直以來網絡虛擬財產在我國法律上屬于空白狀態,處理糾紛的主要依據是網絡運營商與網絡用戶簽訂的相關協議,但如同前面案子一般,這些協議基本排除了用戶的繼承權。
為了回應社會上已經出現的矛盾,順應時代潮流,《民法總則》第127條規定:“法律對數據、網絡虛擬財產的保護有規定的,依照其規定。”該條款作為原則性的導向,表明了國家的態度,給未來網絡虛擬財產的立法提供了依據,但缺乏操作性。雖然人們看到了繼承網絡虛擬財產的希望,但如何繼承,如何分割,繼承范圍是什么,如何解決網絡運營商的地位等等,這些問題均沒有明確,本質問題依舊沒有解決,需要將來在《繼承法》或其他立法當中詳細規定。本文將圍繞以上問題展開論述,提出自己的網絡虛擬財產繼承規則構想,給未來網絡虛擬財產繼承立法提出一點拙見。
二、網絡虛擬財產的基本概況
了解網絡虛擬財產的概念、特征、分類,我們就能從中探討網絡虛擬財產繼承與傳統財產繼承的區別,針對網絡虛擬財產的繼承做特別規定的意義所在。
(一)概念與特征
對網絡虛擬財產的定義目前在理論界尚且沒有達成共識,但可以分成廣義和狹義,廣義上一般是指存在于網絡空間里,又能夠相對獨立地為人力所支配,以數字化形式存在但具備財產價值的各種信息資源。〔1〕王竹教授稱之為是“數字化環境下民事財產權客體的總稱,是具有財產性的數字記錄”。狹義的一般指用戶通過支付一定的貨幣資金,控制和支配賴以虛擬網絡環境存在的虛擬資源,如游戲賬號、裝備寵物等等。〔2〕狹義一般僅包括一些游戲道具、虛擬貨幣等。和麗軍教授在研究相關問題時,針對作為遺產的網絡虛擬財產提出一個概念:作為遺產的虛擬財產應當是指被繼承人死亡時遺留的個人所有的具有一定財產價值或者精神價值且以數字形態存在的各種信息資料,包括網絡賬號、網店、密碼、網游裝備、圖像、影像等等。〔3〕該定義比較具有針對性,強調了網絡虛擬財產作為遺產時的一些特征,也能適用于研究網絡虛擬財產繼承規則。
不同的概念表述其實都反映了網絡虛擬財產共同的特點:(1)數字性。網絡虛擬財產的本質其實是一組保存在服務器上的數據,可以表現為文字、聲音、圖像、數字等。數字性決定著人們只能通過網絡才能感知虛擬財產的存在。(2)價值性。網絡虛擬財產的產生與發展同樣凝聚著人類的勞動,人們對其投入智力、金錢和感情,具有財產價值的同時有著很強的精神價值。〔4〕通過其自身的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能滿足現代人的生活生產需求。(3)可支配性。網絡用戶可以通過自己的操作對虛擬財產進行支配,如拋棄某個游戲角色,購買一定數量的虛擬貨幣等。網絡虛擬財產能通過被用戶控制支配從而實現自己真正的價值。
(二)具體類型
網絡虛擬財產的概念是抽象的,可以將其大體上歸納為以下幾種類型:(1)網絡賬號。網絡用戶通過有償或者無償注冊的方式獲得賬號密碼,如QQ賬號、微信賬號、微博賬號等,用戶可以自己保存賬號密碼并對其進行使用和經營。(2)信息資料。用戶保存或者發表的帶有個人目的和個人感情的資料,如通訊錄、電子郵件、網盤資料、網絡相冊等等。(3)虛擬貨幣。用戶通過充值等方式獲得的網絡虛擬貨幣,可以在網上購買物品或服務等,如QQ幣、游戲幣、百度幣等。(4)虛擬物品。這類型網游裝備占大多數,如游戲玩家塑造的角色、打怪或者購買而得的道具和裝備。網絡虛擬物品具有明顯的物權屬性,網絡用戶可以對其占有、使用、贈與、拋棄等等。
(三)可繼承性
可繼承性主要從兩個方面分析:法理基礎與社會意義。
討論網絡虛擬財產繼承的規則,必須以其在法律上有繼承的可能性為基礎,否則討論就沒有意義。根據《民法總則》第127條可知,法律調整網絡虛擬財產。這背后蘊含著法理基礎,其中繼承方面的法理基礎為以下兩點。首先,網絡虛擬財產具有財產價值。這話有點矛盾,既然為網絡虛擬“財產”,那就應當如一般財產一樣具有財產價值。但其實網絡虛擬物品這個詞更為準確〔5〕,但因《民法總則》將網絡虛擬財產作為立法定語,所以現在用“網絡虛擬財產”來代替百姓一般理解的“網絡虛擬物品”,網絡虛擬物品這個詞意反而被縮小了。但同時也反映我國法律上已經承認了網絡虛擬物品的財產屬性。網絡虛擬財產價值性的形成同樣凝聚著群眾的勞動,并且能與現實財產互通、流通。如用現實財產購買網絡虛擬貨幣,用該虛擬貨幣購買其他物品,或者將虛擬貨幣以退還的方式等轉化成現實財產。虛擬財產極大的豐富了網絡用戶的生產、生活資料,也為用戶創造了現實財產。〔6〕其次,合法的網絡虛擬財產屬于遺產范圍。我國《繼承法》表明“遺產是公民死亡時遺留的個人合法財產”,雖然有限的列舉當中沒有明確表明有網絡虛擬財產,但有個兜底條款“公民的其他合法財產”,網絡虛擬財產可以歸屬為這一類型。法律總是具有滯后性的,在制定《繼承法》時互聯網甚至都沒有那么發達,甚少百姓會因網絡虛擬財產的繼承產生糾紛,故而法律就沒有預想到這一點,但規定了兜底條款,就是為了預防未盡事宜,預防新型財產的出現。總言之,網絡虛擬財產具有財產價值,是公民的其他合法財產,可受《繼承法》調整。
(三)可繼承的遺產范圍
如前分析,網絡虛擬財產可以分成經濟利益型和人格利益型,對于經濟利益型可納入遺產范圍基本沒有爭議,但對于人格利益型財產,如社交型賬號、電子郵箱、網絡照片、網盤資料等等,這些帶有非常強的個人因素,具有隱私性的網絡虛擬財產,是否應當納入法定的可繼承遺產范圍呢?這些類型的虛擬財產很容易涉及網絡用戶的個人隱私,網絡運營商往往就會以該些虛擬財產涉及個人隱私,與用戶簽訂隱私政策并用該隱私政策拒絕被繼承人的相關請求。那這些涉及隱私利益的網絡虛擬財產是否應當在繼承范圍當中?學術界主要有三種態度:不可繼承、可繼承、有條件的繼承。
可繼承說主要認為,我國保護死者的隱私,實際上是保護死者近親屬的權益,死者并無隱私權〔9〕,如果死者近親屬提出繼承要求,就說明死者近親屬的權益不會遭受侵害。并且在一般財產繼承中也會涉及個人隱私,而現實中因此引起的糾紛很少,說明一般人不會將死者遺產進行區分。只要沒有以違反公序良俗的方式利用隱私,就不會侵犯死者隱私。〔10〕還有學者認為根據與被繼承人的關系親密程度,涉及隱私的信息不應當被網絡運營商保存,只有繼承人才是占有和維護該些隱私的最佳人選。〔11〕不可繼承說主要是覺得對于涉及個人隱私的虛擬財產,出于尊重死者的角度應當杜絕該類信息的泄露。特別是一些人身性非常強的,嚴重涉及用戶隱私的部分不應列入遺產范圍。學者張融指出,根據繼承法原理,繼承的客體不包括人身權利,現行繼承法也排除了對人身權利繼承的可能性。但隱私虛擬財產可繼承說已與此法理相背離,間接突破了人身權利繼承的禁止規定。可繼承說會帶來不可估量的風險。〔12〕有條件繼承說對涉及隱私的虛擬財產歸屬問題采取折中的辦法,繼承人在繼承此類虛擬財產時,必須受到諸多限制。如繼承人必須簽署保密協議,必須對被繼承人的信息予以保密,否則要受到一定責罰。
筆者的觀點是,應當明確禁止完全具有人身屬性的網絡虛擬財產的繼承。隱私權作為一個權利來說,死者因為不屬于法律上的民事主體,的確不具有隱私權,但這并不等于死者沒有隱私,不等于死者的隱私無需保護。外人侵犯死者隱私只會給死者近親屬的權益造成損害這種說法并不嚴謹,也會給死者生前的名譽造成損害,而死者近親屬接觸到死者隱私后也是有可能成為破壞死者名聲的傳播者,這種破壞可能在社會上沒有引起很大的糾紛,但在死者生前生活的區域會流傳著流言蜚語。人的一生當中,即使是與關系最密切的配偶、死黨,也會有不想說的秘密,網絡上的陌生人或者非公開場所就成為最好的選擇,與陌生人訴說衷腸、發表僅自己可見的文字、保存非公開的資料等等,都屬于不想為他人知曉的隱私。人無完人,一個人在親朋好友、領導同事面前所展示出來的形象,是這個人想被他人所知的形象,只要背后沒有違法犯罪、破壞公序良俗的事,就應當尊重他人。人的隱私受到保護,不管是生前還是死后,不管是對外人還是近親屬。現在網絡虛擬財產類型繁雜,至于哪些屬于完全具有人身屬性,還需要總結各種經驗來判斷,如在繼承社交型賬號時聊天記錄就應當刪除,賬號內未發布的文字、照片等也應當刪除等等。
綜上,可繼承的網絡虛擬財產的范圍,可以采取概括式、列舉式和排除式并用的方法〔13〕,總體上認可具有經濟利益型的虛擬財產的繼承,列舉現有的典型的虛擬財產,最后明確完全具有人身屬性的虛擬財產不在遺產范圍內。
(四)網絡運營商的權利和義務
網絡虛擬財產的數字特性導致繼承發生時,必然涉及網絡運營商。網絡運營商在給某用戶提供某項網絡服務時,會該用戶簽訂用戶協議、隱私政策等,詳細研究這些協議會發現,里面的內容幾乎都排除了網絡虛擬財產繼承的可能性。如《微信軟件許可及服務協議》中第7.1.2條款規定:“微信賬號的所有權歸騰訊公司所有,用戶完成申請注冊手續后,僅獲得微信賬號的使用權,且該使用權僅屬于初始申請注冊人……非初始申請注冊人不得通過受贈、繼承、承租、受讓或者其他任何方式使用微信賬號。”又如,《百度網盤服務協議》中第一條第三款:“用戶不得濫用百度網盤服務的服務,百度網盤服務賬號僅限用戶個人使用,賬號不得有償或無償提供給任何第三方使用。”等等。禁止網絡虛擬財產主體的轉移,已經成為行業慣例。有學者分析其中原因主要有三:一是為了保護用戶的個人隱私;二是降低運營成本,可以省略繼承中一些列的專業問題、認定問題;三是可以提高網站運行速度。〔14〕網絡用戶在與網絡運營商簽訂該協議時,因內容的冗長,一般不會細看而選擇直接打鉤,這樣無形之中就放棄了網絡虛擬財產的繼承權。但這些服務協議屬于典型的格式合同,依照《合同法》第四十條規定,提供格式條款一方免除其責任、加重對方責任、排除對方主要權利的,該條款無效。據此,網絡服務協議中限制用戶轉讓、繼承、贈與網絡虛擬財產的條款,應屬無效。但繼承過程事情繁雜,僅認定該些條款無效解決不了根本問題,需要正面規定網絡運營商在繼承中的責任與權利。
網絡運營商幫助繼承人完成網絡虛擬財產的繼承,主要有以下幾點需要注意的:第一,在被繼承人死亡后繼承發生之前,保障網絡虛擬財產的安全,保證在這段時間里不會被非法分子鉆漏洞竊取被繼承人的遺產;第二,審核繼承人的身份。繼承人應當提供死者死亡證明、生前身份信息、關系證明等,網絡運營商首先需要根據用戶的注冊信息或者其他信息確定某項網絡虛擬財產的主體,再確認繼承申請人的真實身份以及其與財產主體的關系;第三,審核繼承人要求繼承的內容是否合法,是否屬于強制性要求不得繼承的范圍,如果屬于法律規定的不得繼承的范圍,應當明確拒絕繼承申請人的要求;第四,公告網絡虛擬財產主體的變更,該義務主要作用于網絡賬號。被繼承人在現實中死亡的事情不一定會被網絡朋友或遠朋知曉,他們更難以知曉網絡賬號主體更換。為了防止繼承人利用對方的不知情而進行違法或破壞道德的事情,網絡運營商有義務以提醒的方式告知網絡賬號主體已經更換。第五,必要的時候幫助繼承人認定網絡虛擬財產的價值,確保網絡虛擬財產能夠被順利繼承,等等。當然,也要賦予網絡運營商相關權利,如依舊可以與用戶簽訂網絡服務協議,但該協議不得直接排除繼承人的繼承權利;可以收取因繼承而產生的必要費用;對于無人繼承或不得繼承的網絡虛擬財產可以在具備正當理由的情況下合理回收虛擬財產等等。
(五)完善價值評估體系
前文所說的“2003年李宏晨案”,公安機關以“虛擬財產無法估價”為由拒絕立案,這在現今該理由基本說服不了群眾,網絡虛擬財產具有財產價值基本沒有爭議,但還沒形成完整的價值評估體系。確定網絡虛擬財產的具體價值,在發生法定繼承時,才能減少糾紛,實現分割遺產的意愿,因此需要創建網絡虛擬遺產價值評估機構。有學者建議建立獨立于網絡運營商和用戶的第三方評估機構,這樣相對公平合理。政府可以鼓勵成立專業的網絡虛擬財產價值評估公司,由專業的人做專業的事,綜合考量各種網絡虛擬財產的等級、熱度、交易價格等等,形成網絡虛擬財產價值評估市場。
四、結語
擬定網絡虛擬財產繼承規則,需要結合虛擬財產的特性和繼承的一般規則來構想:為了解決認證被繼承人主體合格問題,應當完善實名制注冊的強制性要求,如同一般財產有登記制保護一樣;在法定繼承時,視情況變通繼承人順序,根據網絡虛擬財產的屬性來分配遺產;明確完全具有人身屬性的網絡虛擬財產不得繼承,以概括式、列舉式和排除式的方式確定遺產范圍;協調網絡運營商的責任和權利,既保證繼承的順利完成,也不能挫傷互聯網的熱情;完善網絡虛擬財產價值評估體系,減少糾紛實現分割。隨著時代的發展,網絡虛擬財產會更加普及,如果缺少相關法律的具體規范,則無法解決隨之而來的糾紛,無法保障百姓的合法權益。《民法總則》第127條是一個信號,應以此為依據出臺相關法律法規切實完善網絡虛擬財產繼承的相關問題。
〔參 考 文 獻〕
〔1〕 張冬梅.論網絡虛擬財產繼承〔J〕.福建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3,(01):35-41.
〔2〕 錢凱.網絡虛擬財產繼承法律問題研究〔J〕.商業經濟研究,2016,(02):98-100.
〔3〕 和麗軍.虛擬財產繼承問題研究〔J〕.國家檢察官學院學報,2017,25(04):63-76.
〔4〕 孫山.網絡虛擬財產權單獨立法保護的可行性初探〔J〕.河北法學,2019,37(08):02-18.
〔5〕 瞿靈敏.虛擬財產的概念共識與法律屬性——兼論《民法總則》第127條的理解與適用〔J〕.東方法學,2017,(06):67-79.
〔6〕 游路遙,陳舒筠,吳國平.虛擬財產繼承立法構想〔J〕.重慶郵電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02):32-38.
〔7〕 劉曉月.論社交性網絡賬號的繼承〔J〕.吉首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7,(38):58-60.
〔8〕 李巖.虛擬財產繼承立法問題〔J〕.法學,2013,(04):88-92.
〔9〕 申晨.虛擬財產規則的路徑重構〔J〕.法學家,2016,(01):84-94.
〔10〕 郭育艷.網絡虛擬財產繼承問題研究〔J〕.河南財經政法大學學報,2014,(01):116-121.
〔11〕 梅夏英,許可.虛擬財產繼承的理論與立法問題〔J〕.法學家,2013,(06):89-92.
〔12〕 張融.關涉隱私利益的網絡虛擬財產繼承問題探討〔J〕.科學與社會,2018,(02):59-73.
〔13〕 潘椒巖.網絡虛擬財產繼承的立法構想〔J〕.人民論壇,2016,(1D):86-87.
〔14〕 王國強,耿偉杰.我國數字遺產繼承現狀研究〔J〕.情報科學,2012,(01):63-68.
〔責任編輯:張 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