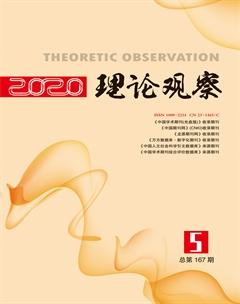網絡服務提供者注意義務的再完善
徐娜
關鍵詞:網絡服務提供者;預防義務;審查義務;網絡侵權
中圖分類號:D923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 — 2234(2020)04 — 0118 — 03
一、問題的提出
(一)《民法典(草案)》與《侵權責任法》第36條的比較
首先,是完善了 “避風港”規則的通知規則。一是增加了錯誤通知應當承擔侵權責任的規定。二是細化了權利人行使通知權的要件,即要求權利人在發出侵權通知同時應當提供其真實身份信息和初步證據。三是明確了網絡服務提供者負有轉送通知和聲明的義務。〔1〕《侵權責任法》對此并無規定,僅在相關的司法解釋中有所體現,即僅在網絡用戶主動要求提供通知內容時,網絡服務提供者才會提供;而《草案》則明確轉送通知和聲明是網絡服務提供者的法定義務。
其次,從法律層面上確立了“避風港”規則的反通知規則。《侵權責任法》第36條只規定了通知規則,沒有規定反通知規則,司法解釋也無具體規定,僅在國務院頒布的《信息網絡傳播權保護條例》第16條中有關著作權網絡侵權時規定了反通知規則,造成了通知規則和反通知規則在立法層級上不統一。而《草案》第1196條增加了反通知規則,網絡用戶有權主張自己不存在侵權行為,該規定實質上是為了網絡用戶與權利人之間進行平等對抗提供途徑。
最后,是擴大了“紅旗規則”的主觀適用要件。《侵權責任法》第36條第3款中“紅旗規則”的主觀要件為“知道”。有學者認為“知道”包含“應當知道”;〔2〕部分學者認為,若包含“應知”實質上是要求網絡服務提供者對網絡行為負有事先審查義務,這是不正確且無法做到的。〔3〕為了定分止爭,《草案》第1197條則明確將“紅旗規則”的主觀要件擴展為“知道或者應當知道”,這無疑是擴大了“紅旗”規則的適用范圍,為權利人提供廣泛的救濟途徑。
(二)《民法典(草案)》下網絡服務提供者注意義務的掣肘
有學者認為網絡服務提供者僅在知曉侵權行為的存在,或是收到侵權通知后未采取必要措施導致損害擴大的情形下,才承擔侵權責任。但是,如果侵權損害遠超過預防成本,則不能因為侵權信息過多而免除在未通知階段網絡服務提供者的注意義務。〔4〕《草案》第1197條的規定與上述觀點不謀而合。但是,在未通知階段網絡服務提供者應當承擔何種注意義務,《草案》未做明確規定。
網絡侵權進入到已通知階段,通知人和聲明人提供侵權信息或者抗辯信息已經明晰,此時,網絡服務提供者是否對初步證據具有審查義務,即網絡服務提供者是否應當積極、主動地審查初步證據的義務;如果有,當其不履行或者不適當履行審查義務,是否應當承擔侵權責任。
二、重新設定網絡服務提供者注意義務的理論基礎
(一)未通知階段預防義務設定的必要性
1.權利行使之限度
有觀點認為在網絡上上傳視頻、音頻等行為是自己的權利,如果在未通知階段即要求網絡服務提供者承擔預防義務會影響其言論自由,與推動網絡信息自由發展的趨勢相悖,可能會阻礙互聯網發展。〔5〕“如果我們從正義的角度出發,決定承認對自由權利的要求乃是根植于人的自然傾向中的,那么即使如此,我們也不能吧這種權利看作是一種絕對的和無限制的權利”,〔6〕網絡用戶是有發表言論等自由,但其享有的自由不應當損害他人合法權益。并且未通知階段的預防義務而不是對所有信息逐一核查,僅在特定情形下預防侵權,并不存在危害言論自由的可能性,設置預防義務是必要且合理的。
2.域外經驗之鏡鑒
美國《數字千年版權法》規定網絡服務提供者對網絡著作權侵權并不負有審查義務,但是,在面臨隱私保護和重復的、大規模侵權時,有責任去審查標準技術措施或者終止侵權人使用網絡;《歐盟電子商務指令》也明確網絡服務提供者沒有“普遍審查義務”,但是當成員國為了監測和阻止非法活動可要求其預防或者終止侵權行為。〔7〕其實,2018年國務院頒布的《互聯網信息服務管理辦法》也規定了網絡服務提供者不得復制、發布以及傳播侵犯他人合法權益或者法律、法規禁止的內容。該規定雖是從公法層面的規定,但也間接說明在私法層面上網絡服務提供者也有能力預防某些網絡侵權行為發生。
(二)已通知階段審查義務設定的合理性
1.遏制通知規則濫用
《草案》中明文規定網絡用戶應當對自己的身份信息以及發出的侵權通知或不侵權聲明提供初步證據,但并未明確是否需要對初步證據進行審查。筆者認為,應當及時對初步證據進行審查。首先,《草案》明確規定網絡服務提供者根據權利人提供的初步證據和服務類型決定采取必要措施,這實質上表明網絡服務提供者有審查權利人提供的初步證據的義務。其次,若僅審查權利人提供的初步證據,而不對未侵權聲明加以審查,網絡用戶只有等待權利人向有關部門投訴或者起訴的合理期限經過,網絡服務提供者才會終止必要措施,此時,不侵權聲明的本質無異于用戶反饋機制,不僅浪費了網絡用戶收集關于未侵權聲明初步證據的時間等成本、誘使權利人濫用侵權通知來拖延維權程序;還會導致權利人和網絡用戶間利益失衡,網絡用戶的正當權利無法得到主張,有失公平。
2.初步證據性質使然
對于已通知階段進行審查的合理性基于審查初步證據負擔較輕。一方面,審查對象明確,無需網絡服務提供者再去收集證據,節省成本。另一方面,依據危險源理論,因為網絡服務提供者離侵權危險源更近,所以其對于網絡侵權的類型、具體形式更加熟悉,更容易判斷初步證據是否具有合法性和合理性,進而依據審查結果決定是否采取或者解除必要措施。鑒于網絡傳播的即時性,由網絡服務提供者進行審查義務避免了審查結果的再周轉帶來的不便,節約成本,防止損害進一步擴大。
三、網絡服務提供者注意義務的重新設定
(一)未通知階段預防義務的設定
1.預防義務設定應采用“善良家父”標準
網絡服務提供者通常具有專業的技術支撐,充足的網絡經驗,所以未通知階段注意義務標準應當與其危險認知能力和預防控制能力相適應,建議以“善良家父”標準來設定未通知階段的預防義務。“善良家父”標準是法國認定侵權責任承擔的一種標準,其要求:“任何行為使他人受損害時,因自己的過失而致行為發生之人對該他人負賠償的責任。”〔8〕可見,“善良家父”不是一般謹慎的普通人,而是一個精明、謹慎如家父般的人,注意程度只有達到精明、勤謹家父的標準才可不成立過失,不承擔責任。〔9〕具體到網絡侵權,應當綜合考慮網絡服務提供者的技術水平、行為類型、權利客體情況來設定具體的預防義務。
2.具體設置
筆者認為,網絡服務提供者的角色轉變,單純提供某一種服務的甚少,將服務類型作為預防義務設定的考量因素不具有現實意義。所以,未通知階段網絡服務提供者預防義務的設定應當考慮其技術水平、行為類型以及權利客體。
首先,由于不同網絡服務提供者技術實力存在差異,而技術水平與網絡服務提供者預防侵權行為發生的能力密切相關。技術水平越高,對侵權行為的預防控制能力越強,網絡服務提供者負擔的預防義務越高。
網絡服務提供者預防義務的設置需要考慮網絡服務提供者的行為類型來設定。網絡服務體用這行為類型主要包括以下:直接獲得經濟利益、關鍵詞銷售以及設置榜單等。針對上述行為類型的預防義務設定應當根據人為干預因素具體衡量。對網絡內容干預越多,網絡服務提供者預防義務越高;反之,預防義務則越低。〔10〕例如,電子商務平臺經營者通常都是網絡交易信息內容的制作者,并從交易信息中直接獲利,故其預防義務更高。提供關鍵詞銷售的網絡服務提供者對于可能實施重復侵權的主體或是對極易被侵權的熱播作品,應當相應地提高預防義務。在“愛奇藝訴今日頭條關于《老九門》獨播權”一案,因為涉案作品是國家發布預警通知的熱播劇,今日頭條應當提高其預防義務的標準,并且本案中網絡用戶上傳的內容直接使用了電視劇名稱,并有“福利”、“搶先看”等字眼,侵權信息極為明顯,通過關鍵詞搜索很容易被發現并阻止上傳,故認定今日頭條侵權。
網絡侵權類型各異,不同權利客體的侵權判斷難度不同,網絡服務提供者應以判斷侵權難度為標準,判斷侵權難度越高則預防義務則越低,反之,則越高。例如,判定網絡用戶是否侵犯專利權等通常需要具有專業人士的專業技術背景支撐,而網絡服務提供者通常不具備相應的素質,所以設置高標準的預防義務不符合經濟效益;相對于是否侵犯他人的隱私權、肖像權等判定則更容易,預防義務標準設定的越高,網絡侵權的可能性越低。
(二)已通知階段審查義務的設定
1.審查義務應采用“權利、義務對等”標準
審查義務的設置應當考慮網絡服務提供者本身的利益與直接受其影響的網絡行業的發展,過重的審查義務不僅會使得該審查義務形同虛設,同時也會抑制網絡經濟的整體發展。“權利、義務對等”標準要求網絡服務提供者在已通知階段負有的審查義務以其享有的權利為限。在已通知階段,網絡服務提供者僅有采取或者終止必要措施的權利,所以審查義務不宜過重,不能要求網絡服務提供者扮演法官角色,來履行“裁判”的職責。
2.具體設置
應當先進行身份信息審查。因為網絡空間通常具有虛擬性,考慮到權利人或者網絡用戶真實身份可能難以認定,增加了認定侵權主體的難度,所以應當先就權利人和網絡用戶所提供的身份信息進行審查,審查通知人的姓名、身份證號、地址以及聯系方式等材料是否齊全。當身份信息缺乏必要材料的,造成難以確認真實身份,網絡服務提供者應當立即終止或者繼續采取必要措施;并且有權拒絕轉送通知或者聲明。但是,允許權利人或者網絡用戶再次補充或者更改材料。
身份信息被認證后,進行審查初步證據。初步證據的審查范圍應當僅限于通知人和聲明人提供的內容,對于侵權通知,應當提供“侵權證明,賬號、用戶名等能夠定位侵權網絡用戶的信息、侵權內容鏈接等可以定位侵權內容的信息、構成侵權的證明材料(如書面說明)等,涉及知識產權侵權的,還應當包括權屬證明,如權利證書等。”〔11〕針對未侵權提供的初步證明材料因具體的侵權類型不同,所以提出的抗辯理由也不具有類型化,應當結合具體情形提供有力的未侵權證據。初步證據的證明力只要達到證明侵權不存在的蓋然性標準,網絡服務提供者即可自主決定是否對疑似侵權鏈接采取刪除、屏蔽等必要措施。對于缺少必要證明材料的,網絡服務提供者應當認定該侵權通知抑或未侵權聲明無效,進而拒絕傳送,且采取或者解除必要措施。
四、結語
伴隨著網絡科技水平的發展,網絡傳播速度加快,互動性與開放性也愈來愈強,網絡侵權影響力極大,確保在不阻礙網絡發展的前提下,應當將網絡服務提供者注意義務分為未通知階段的預防義務和已通知階段的審查義務,為其各自設置相應的標準,加強對網絡侵權事前防范和事后保障力度,平衡各網絡主體之間的利益。
〔參 考 文 獻〕
〔1〕 楊立新.民法典侵權責任編草案規定的網絡侵權責任規則檢視〔J〕.法學論壇,2019,(03):89-100.
〔2〕 楊明.《侵權責任法》第36條釋義及其展開〔J〕.華東政法大學學報,2010,(03):123-132.
〔3〕 楊立新.《侵權責任法》規定的網絡侵權責任的理解與解釋〔J〕.國家檢察官學院學報,2010,(02):03-10.
〔4〕 梁志文.網絡服務提供者的版權法規制模式〔J〕.法律科學(西北政法大學學報),2017,(02):100-108.
〔5〕 崔國斌.網絡服務商共同侵權制度之重塑〔J〕.法學研究,2013,(04):138-159.
〔6〕 E.博登海默.法理學-法律哲學與法律方法〔M〕.鄧正來,譯.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7:305.
〔7〕 謝光旗.普遍與特殊:網絡服務提供者的著作權審查義務〔J〕.西部法學評論,2013,(03):71-77.
〔8〕 羅結珍.法國民法典〔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45.
〔9〕 劉樺.“合理人標準”在我國未成年人侵權責任承擔中的適用研究〔J〕.河南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01):81-85+90.
〔10〕 司曉.網絡服務提供者知識產權注意義務的設定〔J〕.法律科學(西北政法大學學報),2018,(01): 78-88.
〔11〕 寧園.網絡服務提供者之證明材料審查義務的設定〔J〕.科技與法律,2019,(05):88-94.
〔責任編輯:張 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