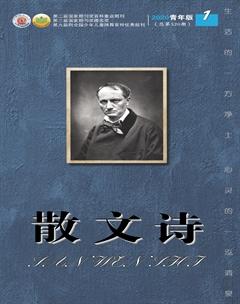伊文思:風(fēng)的故事、晚年與地貌
王年軍:1992年12月生,湖北十堰人。北京大學(xué)中文系電影與文化研究方向博士研究生。
《風(fēng)的故事》(Une histoire de vent,1988)完成于伊文思90歲那年,半年后,他就去世了。但是,影片顯然沒有任何風(fēng)燭殘年的哀怨和彷徨。
伊文思在銀幕中展示了自己作為精靈——美猴王的形象。他像一只跳來跳去的猴子,即使從沙漠盡頭的椅子上倒下去,也會(huì)在下一個(gè)鏡頭中重新站起來。伊文思也許是在20世紀(jì)僅次于毛澤東的另一位重新喚醒了中國自古流傳的美猴王神話的人,也是第一個(gè)嘗試對美猴王形象進(jìn)行現(xiàn)代闡釋的西方電影人。
而在影片的結(jié)尾,伊文思說:“在20世紀(jì)末,我相信了巫術(shù)。”要理解這句話,必須對他此前的一生有所回顧。從拍攝《西班牙土地》《四萬萬人民》起,他就站在了全世界左翼激進(jìn)政治運(yùn)動(dòng)的一邊,后來的大半生從未放棄對社會(huì)主義的信念,即使拍攝大規(guī)模史詩巨著《愚公移山》之后,他也仍然抱守自己孤絕的堅(jiān)持。
但是,在最后一部影片《風(fēng)的故事》中,他卻說自己開始相信巫術(shù)。那時(shí)候,以東歐劇變和蘇聯(lián)解體為標(biāo)志的“歷史的終結(jié)”尚未發(fā)生,而伊文思似乎已經(jīng)事先超越了政治上的左右之爭,達(dá)到了渾然、和解的至境。從某種程度上說,《風(fēng)的故事》也是伊文思的“詩的遺囑”。
和《四萬萬人民》中的抗日戰(zhàn)爭、《早春》中的三大改造和大躍進(jìn)、《愚公移山》中的文革不一樣,《風(fēng)的故事》中,伊文思把眼光主要投向了中國文化的沉積層,那些在歷史巨變中更有恒定性的因素。其所引用的中國文化符號又都經(jīng)過了伊文思的改寫,其中不乏他對東方的奇觀化的挪用,在《愚公移山》中對京劇藝術(shù)和民間手工藝的呈現(xiàn)中,伊文思就嘗試展示一種略顯神秘的東方藝術(shù),這在《風(fēng)的故事》中戴面具的悟空形象、龍的面具中得到了延續(xù)。
后羿射日顯然有伊文思本人的自喻在里面,他是一個(gè)日薄西山的人在黃昏時(shí)追逐太陽、追逐光的故事。千手觀音像和其他佛教雕刻則暗示了伊文思的信仰已經(jīng)從早年的馬克思主義轉(zhuǎn)向了希臘式的多神教。
紅領(lǐng)巾也不再是一種政治信仰的宣示了,甚至是唱著《我們是共產(chǎn)主義接班人》,舉行著“‘發(fā)展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推廣科學(xué)種田,的大會(huì)”,社會(huì)主義符號也僅僅與嫦娥奔月、李白醉酒的神話混合在一起,從而被中立化了。沙漠和黃土地也脫離了原來在中國版圖中的象征意義,而成為伊文思本人地貌觀的注腳,在他的Periplum中,自然界的風(fēng)與巖石、土壤、樹木、動(dòng)物、人之間產(chǎn)生密切而微妙的互動(dòng),以一種日積月累的變化傳達(dá)著關(guān)于變遷的知識(shí)。
影片中的風(fēng)更有多重的含義。首先,它是風(fēng)車之國——荷蘭的歐羅巴之風(fēng)。其次,它是中國文化中特有的風(fēng)。在中醫(yī)中,風(fēng)與人體的不協(xié)調(diào)互動(dòng)造成身體的病灶,影片中的醫(yī)生提示說:秋天到了,風(fēng)要來了,注意身體。風(fēng)預(yù)示著季節(jié)的循環(huán)。最后,風(fēng)還是宇宙之風(fēng),是神秘、無限的事物在影片中的在場,風(fēng)是“氣”,是以太的自然涌動(dòng),是空氣裹挾著物質(zhì)粒子的自然流散。
相比而言,當(dāng)代社會(huì)在伊文思的這部影片中被稀釋了,這甚至可以說是伊文思最與時(shí)代無關(guān)的一部電影。
“到前線去的旅程,喚起了對彩色的意識(shí)。我對風(fēng)景產(chǎn)生了一種新的感覺。過去,一幅風(fēng)景油畫,對我從來不產(chǎn)生任何個(gè)人的喜愛。我到荷蘭博物館去參觀的時(shí)候,向來只觀看人像和有人物的畫。大自然是人物活動(dòng)的背景,意義不大,即使是布魯蓋爾的風(fēng)景畫,在我看來,也不過是前景中人物生活、活動(dòng)和舞蹈的背景罷了。萊斯達(dá)爾斯和霍比馬斯的作品,對我的意義更小。”
在《愚公移山》的訪談中,他還說:
“我們多選擇城市,少拍農(nóng)村,主要是因?yàn)檗r(nóng)村的生活節(jié)奏比較慢,季節(jié)長,要求蹲點(diǎn)的時(shí)間也就多……我們覺得西方城市里的觀念對鄉(xiāng)村生活的興趣也許不大,至少是不夠關(guān)心的。”
如今,他完全放棄了對城市的表現(xiàn)。也許他再也不嘗試去愉悅自己預(yù)期的歐洲觀眾了。否則,他也不會(huì)在電影中引用李白的詩。
燕草如碧絲,秦桑低綠枝。當(dāng)君懷歸日,是妾斷腸時(shí)。春風(fēng)不相識(shí),何事入羅幃。
這些對一個(gè)非中文讀者能意味著什么呢?
他還拍山間的云霧、松樹、棧道,拍毀棄的長城。這些云霧本該是自然的,沒有文化色彩的,但是,在伊文思這里具有了禪意,是對世界的無窮變化和組合的可能性提示。
坐在椅子上,寡言少語的伊文思,意識(shí)到自己成為了紅領(lǐng)巾們的對立面。他也自覺地與時(shí)代擺開了距離,一種并非冷冰冰但卻更加冷靜,并非放棄立場但更加從容、詼諧的距離。詩意來自于他頭腦中對無限事物的并置。因此,這部電影也是一個(gè)20世紀(jì)人對于自身潛意識(shí)的集納箱。他希望在隱喻與隱喻之間建立一種更加漂泊的、不及物的關(guān)系,于是,現(xiàn)實(shí)的考量就漸漸被放在次要的位置了。
伊文思對于元電影的自覺思考體現(xiàn)在這部“最后的電影”對影史最早的科幻電影——梅里愛1902年的《月球旅行記》的互文中。
坐在月球上的不再是一個(gè)法國式的金發(fā)女子,而是一個(gè)有中國古典裝飾的女子,伊文思嘗試在畫面中和她對話。她講述和自己的丈夫——后羿的故事。其實(shí),嫦娥的意象在文革中已經(jīng)因?yàn)槊珴蓶|的悼亡詩《蝶戀花·答李淑一》而變得革命化了。直到1978年,領(lǐng)袖去世兩年后,中國仍然發(fā)行了一部叫《蝶戀花》的電影,講述領(lǐng)袖第一任夫人、親密戰(zhàn)友楊開慧的故事。電影把領(lǐng)袖的悼亡詩改編成神話穿越故事,其中個(gè)人青春情結(jié)與民族成長敘事之間的轉(zhuǎn)化機(jī)制,是值得繼續(xù)探討的。
而在《風(fēng)的故事》中,月球僅僅成為一種漂泊的幻想。伊文思把紀(jì)錄片推到了與其類型最遠(yuǎn)的地方——自傳與科幻。
高唱“君不見高堂明鏡悲白發(fā)”并為攬水中之月而溺亡的李白,也是伊文思的鏡像。在電影中,他是否最后意識(shí)到自己所捕捉的也不過是一枚虛構(gòu)的月亮呢?
嫦娥:“月球上沒有風(fēng)。沒有一絲的風(fēng)。”
幸運(yùn)的是,伊文思并沒有通過神話走向復(fù)古主義。他的神話處于20世紀(jì)現(xiàn)代科學(xué)的邊沿上,是一種被當(dāng)代意識(shí)所提升和轉(zhuǎn)碼了的神話。因此,如今能夠幻想出的嫦娥的月球,也使人想到它是一個(gè)阿姆斯特朗已經(jīng)登陸、并留下過腳印的荒漠,那里空氣稀薄,沒有人煙。
同樣,伊文思首次使兵馬俑活了過來,并且按照西方式的慣常理解,把面具(persona)進(jìn)行了人格化的處理。我們在影片中看到一群兵馬俑(伊文思站在中間)朝觀眾走來。
他拍的兵馬俑,甚至被認(rèn)為是假的(旅游景點(diǎn))。這正好預(yù)言了那年關(guān)于旅游業(yè)中假兵馬俑的新聞。
風(fēng),一種無言的隱喻。這是個(gè)人消弭了行動(dòng)力,但對事物仍然以赫拉克利特式的觀念來理解的世界。
我們瘋狂地拍風(fēng)
拍攝不可能之事才是生命中最美好的
我窮盡一生
去捕捉風(fēng),去駕馭風(fēng)
你們會(huì)看到這一刻的到來
伊文思自白道。他拍了風(fēng),拍了風(fēng)箏——龍,拍了試圖用巫術(shù)引來狂風(fēng)的女人,后者以索要兩臺(tái)風(fēng)扇為代價(jià)。于是,伊文思派人給她運(yùn)來了兩個(gè)風(fēng)扇,由駱駝馱著。
沙漠盡頭、坐在椅子上的伊文思,幾乎沒有行動(dòng)的能力了。他從椅子上跌倒,但是,不久又在另外的鏡頭中站起來,試圖跟兒童們交流:
“我從遠(yuǎn)方來,我不懂中文,很遺憾吧。”
他被送進(jìn)醫(yī)院。那么,他是怎么控制拍攝、怎么‘導(dǎo)演,紀(jì)錄片的?他的妻子瑪索琳娜·羅立丹·伊文思(Marceline Loridan Ivens)偶爾會(huì)在鏡頭中露出半張臉。
一個(gè)人的晚年總是有很多東西不是用語言就能夠表達(dá)清楚的,尤其是他仍然懷著童稚心、對世界抱著持續(xù)探索的欲望。
伊文思的晚年,也想通過《風(fēng)的故事》這樣一部故事片——也許是他的所有紀(jì)錄片中,最接近敘事的一部,講述自己一生遇到的事物,不止是東方,也不止是那些象征性的符號,而是符號所提喻的廣闊的世界,是被風(fēng)所改變的地貌、沙漠、植物和人的面容。
在他的晚年,他從來沒有像現(xiàn)在這么從容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