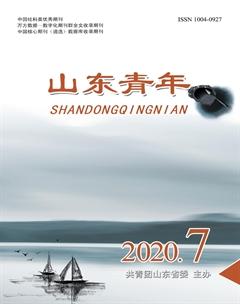正當防衛必要限度的界定
陳欣
摘 要:正當防衛的必要限度問題一直有較大的爭議,在傳統理論上主要有一元論、二元論和多元論三種主流學說的紛爭。二元論的觀點綜合看來是比較妥帖的,但仍需要做出修正和改進,在防衛人的防衛手段過當但沒有造成重大損害的情況下,也不能認定為正當防衛,不能由于對結果的重視而忽略對于防衛行為惡性的考量。近年來有學者提出了“情境論”的主張,該說側重于對防衛人防衛手段的評價,提倡結合防衛人當時所處情境進行綜合評斷,也為司法實務當中如何判斷該問題提供了新的思路。
關鍵詞:正當防衛;必要限度;重大損害
一、學術界主要學說之間的差異
(一)傳統多元論的弊端
如今的刑法學界對于正當防衛必要限度的判斷主要有三種理論的爭議,即一元論,二元論與多元論。
其中多元論的判斷方式的缺陷是顯而易見的,也是通常容易為人所詬病的,該說主張以法官的視角為基準,由法官結合整個案件的情況進行分析從而給出結論。該說提出的目的在于,使法官能夠多方位的考慮案件因素,而不要單一的站在某幾點上做評判,致使重要的細節被疏忽掉,最終的案件結果對當事人有失公允。可這同時也就意味著,沒有統一的判斷標準來評判案件,完全依照法官的個人經驗與情感對當事人作出裁決,給法官的自由裁量權過大的情況下,很容易造成司法不公,以至于民眾對案件的結果產生質疑,從而對司法的公信力失去信心。
(二)一元論與二元論的爭議
支持“一元論”的學者們認為,“超過必要限度”與“造成重大損害”這兩項條件需要綜合在一起進行評價。但是在司法實務當中如果采用這種一體式的判斷方式,卻很容易導致案件判斷方式轉向“唯結果論”:對于防衛人是否構成正當防衛,只需要看他是否造成了重大損害即可,這種評價方式對于防衛人來說顯然是有失公平的。
而二元論的觀點則認為,構成正當防衛需要經過兩道防線的判斷。首先防衛人的防衛手段必須同時滿足比例性和必要性的要求,所謂比例性,就是指防衛行為的強度與侵害行為的強度之間不能明顯失衡,而必要性則是指防衛的手段要盡可能采取最溫和的方式,即能夠有效的制止侵害行為就可以。第二道防線則是對于損害結果的判斷,如果造成了重大損害那么則可以被認定為防衛過當,反之成立正當防衛。
二、對于二元論的改進
(一)合理考慮防衛人防衛手段的惡性
一元論和二元論的爭議雖然激烈,但是在兩種情況下得出的結論是一樣的。當防衛人行為要件和結果要件都過當的情況下,自然構成防衛過當;反之行為和結果都在限度要件以內,則當然成立正當防衛。所以其爭端主要體現在以下兩種特殊情況:一是行為不過當而結果過當,二是行為過當而結果不過當。
筆者認為,二元論的觀點是比較成熟和全面的,對于防衛手段的限度與造成的損害結果給出了比較全面的考察方式,但是依然有其弊端存在。在二元論的觀點下,這兩種情況都不能構成防衛過當。第一種情況下,例如乙盜竊了甲的財物之后被甲立即發現,于是甲轉身追趕逃跑的乙,乙在逃跑的過程中不慎摔倒磕到頭部當場死亡。在這種情況下,甲追趕的行為并沒有超過必要限度,但卻造成了嚴重損害的結果。可是此時甲的防衛目的不過是為了拿回屬于自己的財物,防衛手段也完全符合比例性和必要性的要求,沒有產生過度的惡意,乙死亡的結果顯然不是甲所追求的,因此不能將危害結果歸責給甲,甲的行為仍舊屬于正當防衛。
但在第二種情況下,以二元論的觀點來判斷,正當防衛的成立標準似乎被不合理的放寬了,防衛人無論使用了什么樣的手段進行防衛,只要最后沒有造成損害結果,就依然可以被判定為正當防衛,這顯然忽略了對其防衛方式的評價。例如當一名青壯年男子發現一位行動不便的老人想要對其行兇時,可以選擇的防衛方式有很多種,只需要采取相對輕微有效的方式即可,如果男子此時選擇開槍朝老人射擊,但是由于槍法不準沒有打中,雖然沒有造成老人的傷亡,但是這種手段顯然已經超過了必要的限度。因此男子開槍射擊這一行為中所包含的惡性就不應該被忽略掉,即使沒有造成重大損害,也依然可以被認定為防衛過當,但是可以相比較已造成重大損害的情況從輕或減輕處罰。
(二)區分比例性與必要性的差別
二元論的觀點認為,防衛手段必須同時符合比例性和必要性的要求才能認定為正當防衛,不符合比例性或者不符合必要性依然屬于防衛手段過當,進而再看造成的結果是否過當。但是實務當中卻會將這兩個概念混為一談,這里所講的比例性應當指不能用高強度的防衛行為來防衛低強度的侵害行為,評價的中心應該放在防衛行為與侵害行為強度的比對上面。如果行為本身已經超過了比例性的要求,則無需判斷是否符合必要性的要求,因為此時行為人的防衛手段已經過當。只有在防衛手段符合比例性的要求的情況下,才需要進一步的判斷是否超過了必要性。而必要性的側重點則在于防衛手段已經達到了防衛目的的情況下,是否還繼續造成了不應該有的損害結果。
例如在侵害者持刀行兇的情況下,防衛人也持刀進行反擊來保護自己,這完全符合比例性的要求,如果最終侵害者被刺傷無法正常行動,此時防衛者的目的就已經達到了。至于侵害者的行為應該如何定性,其受到什么樣的懲處,都是國家司法機關人員的工作,作為普通人的防衛者沒有權利對其進行私自的懲罰,因此此時防衛者如果再持刀對侵害者進行打擊,則不能將這種打擊行為評價為防衛行為,而應當歸結為蓄意的傷害,也就是說事后的這種打擊報復行為不符合二元論主張的必要性。
三、對于如何評價防衛人防衛手段的建議
綜合以上觀點來看,對于防衛行為是否過當的判斷還是側重于如何評價防衛手段,近年來有學者提出了情境論的主張,其觀點便是主要考慮如何判斷防衛行為是否超過了必要限度。結合情境論的觀點,筆者認為司法實務當中應當重點判斷以下幾點:
1.防衛人當時所面臨的不法侵害強度。對于侵害強度的判斷可以以侵害人持何種器械為關鍵的參考因素,也需要綜合防衛人受到的傷害來觀察。防衛人所面臨的侵害行為強度越高,就需要相應的采取強度更高的防衛方式。對不法侵害所能造成的損害需要做出事前的判斷,而不是站在事后來得出結論。
2.不法侵害行為是否突然或者緊迫。很多情況下,防衛人是在比較突然的情況下受到不法侵害的威脅,比如說突然從陰暗地方沖出的搶劫者,沒有可能預見到的暴力行兇等等。在這些情況下,由于防衛人心理上沒有絲毫的準備,又加上時間緊迫,所以只能依靠最本能的反應來進行防衛。因此即使在事后發現當時還有更和緩有效的防衛方式,也不能因此苛責防衛人的手段過當。
3.防衛者與侵害者的力量差異。有學者統計了大部分與正當防衛相關的案件當中,有半數以上的防衛人面對的侵害者人數是二人以上。在這種雙方力量差異懸殊的情況下,普通的防衛方式顯然是收效甚微的。
4.周邊環境以及心理因素等。某些案件發生在比較昏暗的環境下,這些例如空間和光線的因素很容易使防衛人的打擊力度和方位產生偏差,造成嚴重的損害結果,所以需求司法人員更細致的加以判斷。而心理因素在案件進行具體判斷的時候比較復雜,需要結合防衛人的年齡,家庭背景,成長經歷,身體狀況等等進行考慮。
結語
對于正當防衛必要限度的判斷過程當中,對于如何理解“明顯超過必要限度”,理論上一直無法給出一個清晰明確的標準。二元論作為緩解一元論困境的新的學說,依然有其自身需要改進的地方。
首先應當從防衛手段進行判斷,如果防衛者的防衛行為與侵害行為之間明顯失衡,則可以認定為防衛過當,如果防衛行為符合比例性的要求卻不符合必要性的要求,則依然屬于防衛過當,但是這兩種情況下,最后依然要看其造成的結果危害性大小,然后在量刑上面做出適當的調整。如果防衛行為符合了比例性和必要性的要求,那么就可以直接認定為正當防衛,即使造成了不應有的損害結果,也就是上述“行為不過當而結果過當”的情況,也不能夠將其歸責于防衛者。
[參考文獻]
[1]鄒兵建.正當防衛中“明顯超過必要限度”的法教義學研究.[J].法學,2018(11).
[2]張明楷.防衛過當:判斷標準與過當類型.[J].法學,2019(01).
[3]尹子文.防衛過當的實務認定與反思——基于722份刑事判決的分析.[J].現代法學,2018(01).
(作者單位:沈陽師范大學,遼寧 沈陽 1100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