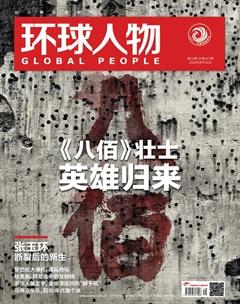毛姆,一邊毒舌一邊愛這個世界
毛予菲

威廉·薩默塞特·毛姆(1874年一1965年)
英國評論家康納利曾說:即使一切消亡,仍然會有一個作家講述的世界留存下來。
對于小說家威廉·薩默塞特·毛姆,他留下的世界覆蓋“從新加坡到瑪貴斯礁群島的一片海洋和土地”。令毛姆聞名全球的《月亮與六便士》,寫的正是這里的故事。他的許多短篇小說,描繪的也是這里的風土人情。
與《月亮與六便士》等暢銷長篇相比,毛姆的短篇故事在中國的熱度一直有點低。其實早在1951年,毛姆就出版了4卷本短篇小說集:《愛德華·巴納德的墮落》《人性的因素》《英國特工阿申登》《紳士肖像》,共收錄91個故事。他親自確定了篇目和順序,并為每一卷撰寫序言。1963年,著名英語圖書出版商企鵝出版社推出新版,自此被認作標準本,多次重印。在標準本的基礎上,一些中文譯本也已零星出版,得以與中國讀者見面。
商務印書館理想國出版社的編輯大概是認為,中文世界也應該有一套完整的“毛姆短篇小說全集”,于是在2014年找到“愛讀毛姆的陳以侃”。陳以侃畢業于復旦大學英語系,那年他29歲,“毛姆不難,但4卷本短篇全集畢竟快150萬字,大概是看我年輕力壯吧……”
無論長篇還是短篇,毛姆作品中文譯本繁多,譯者數量也不在少數,陳以侃卻絲毫不怯場。2016年—2020年,全新毛姆4卷本短篇小說集陸續出版,陳以侃以嚴謹、平實的語言,高度忠實原著精神的筆觸,取得了不俗口碑。2017年,陳以侃入圍了第二屆“單向街書店文學獎·年度文學翻譯”,評語是:“陳以侃對毛姆短篇小說的翻譯,是一次重新的開掘。”
“從痛苦的回憶中解脫”
如果要以作品觀照毛姆的一生,長篇小說《人性的枷鎖》和《月亮與六便士》應該是最合適的選擇。在陳以侃看來,毛姆寫這兩部小說時,都有指向自己的本意。“自卑孤僻的菲利普是毛姆自己,真正的藝術家思特里克蘭德則是他想要成為的人。”
毛姆出生在英國一個律師家庭。他8歲那年,母親因難產而死,兩年后,父親因胃癌去世。孤苦伶仃的毛姆只得被送到伯父家寄養。入讀坎特伯雷國王學院,毛姆又因嚴重口吃,被同齡孩子欺負。童年的痛苦經歷,在他心里留下了無法抹去的陰影。
畢業后,毛姆在伯父的建議下,入讀倫敦圣托馬斯醫學院。在醫院做助產士的同時,毛姆開始了寫作。最初獲得觀眾青睞的作品,是他寫“愚蠢上流社會”的幾個劇本。1908年,倫敦西區同時上演了毛姆的4部戲劇,讓他成為紅極一時的劇作家。當時英國一家媒體刊登了一幅漫畫,畫中莎士比亞蔫蔫地站在毛姆的戲劇海報前,痛苦地咬著自己的手指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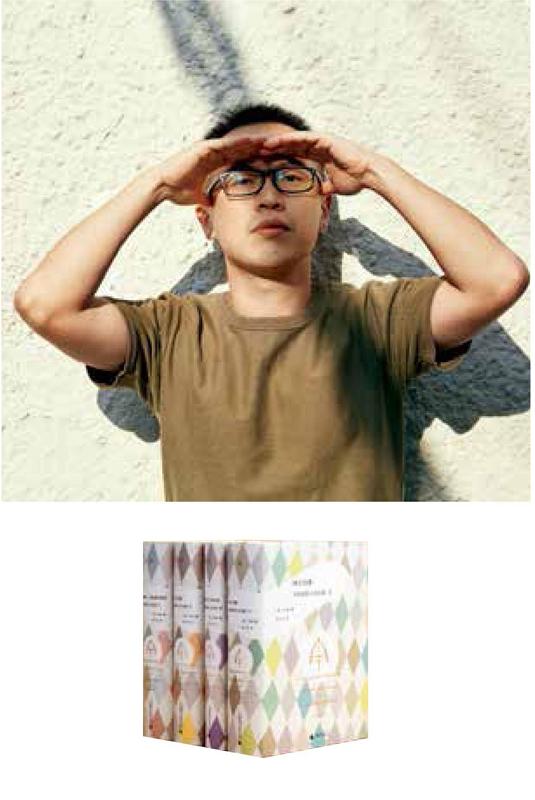
陳以侃:1985年生于嘉善,新銳譯者。2016年起,由其擔綱獨譯的4卷本毛姆短篇小說集陸續完成。近日,第四卷《紳士肖像》出版。
一直渴望獲得尊重和贊譽的毛姆,成功進入了倫敦的名流社交圈。成名后的某天晚上,他獨自在俱樂部吃飯,聽到鄰桌小聲談論著自己。“你認識毛姆嗎?”其中一個問。另一個嘲諷:“當然,他腦袋膨脹得連帽子都戴不上了。”開始,毛姆并沒有把這樣的對話當回事,但不久,越來越多刺耳的羞辱與批評灌進了他的耳朵。
毛姆回憶起童年,痛苦的經歷好像又統統回到了身邊。他翻出了自己在23歲那年完成的小說草稿《灰燼其華》,“感謝當時沒有一家出版社愿意買下它”。毛姆重新拾筆,還給它另起了個名字——《人性的枷鎖》。
這是一部半自傳體小說,其中很多情節源自他人,但感情都是毛姆自己的。主人公菲利普和毛姆的童年極其相似。書中那個敏感害羞的男孩天生患有腿疾,父母早亡,小小年紀被送去古板守舊的伯父家寄養。菲利普的人生道路一點都不順暢,在經歷了不少痛苦后,他才逐漸解除了宗教、學歷、愛情、世俗期待等加諸一生的種種枷鎖。菲利普最終在“毫無意義的人生”中獲得了心靈平靜。小說完結,毛姆也徹底釋放了內心的壓抑:“我永遠地從痛苦回憶中解脫了。”
1915年,《人性的枷鎖》在“一戰”中出版發行。小說最初在倫敦的反響不算好(后來成為暢銷書,毛姆生前共賣出1000萬冊),但毛姆不愿再理會這些聲音。第二年,他放棄了名流社交圈的生活,毅然前往南太平洋旅行。隔著一片汪洋,遠離各種麻煩,毛姆開始為下一部小說搜集素材。回倫敦后不久,他一生中最暢銷、最出名的代表作《月亮與六便士》誕生。
小說基于法國后印象派畫家高更的一生,講述了一個關于“逃離”的故事。一個40歲的證券經紀人,突然對藝術著了魔,放棄了優渥生活,跑去南太平洋的塔西提島,追求藝術理想,成為一名畫家。實利與精神之間,他選了后者。“滿地都是六便士,他卻抬頭看見了月亮。”
1919年4月,《月亮與六便士》率先與英國讀者見面,不出所料地遭到了媒體譏諷。但轉機很快在大洋彼岸出現:同年7月美國版推出后,首印5000本被搶購一空,同年底,銷售數據飆升至10萬冊。一直到今天,這部書仍是全世界最暢銷的小說之一。

《人性的枷鎖》和《月亮與六便士》。
故事背后是“人性”
然而,長篇小說《月亮與六便士》并不足以成就今天的毛姆。美國社會學家伯吉斯曾評價:“毛姆還寫下了英語文學中最好的短篇故事。”
毛姆在年輕時就寫過一些短篇,但都未被收入那部4卷本小說集。收進集子的第一個故事《雨》,是毛姆在53歲時完成的。《雨》最初的命運看起來和他年輕時寫的那些書一樣,被一個又一個編輯拒絕。但毛姆不介意,他繼續寫。當寫完6篇時,這些短篇都被發表在雜志上,獲得全球讀者的喜愛,其中包括奧威爾(《動物莊園》作者)和馬爾克斯(《百年孤獨》作者)。
在這4卷本短篇小說集里,有一些故事與“一戰”時的歐洲有關。“一戰”中,已是知名作家的毛姆受英國軍情六處派遣,赴歐洲大陸從事秘密情報工作。這段“浪漫又荒謬”的經歷,在多年后化作一系列獨立的間諜小說,集結成全套小說集中的第三卷《英國特工阿申登》。這部作品后來被譽為最偉大的英國間諜小說之一,影響了包括“007”之父伊恩·弗萊明在內的眾多作家。
小說集里的更多故事,則發生在濕熱的南太平洋小島。在《雨》《書袋》《愛德華·巴納德的墮落》等篇目中,熱情野蠻的土著人與帶去現代文明的英國殖民者,源源不斷出現在他的筆下。
誕生于旅途中的小說,最能讓讀者見識到世界的多樣性。毛姆的短篇故事光怪陸離、撩人心弦:偏執、專橫的基督徒被自己的欲望反噬;控制欲極強的母親,利用風箏攪渾了兒子的婚姻;美國媳婦嫁到意大利后出軌公公,結果兒子殺死了父親……英國作家格雷厄姆·格林覺得:讀毛姆停不下來,是因為這些逸事秘聞有種內在的力量。
其實講故事的毛姆自己也很享受傳遞八卦的樂趣。他知道,這些“樂趣”背后,有一個共同支撐點——人性。
不過在陳以侃看來,毛姆又和其他那些“專寫人性之惡”的作家不一樣。“毛姆筆下,人性是復雜的。”《月亮與六便士》中,他就曾借藝術家之口說出了這種多樣性:卑微與偉大、善良與惡毒、熱愛與仇恨,可以互不排斥地并存在同一顆心里。毛姆愿意相信:人的心眼都不壞。我們只是因為腦子不好,思考不足,所以才走向了歧途(《六十自述》)。
從1927年《雨》出版,至其后的20年,是毛姆創作短篇小說最豐富的20年。這個時期的毛姆,斷斷續續進行著他的異國之旅。“剛剛出發時,毛姆更多是為了逃離倫敦,擺脫羈絆,享受旅行帶來的自由感。但后來,目的變了,變成了強烈的求知欲和好奇心。”毛姆在世時,就經常將自己的旅行比作“一個動物學家闖入一個物種信息豐富到難以想象的國度”。他瘋狂吸收著周圍的新鮮事,體驗著“人心的復雜與刺激”。
“80后”粉絲代表
毛姆在世時,對自己在主流文學圈的地位從來沒抱過幻想。20世紀初的歐洲文壇,普魯斯特、伍爾夫等意識流派作家正在崛起。他們擅長用“語言的不確定”寫“人心的不確定”。而毛姆不是這樣的。他寫“外放”的故事,用詞簡潔明了,讓讀者一看就明白。但主流文學圈覺得這很粗俗,不像一流文學家的姿態。

毛姆最暢銷的小說《月亮與六便士》,被翻拍為同名電影。
站在“二流文學家最前列”的毛姆,卻在讀者圈中擁有著無以復加的影響力。就像陳以侃說的:“一代一代的讀者不會錯過他。”“永遠有一幫人覺得毛姆好看。”
“在戰后的歐洲,西方傳統價值觀不斷瓦解,毛姆迎來他的第一批讀者;1964年,毛姆去世的前一年,90歲的他說自己最大的慰藉,就是每天收到全世界青年讀者的來信;過去幾十年,算是太平的幾十年,在安逸庸碌的生活中,人們向往逃離,又都‘毛姆了起來;把毛姆放在當下,他看起來與我們的時代精神不合,因為這個時代的人們總是像上了發條一樣。但正因如此,毛姆才值得永遠閱讀。他的故事,可以替任何地方、任何時代的讀者完成‘去世界看看的心愿。”
在中國,毛姆向來不缺粉絲。張愛玲喜歡毛姆,她的力作《沉香屑:第二爐香》就是以毛姆的文風為典范而創作的。王安憶推崇毛姆,她尤其喜歡毛姆簡約的筆法以及他對人性的犀利洞察。
作為“80后”的粉絲代表,陳以侃讀毛姆,最初是上了“一位董先生的當”。陳以侃中學時熟讀董橋文集,這位熟悉英國文學的香港作家一直認定,“這世上寫英文是沒人能寫得過毛姆的”。大二從電子信息與電氣工程專業轉去英文系,董先生那句“帶著床頭的毛姆短篇出門”,陳以侃也跟著學了起來。
在大學,最難忘的閱讀體驗基本都是帶著場景的。“找一間破教室,一個故事讀完了去一趟盥洗室,回來的走廊上,氣氛迷離極了,好像拐角處會隨時款步走出新近喪夫的公爵夫人(《事關尊嚴》)。毛姆真的適合帶著出門,因為他的短篇可以只用半頁,就讓你落進他的氛圍里。”
最近幾年,陳以侃有一半時間都在重讀毛姆。“毛姆真是厲害,當初打動我的東西,現在還是經常打動我。”接下翻譯的活兒,陳以侃又覺得:“毛姆真是體貼。他的文字就像說話一樣,翻譯毛姆的過程非常順利。”
像個傻男孩一樣解剖自己
陳以侃認為,有些讀者對毛姆可能有“誤解”。他毒舌刻薄、傲慢無禮,在讀書隨筆中揶揄了不少文學前輩,還寫信怒懟特地來感謝自己的新人作家。但毛姆并不是一個冷漠的人。他是一邊毒舌,一邊愛著這個世界的。在小說里,他會對激情燃燒的藝術家流露贊美之情,而道貌岸然的文明人都被他當成庸俗的魔鬼。
鮮少有人知道,毛姆60歲時寫過自述,毒舌自己。他的語言犀利,背后卻暗藏純真與情懷。比如毛姆對自己寫完的作品充滿厭惡,當他知道一條街上的劇院正在上演他的戲劇時,要繞道走;他討厭評論家,又忍不住偷偷看大量評論,把夸贊他的人引為知己;他反復強調自己靦腆、害羞、不擅社交,但又渴望結識陌生人、得到故事。有讀者說:毛姆最有趣的時候,或許就在于他像個傻男孩一樣剖析自己。
“二戰”爆發前后,毛姆通過催眠療法治好了口吃,又開始回到了倫敦社交圈。他四處演講,上廣播節目,接受訪談,并設立“毛姆文學獎”,資助文學創作者旅行。公眾普遍認為,作家應該靜謐地生活、寫作,不能和媒體、鏡頭扯上關系。但毛姆活著的時候,就已經成為全英國名氣最大、賺得最多的作家了。
“實在、勤奮、勵志。”陳以侃用這3個詞概括他心中的毛姆。
“如果說毛姆是一個偉大的作家,那是因為他筆下的人性,在跨越一個世紀后,依然能擊中讀者;更是因為,他在窮盡一生探索,發現人生并沒有意義后,依然決定要將其過得有意義。”從這個角度看,毛姆早已站在一流作家的隊伍里了。
威廉·薩默塞特·毛姆(1874年一1965年):英國著名小說家、劇作家。其代表作《月亮與六便士》被認為是現實主義文學最經典作品之一,全球銷量已經突破6000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