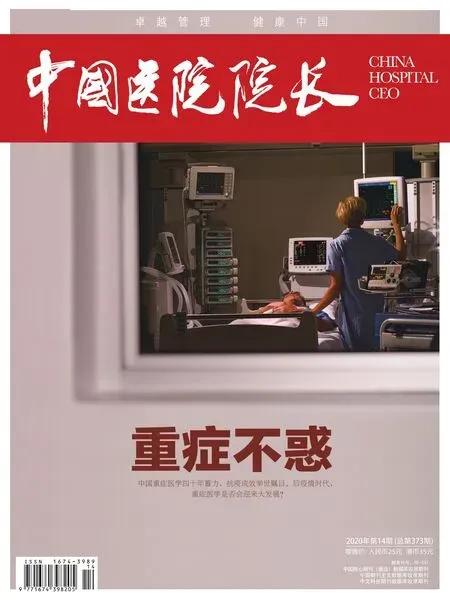完整學科體系建設構成重癥醫學發展的指引與挑戰
——專訪中華醫學會重癥醫學分會第三屆主任委員、東南大學重癥醫學研究所所長邱海波
文/本刊記者 黃柳

邱海波中央疫情防控指導組專家組成員國家衛生健康委專家組專家東南大學中大醫院黨委副書記著名重癥醫學專家
在致力于打造規范化同質化重癥醫學診療體系的同時,重癥醫學正在構建和完善“預警—救治—長期預后”的大學科體系。
“最早的出征,最久的堅守!”“從嚴冬到盛夏,轉戰鄂黑吉,與疫情鏖戰139天”……這些都是中央疫情防控指導組專家組成員、國家衛生健康委專家組專家、東南大學中大醫院黨委副書記、著名重癥醫學專家邱海波教授過去數月的真實經歷寫照。
從2005年四川省豬鏈球菌病疫情,2008年汶川地震救治危重傷者,2009年甲型H1N1流感疫情,2010年玉樹地震……邱海波都奮戰在最前線,且一直講著同一句話,“在最具挑戰的現場,給病人最多的生命機會,這就是ICU醫生的使命!”
從1月19日開始,在湖北武漢新冠肺炎重點疫區,他先后參與了第2版到第7版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診療方案》的制定工作,明確了重癥、危重癥患者治療路徑。
4月24日,武漢重癥新冠肺炎患者清零!
4月26日-6月5日,邱海波轉戰黑龍江、吉林,指導重癥患者的救治。
6月5日,邱海波圓滿完成國家賦予的使命,返回南京;回到東南大學中大醫院重癥醫學科——他和團隊“與死神搶人”的日常主戰場;6月18日,邱海波教授在辦公室接受了《中國醫院院長》雜志記者電話專訪,回溯重癥醫學學科發展,暢談他對學科體系建設的思考,以及在他心目中重癥醫學科長期面對以及仍將面對的重重挑戰……以下為本次采訪部分內容的歸納與總結。
今年是南丁格爾誕辰200周年,其實重癥醫學的萌芽與這位現代護理學奠基人密切相關。19世紀50年代的克里米亞戰爭中,南丁格爾為了降低戰傷感染率而對重傷士兵進行集中護理,這是重癥醫學監護的雛形。到了20世紀20年代,約翰霍普金斯醫院的神經外科專家發現,腦外科手術后患者病情變化特別快,術后的觀察與處理的重要性不遜于手術技藝,因此他們開出了最早的重癥監護床位,也是神經外科ICU。1971年美國重癥醫學會成立,標志著重癥醫學正式誕生。重癥醫學由最初的加強監護單元發展成為獨立的一門醫學學科。
總結來說,伴隨現代醫學的發展,專科亞專業化加速,專科越分越細;在此背景下,有一類患者,隨著病情的發展,其救治必定是超過專科范疇的;從這個角度來看,重癥醫學科的出現與發展是必要的,也是必然的!
正如美國神經外科最早開出重癥監護病房ICU,很多外科侵入性較強的手術,術后監護直接影響了患者存活率。以國內醫療糾紛較多發的脊柱、頸椎手術為例,很多手術操作特別順利,但由于手術過程難以避免的觸碰,導致頸髓微小部分出血、水腫,隨后髓內壓力升高壓迫到了膈神經,進而影響到呼吸功能。如果術后監護及時發現并給氧,患者可安然度過;若不能及時發現,則生命指征可能急轉直下,無可挽回。因此密切、專業的觀察與處理非常重要。與此同時,面對復合型、多發性疾病并且危及患者生命的情況,有一組醫護團隊可以通過抗休克、抗感染、復蘇等多重技術手段,將患者的生命體征控制住,重癥醫學正發揮出跨專業緊急救治、守住生命最后一道防線的無可替代的功能。
在生命被危及,一定的時間階段內,器官衰竭的歷程是有規律可循的;規律包括器官之間的相互影響機制,肌體經歷的共同的病理、生理過程。
因此,重癥醫學涉及神經、血液、消化、呼吸等多系統以及多器官、多學科的診斷、綜合性理解與救治,專業性、學科性特別強。
合格的重癥醫學科醫生需要滿足三項基本要求:第一,了解各類的原發病,具備系統、綜合性的醫學知識;第二,懂得各個系統疾病以及不同的損傷導致器官衰竭的機制是怎樣的;第三,掌握生命支持技術,懂得在合適的時機用恰當的技術,守住生命的最后防線。學理念與思想武裝的一批醫務人員。院長、醫院管理者應該要了解,醫院經過專業化培訓、掌握了重癥醫學理念與技術的醫生,遠比設備更重要、更有價值。
現代醫學及技術發展到今天,器官功能支持的技術已經非常強大了,我國一些三級醫院的相關硬件與設備絲毫不遜色于西方發達國家,但我們需要提升的,正是在恰當的時間或時機,給病人恰當的器官支持或生命支持手段,國際慣常的表達是Right Time,Right Therapy。
以這次疫情中新冠肺炎重癥患者的救治為例,重癥醫學科醫生的生命支持技術有很多種,有鼻導管吸氧、氣道插管、有俯臥位、有ECMO等,但在什么時機應該用什么,對不同的病人應該怎么用;如何判斷并合理施治,恰是考驗重癥醫學科醫生的救治思維與水平的時候。比如俯臥位通氣,我們發現對重癥患者效果很好,且不依賴于設備;但要將插管的患者翻身,還要避免病人身上各種插管的脫落和損傷,這一定是考驗醫護的技術活,也是力氣活!
合格的重癥醫學科醫生需要滿足三項基本要求
◎第一,了解各類的原發病,具備系統、綜合性的醫學知識。
◎第二,懂得各個系統疾病以及不同的損傷導致器官衰竭的機制是怎樣的。
◎第三,掌握生命支持技術,懂得在合適的時機用恰當的技術,守住生命的最后防線。
不可否認,類似ECMO這樣的高端設備讓全社會更加關注到重癥醫學;但我對以昂貴、復雜性設備作為學科力量的衡量標準持審慎與保留態度。權威的研究也表明,在ECMO的年使用例數為個位的機構,使用ECMO事實上是增加了死亡率;而在年使用例數在10~20之間的機構,ECMO的應用并沒能降低病死率。從臨床實踐來講,是否使用ECMO需要對先決條件予以科學評判,因為你給上去,需要什么模式、隨著生命體征的變化如何調整,這些細節都決定了病人的病情會往哪個方向走。
重癥醫學的救治水平與能力,一定程度上有設備發揮的助力,但更重要的決定因素是有重癥醫
重癥醫學科不能僅關注已發生器官功能衰竭的患者,應將關口前移,實現早期救治。而對經重癥醫學救治存活的患者,近期大量研究對其轉出重癥監護病房ICU或出院后的健康狀況和遠期預后進行調查發現,結果并不樂觀,伴隨疾病產生的心理和生理問題嚴重影響后期生活質量和遠期預后。改善生存質量,提高遠期預后,是重癥醫學治療的最終目標,亦應成為重癥醫學大學科體系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
在東南大學中大醫院,我們多年前開始踐行國際通行的“重癥監護快速反應小組”CCRRT(Critical Care Rapid Response Team)的理念,將劃分出神志、呼吸、血液循環、氣道、心率等多指標、多維度的“重癥量表”,發放到不同專科;專科在實施患者的量表評估時,一旦發現指標危急,可以請重癥醫學科會診、提前介入,這樣患者就不會出現危及生命的問題。這種工作模式取得了一定成效,但與理想中學科戰線前移的狀態尚有差距。
2018年,醫院重癥醫學科入選了國家疑難病癥診治能力提升工程,獲得了一定數目的項目支持資金。于是去年我們開始籌備“TELE ICU”項目,就是在全院普外科、腦外科等重點科室,一共選取300~400張專科床位,設置床旁“簡裝版”重癥監護功能。這其中融入可穿戴設備實時數據采集、人工智能輔助分析等要素,相當于將ICU就落到科室。我們醫院ICU床位是有限的,短時間內也不可能大幅增加。因此,“TELE ICU”的項目中我們設置了院內的遠程ICU中心,通過實時的數據傳遞,預警通知,能實現將戰線前移。秉持不能讓重癥患者越來越多的初衷,這個項目在論證階段也得到了各專科的普遍支持。
關注早期康復、改善長期預后是重癥醫學重要任務。重癥患者在轉出ICU后經常面臨不同程度的生理和心理問題,包括運動能力下降、思維遲緩和理解能力下降等認知障礙、睡眠障礙、焦慮或抑郁等精神心理障礙等,這些癥候群稱為重癥醫學科后綜合征(PICS)。
著眼重癥醫學科后綜合征的問題,中大醫院的重癥醫學科近年積極倡導早期康復以及早期心理干預,也付諸了相關的實踐。對病情尚嚴重的患者,哪怕還插著管、連著呼吸機甚至是ECMO,在度過了最危急的階段后,我們都鼓勵他能坐到床邊、下床直立。因此,臨床操作中提倡將鎮痛、鎮定的藥物,該停的及早停掉,讓患者可以更早地活動,這樣在重力的作用下,其肌肉力量、膈肌力量開始恢復,感染也會減少。
優化重癥醫學科期間的治療,包括合理鎮痛鎮靜、改善睡眠、自主呼吸調整和延長探視時間等均有助于緩解患者譫妄和精神心理問題。早期主動運動和康復則有助于改善患者運動能力、促進呼吸肌力恢復、提高免疫功能等;更重要的一點還包括提升患者的自信心。
隨著病情好轉,患者離開ICU,如果是轉到別的專科病房,我們會按常規將重癥后患者的康復建議給到科室,并保持持續的溝通;而對于出院患者,醫院則為他們開設了ICU后門診。
重癥醫學科后門診的開展實現了對轉出患者病情的連續監測與評估,有利于及時制定相應的干預措施早期治療。相信包含重癥、康復、心理等的多學科協作模式必將促進重癥患者遠期生存質量和長期預后的改善與提高。

作為碩士和博士學位授予點,東南大學附屬中大醫院重癥醫學科培養的重癥醫學人才遍布全國31 個省區市。
總結而言,我國重癥醫學科走到今天,面臨的最大挑戰是構建更強有力、更完整的重癥醫學學科體系。在重癥醫學領域我們的最新思考,也是學科發展的三方面理念,構成學科未來發展的指引。
思考一,我們需要將重癥醫學的戰線前移,做到預警、提前處理,不能等著重癥患者越來越多。
思考二,我們如何融合重癥的理念與技術,實現恰當的治療,對于已經發生器官衰竭的患者,怎樣實施生命支持、中止病程實現逆轉?相信通過住院醫師規范化培訓以及過去持續推進的重癥醫學領域的繼續醫學教育與培訓,在整體水平上我們能得到較大的提升。
思考三,走出ICU之后,患者怎樣高質量地存活以及生活;ICU的早期康復、改善長期預后刻不容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