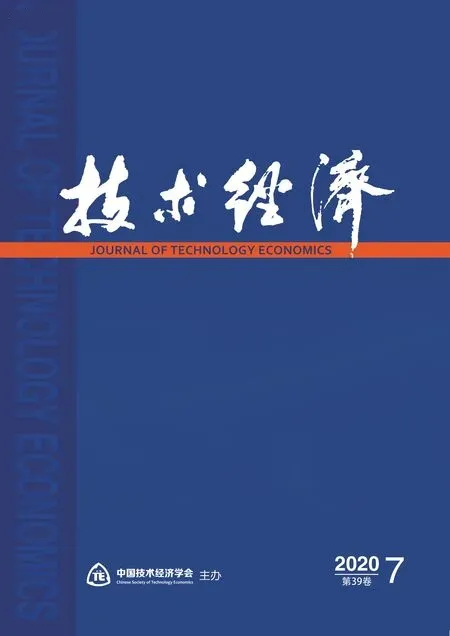“絲路經濟帶”核心區物流非均衡發展態勢及其效應
——以陜西省城市樣本為例
陳 恒,劉 柯,楊 帆
(西安工程大學管理學院,西安710048)
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之后,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了新的區域發展戰略思想,多次強調要繼續實施區域協調發展戰略,并將其作為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的重點任務。而培育現代物流業,有助于推動產業融合,實現產業升級,提升潛在經濟增長率及經濟發展質量,對實施區域協調發展戰略、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具有重要推動作用。然而,陜西省作為“絲綢之路經濟帶”核心區域,長期以來由于南北區域跨度大(處于北緯31°42′~39°35′),且陜西省地勢呈南北高、中間低,由高原、山地、平原和盆地等多種地貌組成,引致陜北、關中、陜南城市群經濟發展的要素稟賦具有較大差異,并導致陜西省產業結構和生產力布局存在區域異質性、區域運輸結構不合理和協同性不足等問題,直接影響了陜北、關中、陜南物流需求總量和水平,導致陜西省物流業發展長期處于非均衡狀態。2011年以來,我國產業從東部向中西部轉移趨勢較為明顯。在此過程中,西安作為陜西省的省會城市則順利承接了部分東部產業,但是西安市原有的技術相對落后的產業卻并沒有按照區域梯度理論向周邊城市順利轉移,主要原因除產業配套不全外,更為重要的是物流成為產業轉移的制約因素。例如,由于陜西省物流非均衡發展態勢較為明顯,導致不同區域的物流承載力及其服務能力具有差異,因而西安市原有產業在空間布局上更偏好于物流承載力及其服務能力較好的西安城市圈,較少考慮陜北和陜南地區。并且處于陜北和陜南地區的企業也有極強的意愿遷離本地區而向西安城市圈集聚。因此,通過何種方式緩解或逐漸消除陜西省物流非均衡發展態勢,促進物流業形成區域產業新體系,成為“絲路經濟帶”核心區域陜西省區域協調發展與經濟高質量發展中一個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
一、文獻綜述
對于非均衡發展的理論和概念研究,按照其適用性可以分為兩類:一類為無時間變量,主要包括循環累積因果論、不平衡增長論與產業關聯論、增長極理論,中心-外圍理論、梯度轉移理論等;另一類有時間變量,主要以倒“U”型理論為代表。盡管以上理論具有一定差別,但是均認為非均衡發展是區域經濟差異的表現形式,并且在社會經濟發展中處于常態化,而均衡發展則被認為是一種偶然[1]。然而,在社會經濟發展中追求均衡發展卻是學術界和實業界普遍關注的焦點。在有關非均衡發展的概念闡述中,眾多學者從不同視角對非均衡的內涵進行了分析,均認為非均衡的實質就是差異性的具體表現。代表學者有孫曰瑤[2]和周建國[3],而孫曰瑤[4]早在1999年就對我國區域經濟發展的非均衡概念進行了探討,認為經濟發展非均衡的內涵實質為地區發展的差異。周建國[5]通過對社會資本非均衡的含義進行梳理分析,認為非均衡主要指社會資本在不同時間、空間位置上的存量不同,使得社會中處于不同位置的人對社會資本的擁有量有著先天的差異。
在非均衡發展成因研究方面,現有研究主要關注兩個方面:第一,產業非均衡發展的成因研究。眾多學者的研究更多關注于金融業、旅游業以及教育業,如王永龍[6]、李樹和魯劍陽[7]、王雪和何廣文[8]從不同視角采用不同指標對金融業非均衡發展的成因展開了研究。鄭鵬等[9]、喬華芳等[10]對旅游業非均衡發展的成因進行分析,并提出了實現旅游業均衡發展的對策。趙春雷[11]、焦秀煥等[12]對我國教育業非均衡發展的成因進行了研究。在物流業非均衡發展研究方面,國內外學者更多關注物流業發展的影響因素,較少涉及物流業非均衡發展。在影響因素研究中主要從信息化[13-16]和基礎設施[17-19]等視角展開研究。第二,經濟非均衡發展的成因研究。王松奇[20]研究認為受投資擴張沖動、超前消費傾向等影響,我國區域經濟呈現非均衡發展。魏后凱[21]從國際直接投資(FDI)角度探索了我國區域經濟增長,研究發現我國區域經濟非均衡發展的主要成因在于對FDI的吸引力差異。與魏后凱[21]相似,廉麗娜[22]采用同樣的指標對甘肅省經濟非均衡增長成因進行分析,并得出了相似結論。張榮天和韓玉剛[23]對江蘇省縣域經濟發展進行分析,研究發現地理區位條件、經濟發展基礎、政策差異對江蘇省縣域經濟非均衡發展影響最大。李健[24]對京津冀經濟非均衡發展的成因進行了研究,結論表明產業結構、投資水平、財政收入以及人口規模是造成京津冀區域經濟非均衡發展的成因。在非均衡發展的影響效應研究中,陳瑾瑜[25]對區域經濟發展非均衡性的外部性進行研究,研究結論表明發展循環經濟有助于消除區域非均衡發展的負向影響效應。但是,吉宏等[26]的研究結論與陳瑾瑜[25]卻不同,其通過對江西邊界經濟非均衡發展的現象研究,指出適度非均衡對社會經濟的發展具有積極的作用,只有非均衡過于顯著才不利于區域經濟協調發展。
通過重新梳理和系統歸納與本研究相關的文獻,發現涉及非均衡發展的理論研究較多,但缺乏對非均衡發展的態勢分析,且量化研究較少。在非均衡發展的成因研究中,主要關注兩個方面:第一,產業非均衡發展的成因。在構建現代化經濟體系中,物流是現代經濟體系的重要構成,而現有研究對該行業的研究關注較少。第二,經濟非均衡發展的成因。現有研究多從宏觀層面對經濟非均衡發展成因進行了研究,但是對如何促進經濟協調發展卻并未涉及。此外,盡管有少量學者分析了非均衡的影響效應,但由于我國區域發展具有明顯差異性,所得研究結論并不一致,尤其是對物流非均衡發展的影響方向仍不明確。陜西省作為“絲綢之路”經濟帶的歷史起點,對發揮陸上貿易具有承東啟西的重要作用,物流發展水平對國際貿易具有重要的影響。若陜西省物流非均衡發展在長期內不能得到緩解,不僅會影響陜西省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速度,也會對國家“一帶一路”倡議的順利實現帶來不利影響。然而,現有研究較少關注“絲路經濟帶”核心區域的陜西省物流非均衡發展問題。基于此,在借鑒現有研究的基礎上,本文進行了以下擴展:①從物流要素集聚和物流通達性角度,定量化了陜西省城市物流非均衡發展態勢及其收斂性特征;②探索了陜西省城市物流非均衡發展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效應;③結合影響效應,對緩解陜西省城市物流非均衡發展的關鍵因素進行了識別,并對影響關鍵因素變化的路徑進行了分析。
二、“絲路經濟帶”核心區域:陜西省城市物流非均衡發展態勢測度及其收斂性分析
(一)陜西省城市物流發展現狀
本文采用物流要素集聚能力、物流通達性兩個指標來衡量陜西省城市物流發展現狀。其中,物流要素集聚能力分別采用物流貨運量和客運量兩個變量作為替代變量;而物流通達性主要采用貨運周轉量和客運周轉量兩個變量作為替代變量。具體分析結果如下。
1.陜西省城市物流客運要素集聚能力及其演進趨勢
本文將物流客運要素集聚能力分為累計綜合能力和平均綜合能力,其中累計綜合能力為2009—2017年客運量的累計值替代;平均綜合能力采用2009—2017年平均值替代。計算結果如下:西安市客運要素集聚累計綜合能力排名第一,咸陽第二,渭南第三,寶雞第四,漢中第五,安康第六,延安第七,榆林第八,商洛第九,銅川第十。分三大區域觀察:陜西省關中地區物流客運要素集聚累計綜合能力高于陜南地區,陜南地區高于陜北地區。而陜西省城市物流客運要素集聚平均綜合能力也表現出相同的排名。
從物流客運要素集聚能力的動態演進過程觀察:在2009—2013年期間,西安市物流客運要素集聚能力持續提高;2014—2017年持續下滑。咸陽在2009—2013年期間與西安市的趨勢一致,但是2014—2017年卻與西安市相反,即物流客運要素集聚能力基本持續上升。渭南市在2009—2016年與西安市趨勢基本一致,但是2017年物流客運要素集聚能力開始上升。寶雞市在2009—2014年物流客運要素集聚能力持續下降;2015—2017年又開始緩慢上升。漢中、商洛、延安、榆林及安康市在2009—2013年期間物流客運要素集聚能力持續提高;2014—2017年持續下滑。商洛和銅川市的物流客運要素集聚能力基本無變化。進一步,本文對陜西省各地級市物流客運要素集聚能力變動趨勢進行灰色關聯度分析,結果見表1。由表1可知,與西安市物流客運要素集聚能力動態演進過程相關性最強的是漢中市,與西安市相關性最弱的是商洛市。而與銅川市相關性最強的是商洛市,最弱的是寶雞市。與寶雞市相關性最強的是渭南市,最弱的是安康市。與咸陽市相關性最強的是榆林市,最弱的是商洛市。與渭南市相關性最強的是延安市,最弱的是咸陽市。與延安市相關性最強的是榆林市,最弱的為商洛市。與漢中市相關性最強的是西安市,最弱的是商洛市。與榆林市相關性最強的是西安市,最弱的是商洛市。與安康市相關性最強的是西安市,最弱的是商洛市。與商洛市相關性最強的是銅川市,最弱的是榆林市。
2.陜西省城市物流貨運要素集聚能力及其演進趨勢
本文將物流貨運要素集聚能力分為累計綜合能力和平均綜合能力,其中累計綜合能力由2009—2017年客運量的累計值替代;平均綜合能力采用2009—2017年平均值替代。計算結果如下:西安市物流貨運要素集聚累計綜合能力排名第一,榆林第二,渭南第三,寶雞第四,咸陽第五,銅川第六,延安第七,漢中第八,安康第九,商洛第十。分三大區域觀察:陜西省關中地區物流貨運要素集聚累計綜合能力高于陜北地區,陜北地區高于陜南地區。陜西省城市物流貨運要素集聚平均綜合能力也表現出相同的排名。
從物流貨運要素集聚能力的動態演進過程觀察:在2009—2013年期間,西安市物流貨運要素集聚能力持續提高;2014—2015年持續下滑;2016—2017年又具有緩慢上升趨勢。咸陽、渭南、寶雞、商洛、榆林在2009—2017年期間物流貨運要素集聚能力持續提高;漢中市在2009—2014年期間,物流貨運要素集聚能力持續提高;2015—2017年期間,持續下滑。延安和安康兩市在2009—2013年期間,物流貨運要素集聚能力持續提高;2014—2017年期間,持續下滑。進一步,本文對陜西省各地級市物流客運要素集聚能力變動趨勢進行灰色關聯度分析。由表2可知,與西安市物流貨運要素集聚能力動態演進過程相關性最強的是安康市,與西安市相關性最弱的是寶雞市,并且與寶雞市貨運要素集聚能力動態演進呈弱負相關。而與銅川市相關性最強的是榆林市,最弱的是漢中市,并且與銅川市呈弱負相關。與咸陽市相關性最強的是渭南市,最弱的是漢中市。與渭南市相關性最強的是寶雞市,最弱的是延安市。與延安市相關性最強的是漢中市,最弱的為咸陽市。與漢中市相關性最強的是安康市,最弱的是商洛市。與榆林市相關性最強的是西安市,最弱的是寶雞市。與安康市相關性最強的是西安市,最弱的是寶雞市,并呈現弱的負相關性。與商洛市相關性最強的是榆林市,最弱的是漢中市。

表1 陜西省城市物流客運要素集聚能力變動趨勢相關性
3.陜西省城市物流客運通達性及其演進趨勢
本文將物流客運通達性分為累計通達性和平均通達性,其中累計通達性為2009—2017年客運周轉量的累計值替代;平均通達性采用2009—2017年平均值替代。經計算結論為:西安市物流客運通達性累計值排名第一,渭南第二,榆林第三,咸陽第四,漢中第五,延安第六,安康第七,寶雞第八,銅川第九,商洛第十。分三大區域觀察:陜西省關中地區物流客運通達性累計值高于陜南地區,陜南地區高于陜北地區。陜西省城市物流客運通達性平均值也表現出相同的排名。
但是,從物流客運通達性動態演進過程觀察:在2009—2013年期間,西安市、榆林市、咸陽市、商洛市以及安康市物流客運通達性持續提高,而2014—2017年持續下滑。延安市在2009—2013年物流客運通達性持續提高,經過2014年的下滑后,2015—2017年具有緩慢提升的趨勢。漢中市和渭南市在2009—2013年期間,物流客運通達性持續提高;2014—2016年持續下滑,但是2017年又具有上升趨勢。寶雞市在2009—2014年期間,物流客運通達性持續提高,2015—2017年期間持續下降。進一步,本研究對陜西省各地級市物流客運要素集聚能力變動趨勢進行灰色關聯度分析。由表3可知,與西安市物流客運通達性動態演進過程相關性最強的是渭南市,與西安市相關性最弱的是商洛市。與銅川市相關性最強的是寶雞市,最弱的是漢中市。與咸陽市相關性最強的是西安市,最弱的為銅川市。與渭南市相關性最強的是西安市,最弱的是商洛市。與延安市相關性最強的是漢中市,最弱的為銅川市,并呈負相關性。與漢中市相關性最強的是延安市,最弱的是銅川市。與榆林市相關性最強的是安康市,最弱的是銅川市。與安康市相關性最強的是渭南市,最弱的是銅川市。與商洛市相關性最強的是榆林市,最弱的是銅川市。
4.陜西省城市物流貨運通達性及其演進趨勢
本文將物流貨運通達性分為累計通達性和平均通達性,其中累計通達性為2009—2017年貨運周轉量的累計值替代;平均通達性采用2009—2017年平均值替代。經計算結果如下:榆林市物流貨運通達性累計值排名第一,渭南第二,西安第三,咸陽第四,寶雞第五,漢中第六,銅川第七,延安第八,安康第九,商洛第十。分三大區域觀察:陜西省關中地區物流貨運通達性累計值高于陜南地區,陜南地區高于陜北地區。陜西省貨運物流通達性平均值排名與累計值一樣。
但是,從物流貨運通達性動態演進過程觀察:在2009—2017年期間,榆林、咸陽、銅川以及商洛市物流貨運通達性持續提高;西安、渭南、寶雞以及漢中市在2009—2013年期間,物流貨運通達性持續提高;2014—2015年不斷下降,2016—2017年物流貨運通達性持續提高。延安市和安康市在2009—2014年物流貨運通達性持續提高;2015—2017年持續下降。進一步,本文對陜西省各地級市物流貨運通達性變動趨勢進行灰色關聯度分析。由表4可知:與西安市物流貨運通達性動態演進過程相關性最強的是漢中市,相關性最弱的是商洛市。與銅川市相關性最強的是咸陽市,最弱的是漢中市。與寶雞市相關性最強的是渭南市,最弱的是安康市。與咸陽市相關性最強的是銅川市,最弱的漢中市。與渭南市相關性最強的是西安市,最弱的是安康市。與延安市相關性最強的是漢中市,最弱的為渭南市。與漢中市相關性最強的是西安市,最弱的是商洛市。與榆林市相關性最強的是咸陽市,最弱的是安康市,并呈現負相關。與安康市相關性最強的是延安市,最弱的是商洛市,并呈現負相關。與商洛市相關性最強的是銅川市,最弱的是安康市,并呈負相關。

表2 陜西省城市物流貨運要素集聚能力變動趨勢相關性

表3 陜西省城市物流客運通達性變動趨勢相關性

表4 陜西省城市物流貨運通達性變動趨勢相關性
(二)陜西省城市物流非均衡發展態勢測度及其特征
1.測度方法
基于現有研究對非均衡的概念界定,本文也采用差異性作為物流非均衡發展的測量依據。本研究所采用的指標為物流要素集聚能力、物流通達性非均衡兩個指標來衡量陜西省城市物流非均衡發展態勢。其中:物流要素集聚能力主要選擇貨運量和客運量指標;物流通達性主要選擇客運周轉量和貨運周轉量作為替代指標。本文所采用的非均衡測度方法,主要借鑒王婷[27]、鄭鵬等[9]的研究方法,采用δ-收斂模型。但是以上方法僅能測度非均衡發展態勢的演進過程,并不能定量化非均衡態勢變化的速度。因此,本文在采用以上方法的同時,應用β-收斂模型對陜西省城市物流非均衡發展實現的收斂速度進行分析與測量。各模型的計算方法如下所示。
(1)δ-收斂模型。本文應用δ-收斂模型對陜西城市物流非均衡發展態勢的動態演進行研究。其中,δ-收斂模型計算方法如式(1)所示:

其中:CV代表物流要素集聚性和物流通達性非均衡的收斂系數;yi代表各地區的物流要素集聚性和物流通達性;i代表陜西省各地級市;yˉ代表各地區這一指標值的平均值;n代表陜西省所轄城市數量。
(2)β-收斂模型。通過對物流要素集聚性和物流通達性非均衡的態勢演進過程研究。但對于物流要素集聚性和物流通達性非均衡的收斂速度而言,卻無法實現有效度量,從而不能定量化物流非均衡發展態勢變化的總體特征。因此,本文借助β-收斂模型進一步衡量陜西省城市物流要素集聚性和物流通達性非均衡態勢的收斂速度,明確陜西省城市物流實現協調發展的速率。設定的面板數據β-收斂模型如式(2)所示:

其中:yit和yit-1分別表示全局以及各城市變量值;it代表陜西省i城市t年物流要素集聚性和物流通達性;α代表截距項;eit代表隨機擾動項;μit代表面板數據可能存在的固定效應或隨機效應假設,服從N(0,δ2)。如果向量yit存在β-收斂,則β系數為負值,表明物流要素集聚性和物流通達性較為落后的城市增長速度要高于較為發達城市,若為正值則相反。同時,根據收斂系數β的估計值,還可計算收斂所達到的穩態值γ0和收斂速度θ,代表通過向發達城市追趕實現物流均衡發展的速度:

2.測度結果分析
(1)陜西省城市物流非均衡發展態勢分析。由表5陜西省城市物流客運要素集聚能力非均衡發展態勢測度的平均值可知,關中-陜南城市間物流客運要素集聚能力非均衡發展的程度最高,陜北城市之間的非均衡發展程度最低。從物流客運要素集聚能力非均衡發展態勢觀察:2009—2011年期間,陜西省城市間物流客運要素集聚能力非均衡態勢不斷下降;2012—2016年期間,非均衡態勢不斷提高;2017年又開始下降。而關中城市群間物流客運要素集聚能力非均衡態勢在樣本觀測期間基本持續處于下降趨勢。2009—2016年期間,陜北城市間非均衡態勢不斷提高,2017年非均衡態勢開始下降。2009—2014年期間,陜南城市間非均衡態勢不斷下降;2015—2017年期間,非均衡態勢開始提高。2009—2014年期間,關中-陜南城市之間非均衡態勢不斷下降,2015—2017年非均衡態勢不斷提高。2009—2017年期間,陜北-陜南城市之間非均衡發展態勢不斷下降。
由表6陜西省城市物流貨運要素集聚能力非均衡態勢測度的平均值可知,關中城市群間物流貨運要素集聚能力非均衡發展的程度最高,陜南城市之間的非均衡發展程度最低。從非均衡發展的態勢觀察:2009—2016年期間,陜西省城市間物流貨運要素集聚能力非均衡態勢不斷下降;2017年非均衡發展態勢開始增強。2009—2014年期間,關中城市群間物流貨運要素集聚能力非均衡發展態勢不斷下降;2015—2017年又有所提高。2009—2014年期間,陜北城市間非均衡發展態勢不斷提高;2015—2017年期間非均衡發展態勢不斷下降。2009—2013年期間,陜南城市間非均衡發展態勢不斷提高;2014—2016年期間,非均衡發展態勢減弱,而2017年又持續提高。2009—2017年期間,關中-陜北城市間非均衡發展態勢不斷降低。2009—2013年期間,關中-陜南城市間非均衡發展態勢不斷提高;2014—2017年期間,非均衡發展態勢不斷得到緩解。2009—2016年期間,陜北-陜南城市間非均衡發展態勢較為平穩,而2017年非均衡發展態勢增強幅度較高。
由表7陜西省城市物流客運通達性非均衡發展態勢測度的平均值可知,關中-陜南城市間物流客運通達性非均衡發展的程度最高,陜南城市間物流客運通達性非均衡發展程度最低。從非均衡發展的態勢觀察:2009—2017年期間,陜西省城市間物流客運通達性非均衡發展的程度不斷緩解。分區域觀察:2009—2017年期間,關中城市群間、陜南城市間、關中-陜北城市間、關中-陜南城市間物流客運通達性非均衡發展的程度不斷緩解。2009—2017年,陜北城市間非均衡發展的程度不斷增強。而2009—2017年,陜北-陜南城市間物流客運通達性非均衡發展的程度不斷增強。
由表8陜西省城市物流貨運通達性非均衡發展態勢測度的平均值可知,關中-陜南城市間物流貨運通達性非均衡發展的程度最高,陜北-陜南城市間物流貨運通達性非均衡發展的程度最低。從非均衡發展的態勢觀察:2009—2014年期間,陜西省城市之間物流貨運通達性非均衡發展態勢不斷緩解;2015—2017年,物流貨運通達性非均衡發展態勢不斷增強。2009—2017年期間,關中城市群之間物流貨運通達性非均衡發展態勢不斷緩解。2009—2017年期間,陜北城市之間非均衡態勢不斷增強。2009—2014年期間,陜南城市之間非均衡態勢不斷緩解;2015—2017年又不斷增強。2009—2014年期間,關中-陜北城市間非均衡態勢不斷緩解;2015—2017年又不斷增強。2009—2017年期間,關中-陜南城市間非均衡發展態勢不斷緩解。2009—2017年期間,陜北-陜南城市間非均衡發展態勢不斷緩解;2015—2017年又不斷增強。

表5 陜西省城市物流客運要素集聚能力非均衡態勢測度

表6 陜西省城市物流貨運要素集聚能力非均衡態勢測度

表7 陜西省城市物流客運通達性非均衡態勢測度

表8 陜西省城市物流貨運通達性非均衡態勢測度
(2)陜西省城市物流非均衡發展實現收斂的速度。基于上述對陜西省城市間物流非均衡發展態勢的動態性分析,本研究采用β-收斂模型對城市物流非均衡發展的收斂速度進行測度。回歸結果見表9~表13。由表9陜西省城市物流非均衡發展的β-收斂結果可知,從陜西省10個地級市的研究樣本的回歸結果觀察,物流客運要素集聚能力非均衡β參數為正值且顯著,表明陜西省城市間客運要素集聚能力的非均衡發展態勢不具有收斂性,而存在發散性特征。物流貨運要素集聚能力非均衡β參數為負值且顯著,表明陜西省城市物流貨運要素集聚能力非均衡發展態勢存在收斂性,且以1%的速度實現收斂。物流客運通達性非均衡β參數為負值且顯著,表明陜西省物流客運通達性非均衡發展態勢也存在收斂性,且以0.4%的速度實現收斂。物流貨運通達性非均衡的β參數為負值且顯著,表明陜西省城市物流貨運通達性非均衡發展態勢具有收斂性,且以0.65%的速度實現收斂。
從表10中的關中城市群間物流非均衡發展的β-收斂結果可知:物流客運要素集聚能力非均衡β參數為負值且顯著,表明關中城市群之間物流客運要素集聚能力非均衡發展態勢具有收斂性,且能以7.16%的速度實現收斂。物流貨運要素集聚能力非均衡β參數為負值,表明關中城市群之間物流貨運要素集聚能力非均衡發展態勢具有收斂性,且以1.27%的速度實現收斂。而物流客運通達性非均衡β參數為正值且顯著,表明關中城市群之間物流客運通達性非均衡發展不存在收斂性,且具有發散性特征。物流貨運通達性非均衡β參數為負值且顯著,表明關中城市群之間物流貨運通達性非均衡發展態勢具有收斂性,且以0.73%的速度實現收斂。
從表11中的關中-陜北城市物流非均衡發展的β-收斂結果可知:物流客運要素集聚能力非均衡β參數為負值且顯著,表明關中-陜北城市之間物流客運要素集聚能力非均衡態勢具有收斂性,且能以8.27%的速度實現收斂。物流貨運要素集聚能力非均衡β參數為負值,表明關中-陜北城市之間物流貨運要素集聚能力非均衡具有收斂性,且以0.901%的速度實現收斂。而物流客運通達性非均衡β參數不具有顯著性,表明關中-陜北城市之間物流客運通達性非均衡不存在收斂性。物流貨運通達性非均衡β參數為負值且顯著,表明關中-陜北城市之間物流貨運通達性非均衡態勢具有收斂性,且以2.8%的速度實現收斂。
從表12中的關中-陜南城市物流非均衡發展的β-收斂結果可知:物流客運要素集聚能力非均衡β參數為負值且顯著,表明關中-陜南城市之間物流客運要素集聚能力非均衡發展態勢具有收斂性,且能以6.06%的速度實現收斂。物流貨運要素集聚能力非均衡β參數為負值且顯著,表明關中-陜北南城市之間物流貨運要素集聚能力非均衡發展態勢具有收斂性,且以1.14%的速度實現收斂。而物流客運通達性非均衡β參數不具有顯著性,表明關中-陜南城市之間物流客運通達性非均衡發展不存在收斂性的特征。物流貨運通達性非均衡β參數為負值且顯著,表明關中-陜南城市之間物流貨運通達性非均衡發展態勢具有收斂性,且以0.866%的速度實現收斂。
從表13中的陜北-陜南城市物流非均衡發展的β-收斂結果可知:物流客運要素集聚能力非均衡β參數為負值且顯著,表明陜北-陜南城市之間物流客運要素集聚能力非均衡發展態勢具有收斂性,且能以2.4%的速度實現收斂。物流貨運要素集聚能力非均衡β參數為負值且顯著,表明陜北-陜南南城市之間物流貨運要素集聚能力非均衡發展態勢具有收斂性,且以1.41%的速度實現收斂。而物流客運通達性非均衡與物流貨運通達性非均衡的β參數不具有顯著性,表明關中-陜南城市之間物流客運通達性、貨運通達性非均衡發展態勢不存在收斂性特征。
從以上比較分析可知,物流客運要素集聚能力非均衡的收斂速度表現出如下特征:關中-陜北城市間>關中城市群間>關中-陜南城市間>陜北-陜南城市間。物流貨運要素集聚能力非均衡的收斂速度表現出的特征如下:關中-陜北城市間>關中城市群間>關中-陜南城市間>陜北-陜南城市間。物流貨運通達性非均衡收斂速度表現出的特征為:關中-陜南城市間>關中-陜南城市間>關中城市群間。

表9 陜西省物流非均衡發展的β-收斂結果

表10 關中城市群物流非均衡發展的β-收斂結果

表11 關中-陜北城市物流非均衡發展的β-收斂結果

表12 關中-陜南城市物流非均衡發展的β-收斂結果

表13 陜北-陜南城市物流非均衡發展的β-收斂結果
三、“絲路經濟帶”核心區:陜西省城市物流非均衡發展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效應
(一)變量選取與指標來源
(1)物流非均衡發展的測度(logisticsCV)。對于物流非均衡發展的指標選取,結合上文中對物流要素集聚能力和物流通達性非均衡的測度,主要選擇貨運量、客運量、貨運周轉量和客運周轉量作為替代指標。樣本區間為2009—2017年,數據來源于《陜西省統計年鑒》[28]。
(2)經濟增長水平的測度(GDPCV)。對經濟增長的測度,本研究主要選擇陜西省地級市2009—2017年GDP作為基礎測度數據,數據來源于2010—2018年《陜西省統計年鑒》[24]。
(二)數據分布特征與模型構建
1.數據分布特征
本文將陜西省經濟增長水平作為因變量。為進一步清晰陜西省GDP數據分布,將其繪制成核密度分布圖,如圖1所示。從圖中可以發現從2009—2017年,陜西省經濟增長數據存在非正太分布和非對稱特征。而通常使用的OLS回歸方法主要是對被解釋變量均值回歸,如果被解釋變量為非正太分布,采用OLS會損失大量信息,導致所構建的模型估計系數會存在一定偏差,對實證結果的解釋力度可能會下降。考慮到分位數回歸突出的是對于因變量的某一個區域進行重點分析,所以它可以在保留變量之間的大部分信息的同時,在一定程度上消除異方差問題[29]。因此,本文選擇構建分位數回歸模型解決該問題。
2.模型構建
本文將陜西省經濟增長水平作為因變量,主要選擇物流要素集聚能力非均衡以及物流通達性非均衡作為自變量,并采用客運量、貨運量、客運周轉量以及貨運周轉量非均衡測度值作為替代變量。考慮到客運量、客運周轉量、貨運量以及貨運周轉量之間在原始數值計算中存在關聯性,為降低多重共線性問題,本文分別對客運量、客運周轉量、貨運量以及貨運周轉量非均衡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建立分位數回歸模型,如下所示:

圖1 “絲路經濟帶”核心區域陜西省經濟增長水平數據分布圖

其中:logisticsQVi、logisticsHi、logisticsQi、logisticsHVi分別代表物流客運通達性、物流貨運要素集聚、物流客運要素集聚、物流貨運通達性非均衡;GDP代表經濟增長水平。研究中所選取的樣本為陜西省地級市樣本,樣本區間為2009—2017年。在方程回歸中為消除變量異方差及量綱的影響,對樣本進行了對數化處理。
3.回歸結果分析
在樣本回歸中,為比較OLS回歸與分位數回歸(QR)的結果差異,本文同時采用兩種方法進行了樣本回歸,回歸結果見表14和表15。從表14的OLS回歸結果可知,陜西省城市物流客運要素集聚能力非均衡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效應不顯著;物流客運通達性非均衡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效應為負值,表明物流客運通達性非均衡對陜西省經濟增長產生了抑制效應。物流貨運要素集聚能力非均衡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效應為負值,表明物流貨運要素集聚能力非均衡對陜西省經濟增長也產生了抑制效應,且抑制效應高于物流客運通達性非均衡所產生的影響。然而,物流貨運通達性非均衡的影響效應并不顯著。為進一步從動態視角觀察物流要素集聚能力非均衡和物流通達性非均衡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效應變化,本文對陜西省城市樣本進行了分位數回歸,回歸結果見表15。陜西省城市物流客運要素集聚非均衡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效應在分位點(0.25-0.5-0.75)不顯著。而物流客運通達性非均衡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效應在分位點(0.25-0.5-0.75)均顯著為負值,但是系數值逐漸變小,表明隨著陜西省經濟增長水平不斷提高,物流客運通達性非均衡對經濟增長的抑制效應處于不斷縮減狀態。而物流貨運要素集聚能力非均衡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效應在分位點(0.25-0.5-0.75)均為負值,但是僅在0.25分位點顯著,表明在陜西省經濟增長水平相對較低時,物流貨運要素集聚能力非均衡所產生的抑制效應最強。從以上分析發現,不管是OLS回歸還是分位數回歸,物流貨運要素集聚非均衡對經濟增長的抑制效應均最強。

表14 陜西省物流非均衡發展對經濟增長的外部效應分析(OLS)

表15 陜西省物流非均衡發展對經濟增長的外部效應分析(QR)
四、緩解“絲路經濟帶”核心區陜西省城市物流非均衡發展的關鍵因素識別
(一)變量選取與指標來源
從以上研究分析發現,物流貨運要素集聚非均衡發展對陜西省經濟增長的抑制效應最強,因此,提高陜西省城市物流貨運要素集聚能力,并緩解其非均衡發展是降低陜西省城市物流非均衡發展的負外部效應的關鍵因素。故而,需要進一步挖掘能夠促進陜西省城市物流貨運要素集聚能力提高的影響因素,甄別其影響效果強弱,從而辨別促進陜西省城市物流協調發展的有效路徑。本文在對文獻梳理中,結合物流業派生性特征,選取了能夠影響物流貨運要素集聚能力的關鍵性影響因素作為變量,具體指標選擇如下:
(1)國際貿易(Trade)。國際貿易發展主要分為進口貿易和出口貿易,對國際貿易發展的測度,本文主要選擇陜西省地級市2009—2017年區域進口和出口總額作為基礎測度數據,樣本觀測期間為2009—2017年,數據來源于2010—2018年《陜西省統計年鑒》[24]。
(2)物流交通基礎設施(Traffic)。對物流交通基礎設施的測度,本文主要選擇陜西省地級市2009—2017年等級公路里程作為基礎測度數據,樣本觀測期間為2009—2017年,數據來源于2010—2018年《陜西省統計年鑒》[24]。
(3)產業結構(Industry)。對產業結構的測度,本文分別選取陜西省各城市第一(農業)、第二(工業)、第三產業(服務業)的增加值作為替代變量,樣本觀測期間為2009—2017年,數據來源于2010—2018年《陜西省統計年鑒》[24]。
(二)模型構建
結合上述指標選取以及相關替代變量,本文選擇物流貨運要素集聚能力作為因變量,結合物流貨運要素集聚能力的屬性特征,分別引入國際貿易、物流交通基礎設施、產業結構等作為影響物流要素集聚綜合能力變化的因素納入到方程之中。本文構建的面板回歸模型,如下所示:

其 中 :lnlogisticsHi,t代 表 物 流 貨 運 要 素 集 聚 能 力 ;lnTradeini,t代 表 進 口 規 模 ;lnTradeinouti,t代 表 出 口 規 模 ;lnTraffici,t代 表 物 流 交 通 基 礎 設 施 ;lnIndustry1i,t代 表 農 業 發 展 規 模 ;lnIndustry2i,t代 表 工 業 發 展 規 模 ;lnIndustry3i,t代表服務業發展規模。研究中所選取的樣本為陜西省地級市樣本,樣本區間為2009—2017年。在方程回歸中為消除變量異方差及量綱的影響,對樣本進行了對數化處理。
(三)回歸結果分析
從陜西省城市樣本回歸結果(表16)可知:進口規模(lnTradein)的回歸系數為負值,表明進口規模擴大不利于陜西省物流貨運要素集聚能力水平提高,然而陜西省出口規模(lnTradeinout)的回歸系數并不顯著。主要原因:第一,由于陜西省進出口規模中主要以化學工業及其相關工業的產品、賤金屬及其制品進出口為主,而這些商品主要運輸工具為鐵路運輸,由于本省鐵路運輸樞紐主要集中于關中地區,因此進出口規模擴大并不利于陜西省總體物流貨運要素集聚能力水平的協調發展,從而表現出進口規模擴大抑制了物流貨運要素集聚水平的發展。第二,由于陜西省的國際貿易結構中進口比重較大,而出口比重較小引起。進口運輸主要是從外埠將貨物運輸到陜西省境內,出口貿易則是將本省貨物運輸到外埠,若進口規模較大,實質上對本地運輸工具的使用率比較低,而一個地區對貨運量的統計主要考核的方式是本地運輸工具的運輸規模或者運輸到目的地的規模。因此,陜西省進口規模擴大表現出抑制了物流貨運要素集聚水平的提升。對陜西省而言,要加快建設圍繞陜北、陜南的中心城市,建設輻射北方和南方的進口出口貿易的鐵路樞紐中心,將陜北和陜南建設成陜西省南出和北出的重要國際貿易鐵路樞紐中心,且仍然要將走出去作為重點任務推進,并加大出口貿易規模。物流交通基礎設施(lnTraffic)的回歸系數為負值且顯著,表明陜西省物流交通基礎設施發展對物流貨運要素集聚能力水平提高產生了抑制效應,主要原因在于陜西省物流交通基礎設施中的等級公路比重過小,如圖2所示,三級公路和高速收費公路占比最高。而三級公路所能承擔的貨運車輛流通量遠遠低于一級或二級公路;高速收費主要按照貨運的重量(噸位)收費,公路運輸成本較高,以上惡化了陜西省物流貨運要素集聚能力水平的提高,表現出物流交通基礎設施發展對物流貨運要素集聚能力水平提升的抑制效應。因此,應進一步提高一級或二級公路建設規模,逐步降低高速路收費費率,才能有效促進陜西省城市物流貨運要素集聚水平提升。從產業結構觀察:農業發展規模(lnIndustry1)對陜西省城市物流貨運要素集聚能力水平的影響效應不顯著;而工業發展規模(lnIndustry2)的影響為正值且顯著,表明工業發展規模擴大有利于陜西省城市物流貨運要素集聚能力水平的提高。服務業發展規模(lnIndustry3)的影響為負值且顯著,表明服務業發展規模擴大抑制了物流貨運要素集聚能力水平提高,主要原因在于陜西省第三產業的產業鏈條相對短,且主要面對消費市場,投資的強度不如工業,對大規模貨運需求較弱,并且可能主要依賴于陜西省區域外的運輸工具完成運輸任務,而對陜西省的運輸工具依賴性較弱。因此,在加快服務業發展過程中,要更注重服務業業態培養,深化產業鏈建設,圍繞服務業核心產業拓展產業鏈,提高省內運輸活力,促進貨運需求水平。

表16 陜西省物流業協調發展的路徑選擇
分區域觀察:從關中城市群的樣本回歸結果可知,進口規模(lnTradein)的回歸系數也為負值,而出口規模(lnTradeinout)的回歸系數不顯著。表明進口規模擴大不利于關中城市群物流貨運要素集聚能力水平提高。主要原因與上述原因相同。物流交通基礎設施(lnTraffic)的回歸系數為正值,但是不具有顯著性。主要原因可能在于關中地區公路里程占全省接近40%,等級公路占全省35.7%,比例均較大引致。同樣,對關中城市群而言,工業發展規模(lnIndustry2)的影響為正值且顯著,表明工業發展規模擴大有利于關中城市群物流貨運要素集聚能力水平的提高,而其他因素均不顯著。從關中-陜北城市群樣本回歸觀察:進口規模(lnTradein)和出口規模(lnTradeinout)的回歸系數均為負值,表明進口規模擴大均不利于關中-陜北城市群物流貨運要素集聚能力水平提高。進口規模對物流貨運要素集聚能力提升的抑制性原因與上述相同,但是出口規模擴大對物流貨運要素集聚能力的不利影響主要原因在于陜北地區缺乏對外貿易機構,并且沒有相對獨立的運輸系統造成,而陜北地區的出口貿易主要依靠西安的對外貿易機構或運輸系統進行出口貿易活動。物流交通基礎設施(lnTraffic)的回歸系數不顯著。工業發展規模(lnIndustry2)的影響為正值且顯著,表明工業發展規模擴大有利于關中-陜北城市群物流貨運要素集聚能力水平的提高。從關中-陜南城市群樣本回歸觀察:進口規模(lnTradein)的回歸系數也為負值,表明進口規模擴大不利于關中-陜南城市群物流貨運要素集聚能力水平提高。而出口規模(lnTradeinout)的影響效應不顯著。物流交通基礎設施(lnTraffic)的回歸系數為負值且顯著,表明關中-陜南物流交通基礎設施發展對物流貨運要素集聚能力水平提高產生了抑制效應,主要原因也在于關中-陜南城市群之間物流交通基礎設施中的等級公路比重過小所致。而工業發展規模(lnIndustry2)的影響為正值且顯著,表明工業發展規模擴大有利于關中-陜南城市群物流貨運要素集聚能力水平的提高。

圖2 陜西省等級公路占比
五、研究結論
本文通過應用δ-收斂模型和β-收斂模型對“絲綢之路經濟帶”核心區,即陜西省城市物流非均衡發展態勢進行了測度;通過構建分位數回歸,探索了陜西省城市物流非均衡發展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效應。結合影響效應,對緩解陜西省城市物流非均衡發展的關鍵因素進行了識別;并對影響關鍵因素變化的路徑進行了分析。主要結論如下:
第一,從陜西省物流非均衡發展態勢觀察,物流客運要素集聚能力非均衡的收斂速度表現出如下特征:關中-陜北城市之間的收斂速度>關中城市群之間的收斂速度>關中-陜南城市之間的收斂速度>陜北-陜南城市之間的收斂速度。物流貨運要素集聚能力非均衡的收斂速度表現出的特征如下:關中-陜北城市之間的收斂速度>關中城市群之間的收斂速度>關中-陜南城市之間的收斂速度>陜北-陜南城市之間的收斂速度。物流貨運通達性非均衡收斂速度表現出的特征為:關中-陜南城市之間的收斂速度>關中-陜南城市之間的收斂速度>關中城市群之間的收斂速度。
第二,從陜西省城市物流非均衡發展對經濟增長的外部效應及緩解非均衡發展的關鍵因素研究發現:陜西省物流客運要素集聚非均衡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效應不顯著;物流客運通達性和物流貨運要素集聚性非均衡對陜西省經濟增長產生了抑制效應,且抑制效應高于物流客運通達性非均衡所產生的影響。而物流貨運通達性非均衡的影響效應并不顯著。從動態視角觀察物流要素集聚非均衡和物流通達性非均衡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效應變化發現:陜西省物流客運要素集聚非均衡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效應在分位點(0.25-0.5-0.75)不顯著。而物流客運通達性非均衡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效應在分位點(0.25-0.5-0.75)均顯著為負值,但是系數值逐漸變小,表明隨著陜西省經濟增長水平不斷提高,物流客運通達性非均衡對經濟增長的抑制效應處于不斷縮減狀態。物流貨運要素集聚非均衡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效應在分位點(0.25-0.5-0.75)均為負值,但是僅在0.25分位點顯著,表明在陜西省經濟增長水平相對較低時,物流貨運要素集聚非均衡所產生的抑制效應最強。從以上分析發現,不管是OLS回歸還是分位數回歸,物流貨運要素集聚非均衡對經濟增長的抑制效應均最大。
第三,促進物流貨運要素集聚能力提高,是緩解陜西省城市物流非均衡發展的關鍵因素。而從影響物流貨運要素集聚水平提高的影響因素觀察:進口規模擴大不利于陜西省物流貨運要素集聚能力水平提高,然而陜西省出口規模的回歸系數并不顯著。主要原因:(1)由于陜西省進出口規模中主要以化學工業及其相關工業的產品、賤金屬及其制品進出口為主,而這些商品主要運輸工具為鐵路運輸,由于我省鐵路運輸樞紐主要集中于關中地區,因此進出口規模擴大并不利于陜西省總體物流貨運要素集聚能力水平的協調發展,從而表現出進口規模擴大抑制了物流貨運要素集聚水平的發展。(2)由于陜西省的國際貿易結構中進口比重較大,而出口比重較小引起。而進口運輸主要是從外埠將貨物運輸到陜西省內,出口貿易則是將本省貨物運輸到外埠,若進口規模較大,實質上對本地運輸工具的使用率比較低,而一個地區對貨運量的統計主要考核的方式是本地運輸工具的運輸規模或者運輸到目的地的規模。因此,陜西省進口規模擴大表現出抑制了物流貨運要素集聚水平的提升。對陜西省而言,要加快建設圍繞陜北、陜南的中心城市,建設輻射北方和南方的進口出口貿易的鐵路樞紐中心,將陜北和陜南建設成陜西省南出和北出的重要國際貿易鐵路樞紐中心,且仍然要將走出去作為重點任務推進,并加大出口貿易規模。陜西省物流交通基礎設施發展對物流貨運要素集聚能力水平提高產生了抑制效應,主要原因在于陜西省物流交通基礎設施中的等級公路比重過小,三級公路和高速收費公路占比過高。而三級公路所能承擔的貨運車輛流通量遠遠低于一級或二級公路;高速收費公路成本較高,主要按照貨運的重量(噸位)收費,以上惡化了陜西省物流貨運要素集聚能力水平的提高,表現出物流交通基礎設施發展對物流貨運要素集聚能力水平提升的抑制效應。因此,應進一步提高一級或二級公路建設規模,逐步降低高速路收費費率,能有效促進陜西省城市物流貨運要素集聚水平提升。從產業結構觀察:農業發展規模對陜西省城市物流貨運要素集聚能力水平的影響效應不顯著;而工業發展規模擴大有利于陜西省城市物流貨運要素集聚能力水平的提高。服務業發展規模擴大抑制了物流貨運要素集聚能力水平提高,主要原因在于陜西省第三產業的產業鏈條相對短,主要面對消費市場,投資的強度不如工業,對大規模貨運需求較弱,并且可能主要依賴于陜西省區域外的運輸工具完成運輸任務,對陜西省的運輸工具依賴性較弱。因此,在加快服務業發展過程中,要更注重服務業業態培養,深化產業鏈建設,圍繞服務業核心產業拓展產業鏈,提高省內運輸活力,促進貨運需求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