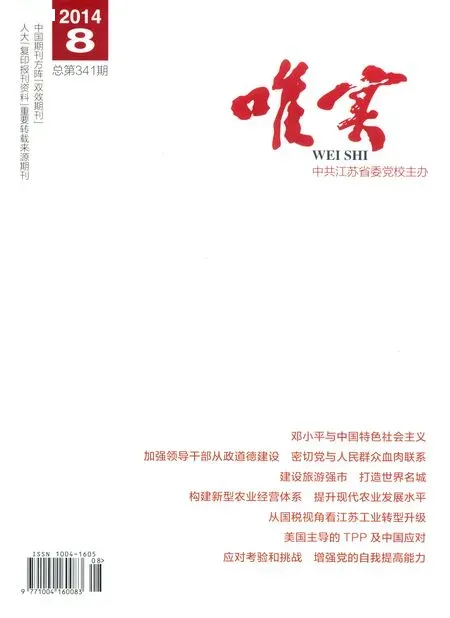中東歐國家的彈性外交
付爭

中東歐國家位處歐亞大陸的“心臟地帶”,是中國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的樞紐和支點地區。無論是在貿易還是融資方面,中東歐國家都對中國有著較強的市場需求,也是中國與歐洲展開合作的重要試水區。自歐債危機以來,歐盟對中東歐國家支持乏力,而中東歐國家恰恰對外部市場和國際貿易具有很強的依賴性。近幾年來國際貿易保護主義與單邊主義抬頭,中東歐國家也在積極尋求更廣闊的新市場與投資來源地。“一帶一路”建設的基礎和核心是互聯互通,即打通原本處于全球化進程之外的斷層與邊緣地帶,并將其納入新的一體化進程。中東歐國家參與“一帶一路”建設為國內的轉型發展以及自身地緣關系的重構提供了新契機,也因此可以借力實現國家的加速發展,提高國家和地區在全球范圍內的相對實力,并引致地緣格局與結構發生相應改變。目前,中東歐16國①已整體加入“一帶一路”的互通互聯建設,并在基礎設施建設、貿易運輸、資金融通、互通互聯以及人文交流方面取得了豐碩的合作成果。當然,我們也注意到,中東歐16國彼此在歷史文化、宗教信仰、政治環境和社會經濟方面存在諸多差異,這些差異必然會導致中東歐國家在加入“一帶一路”建設后的利益訴求呈現多樣化特點,也為中國在相關合作中協調各國甚至各區域聯盟的利益訴求帶來挑戰。與此同時,中東歐國家既是俄羅斯的西部鄰國,也是歐盟成員國或準成員國,中國與中東歐國家深化合作會不可避免觸碰到地緣鄰國在政治與經濟利益上的敏感神經,疏導與緩解此類壓力的有效途徑之一便是彈性外交。
當前,世界格局正發生深刻變化,中美俄歐外交大博弈局面已然形成——俄羅斯與美國緩和關系但也與中國保持友好;中美貿易摩擦波瀾起伏、走向不明;美歐矛盾向外交和防務等關鍵領域拓展。值此之際,中國與中東歐國家進一步深化合作,可能會招致歐盟、美國和俄羅斯的誤解、不滿。改革開放40多年以來,中國外交的成功經驗便是準確把握全球政治、經濟和安全領域發展變化趨勢,根據中國的實力地位和階段性目標,確立外交的戰略方針和推進路線。[1]因此,在“中心—外圍”結構的世界體系進入由解構到建構的歷史過渡時期,中國在與大國博弈交鋒地帶——中東歐國家的合作中,如何發揮自己的比較優勢,如何審時度勢因地制宜地尋找合作機遇和可能性,在此過程中又如何避免與歐、美、俄的既定利益格局產生正面碰撞,這些是中東歐參與“一帶一路”后中國外交已然面臨且亟待解決的重大問題。
一、務實合作制度下的多元外交
無論是“16+1”合作機制,還是中東歐16國作為整體加入的“一帶一路”倡議,可以說中國與中東歐國家的合作在務實制度主義框架下不斷擴大與深化,并在政策溝通、經貿合作和人文交流方面取得了豐碩的合作成果。然而,隨著合作的深化與合作制度效率的不斷提升,其間的矛盾與問題也日益顯現。
首先是中東歐國家對中國履行倡議的能力以及是否能形成令人滿意的合作實效缺乏信心。其次,歐盟擔心中國通過與中東歐國家合作,進而在歐盟內部擴大影響力,創建更多的區域次級機制,從而破壞歐盟形成一致的對外政策,包括一致的對華政策。另外,俄羅斯擔心中國會在其“后院”擴張影響力,搶占其貿易機會和政治力量。[2]當前中國與中東歐的合作,不以強規則、制度化和身份認同為目標,而是一個由各種雙邊、小多邊和多邊合作協議與合作安排構成的靈活開放的制度網絡。[3]上述已顯露的矛盾與問題,需要中國在這樣制度網絡合作框架下,進一步采取更具彈性的外交策略。
首先,合作框架雖然處于靈活開放的制度網絡中,但中國的大國外交依然繼承著新中國的外交優良傳統,即連續性,以及支持連續性符合現實和長遠需要的“合理性”。[1]對中國與東南亞地區的投資與經貿合作,前有中國與東盟建立的“東盟10+3”合作機制,后有“海上絲綢之路”建設倡議。因此,中國對東南亞的投資,無論是規模還是領域,必然因為合作歷史久、信任度高而暫時領先于中東歐和其他地區。而正是有東南亞與中國合作成果在前,中東歐地區更應該對中國與中東歐地區的投資承諾充滿信心,況且,中東歐地區的投資環境較東南亞地區也各具優勢。①其次,從經濟層面,中國沒有不兌現投資承諾的理由。作為同處于“中心—外圍”結構中的“邊緣—半邊緣”國家,合作實效的不平等問題也不應成為中東歐國家的顧慮。而參與“一帶一路”建設會導致“債權危機”更是無稽之談。[4]無論是早期與中國投資經貿往來密切的東南亞,還是近幾年被中國投放了大量基礎設施援助資金的非洲,都還未曾爆發債務危機。這些暴露出來的問題和誤解,其實不難化解,因此這也凸顯當前合作框架下政策溝通平臺的乏力,必要時中國和中東歐國家可以商討建立完備的組織架構為利益共同體合作機制建設提供支撐,增強對彼此的了解與信任。
相對于中東歐國家,來自歐美和俄羅斯的尖銳質疑,甚至可能會加大中國與歐盟和俄羅斯之間的嫌隙,這一考驗中國大國外交智慧的問題則更為棘手。中國與中東歐國家的合作共贏是直接可見或是可期的,但作為新興市場大國,在國際格局轉型之際,中國介入傳統大國利益格局已定、地緣政治色彩濃厚的中東歐地區,從而招致來自三方的警惕與不滿,也在情理之中。根據十九大報告精神,中國特色大國外交要“立足于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的基本國情”。無論從中國現階段的經濟發達程度,還是國際政治分屬,中國都屬于發展中國家,最多也就是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的崛起,是在美國霸權主導的“系統內的地位提升”,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擠壓了中國在東亞和平發展的戰略空間,中國不得已才借助“一帶一路”倡議向東北、東南、西面尋找出路。[5]中國既無心無力插足中東歐地區的地緣政治博弈與地區資源競爭,更無意于擴大在歐盟內部的影響力。歐盟內部凝聚力的下降根源于歐盟內部體制設計問題,而非外力所能決定。中國在與中東歐合作期間,格外重視與歐盟和俄羅斯的外交關系,對大國關系與地緣政治形勢變化審時度勢、趨利避害,避免與既定利益格局產生正面沖突,以經促政,必要時也可以利用規則制定和議程設置,化解布魯塞爾方面對中國的誤解,鞏固中國及其與俄羅斯的戰略伙伴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