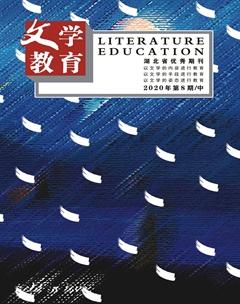海派文學中夫妻倫理關系之考察
柏玉美
內容摘要:隨著現代都市夫妻小家庭的出現,海派作家對夫妻倫理關系的書寫形成了新范型。相對于早期海派作家,施蟄存與張愛玲開始將敘事著眼點置于更日常化的家庭情境中。在以“飲食男女”為主題的日常生活中,他們探索關于夫妻倫理危機的書寫,并以更加現代的性別平等意識投入寫作中,發現現代家庭婚姻背后“夫尊妻卑”的實質,并關注已婚婦女“浮世悲哀”的命運。
關鍵詞:施蟄存 《善女子行品》 張愛玲 《傳奇》 夫妻倫理
在30年代的上海,處于家庭核心位置的夫妻倫理,在現代都市文明的吹拂中逐漸嬗變。畸形的現代都市婚戀模式炫異爭奇,家庭主婦的潛在欲望開始被作家發掘,夫妻間的日常生活圖景也走向了歷史前臺,并在海派作家筆下形成了新范型。
相對于早期海派作家追逐“新興”、“尖端”的夫妻關系書寫(比如劉吶鷗在《禮儀和衛生》中對“換妻”的書寫),施蟄存與張愛玲兩位海派作家開始將海派文學敘事著眼點置于更日常化的家庭情境中。這一書寫重心的挪移,是40年代以“婚姻生活”為基本主題的新市民小說成為海派文學主流的前兆。
一.飲食男女:都市婚姻的本質
按照雷蒙德·威廉斯的研究,英語中的family一詞語義局限在單戶的小型親屬團體與現在所謂的“中產階級家庭”(the bourgeois family)的興起有關,直到19世紀中葉以后才成為主流,以詹姆斯·穆勒的定義就是:“由父親、母親及小孩組成的團體稱為一家(a family)。”[1]
這種都市小家庭模式就是20世紀中國家庭現代化的模式。在新出現的現代家庭中,夫妻關系讓位于父子關系,成為家庭軸心與基礎。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身處劇烈變動中的現代性都市,婚戀機遇稍縱即逝,而即使男女雙方締結良緣,用情不專的沖動也時時沖撞著現代婚姻的理性根基。這些都使得滬上家庭里的夫妻倫理具有不確定性。一方面,在所謂“自由戀愛”的背后,夫妻又常常并非自愿結合,實際上既有傳統宗法倫理觀的魅影推動,又有著金錢至上主義的功利心態作祟。另一方面,都市生活的流動性特征讓婚姻中的任何一方都可能脫離正常的道德準則去謀求非正當的感情和性的利益。各種婚姻危機屢屢現于三四十年代海派作家的筆端。
非常態的夫妻關系,包含在海派作家饒有興致的“飲食男女”這一總主題之中。“飲食男女”一詞源于《禮記》,儒家認為賴以生存的飲食和男女之間的性,是人最大的追求和欲望,是“心之大端”,即人的本性。海派作家普遍置身于理想主義的寫作潮流之外,將“飲食男女”援引為主張書寫凡俗化人生的旗幟,從而常常書寫都市婚姻中男女雙方被壓抑的種種世俗欲望,以及伴隨這種欲望產生的各種觸探正常夫妻倫理邊緣的欲望訴求和行動。
如施蟄存曾說:
蒲松齡筆下之鬼,若當時直接痛快地一概說明是人,他的小說就是“鴛鴦蝴蝶派”,因為有飲食男女而無革命也。[2]
施蟄存對“有革命意識而無飲食男女之欲”展開批評,認為所謂的左派精英思維里“到底還是為了飲食男女”,這顯然說明施蟄存認為人的本質都是“為了飲食男女”的“下等人”、俗人。
張愛玲也發表過見解:
去掉了一切的浮文,剩下的彷佛只是飲食男女這兩項。[3]
在《燼余錄》中,張愛玲有感于日軍入侵香港的戰爭體驗,哀矜于人類終究離不開物欲和情欲這最基本的需求。這種感受,在《傾城之戀》中以女主人公的視角發現:“在這動蕩的世界里,錢財、地產、天長地久的一切,全都不可靠了。靠得住的只有她腔子里的這口氣,還有睡在她身邊的這個人。”[4]她發現在戰爭年代,個人主義者會被淹沒于亂流中,但平凡夫妻卻總會尋得歸宿。這種生命的極端體驗可以看出,相較于其他的物質追求,張愛玲更看重的還是夫妻間死生契闊的情感維系。
通過梳理可以發現海派作家針對人性有一種普遍的認識,他們往往為物欲、性欲這些一向被正統主流文學排斥鄙薄為所謂的“低級趣味”進行辯護,并對文學書寫追求的本質進行修正,由此也易發現夫妻倫理的脆弱性,并因此而出現諸多對于夫妻倫理危機的書寫。
在公開自由的男女交往方式下,“第三者”的出現愈加普遍,但是相對于五四時期,其理想主義、啟蒙乃至革命色彩逐漸褪色,也很少涉及對傳統觀念與制度的顛覆。在海派作家筆下,婚外戀則從側面展現了現代家庭中夫妻關系的不穩定性,“不經久的家庭”給人們以一種“惘惘的威脅”。人們對自由結合的家庭往往又視之為圍城和樊籠,從而紛紛展開跨越正常婚姻倫理軌道的“冒險”。家庭不再“經久”,而時常處于瀕臨解體、半解體、精神解體的命運中。
在張愛玲的《留情》里,與米晶堯“同居”的敦鳳,風情萬種,溫柔漂亮。但她對米先生是無情的,她留念死去的前夫,米先生反而為臨危的糟糠之妻“眼睛鼻子里有涕淚的酸楚”,[5]這一段二婚,也如火盆里的紅碳,很快就會成為灰燼。在這里,張愛玲將婚姻的利己性刻畫無疑,婚姻成為了錢色交易的外在空殼,敦鳳心理壓抑過度導致失衡,也讓自己滑向曹七巧一般的命運深淵之中。
女方的越軌行為,往往又和男方對二人情感生活的漠視,以及男方性格的缺陷有關。在施蟄存的《蝴蝶夫人》中,被疏忽的妻子則因為丈夫的無意冷落而用消耗金錢的方式來發泄郁憤,這一過行為并不是簡單用拜金主義可以囊括,而是過度補償心理在其中發生作用,情感的空虛使得她通過消費的方式來作為自己的精神依托。李約瑟向夫人敘述的莊周蝶的故事,實際是其自身愛情命運的隱喻,“永遠地追蹤著他底美麗底妻底身后”的那只隱喻為圣潔之戀的蝴蝶,卻成為夫妻情感淡薄、女方移情別戀的催化劑。
即使家庭最終并未解體,但也會陷入死水般的境地。在施蟄存的《港內小景》中,作為城市中產階級的丈夫以一種曖昧的“平衡游戲”的方式處理情感問題。一方面他在情人身上追逐愛情,而另一方面面對病妻,他的悉心照料也絕非偽善。讀者也很難對丈夫進行傳統的“負心漢”道德評判,丈夫與情人和妻子的關系,仿佛也并行不悖。故事的結局丈夫看似又回歸到病妻身邊,但這也只是“例行公事”,與情人的交際受挫意味著如果有新的可能,夫妻間脆弱的情感維系也將不再。在這里,現代夫妻倫理的復雜性進一步體現出來。
二.虛偽的“平等”:“夫尊妻卑”的實質
女結婚員們的愛情悲劇早已被白流蘇注下讖語:婚姻就是長期的賣淫。這句話很容易讓人聯想到周作人的經典論斷:“傳統的婚姻即是長期賣淫,這句話即使有人盛氣反對,事實終是如此。”[6]對婚姻的重新審視,激發了中國社會對兩性道德、婚姻形式的巨大轉變,并產生了以追求自由戀愛、自由婚姻為核心的新型兩性倫理。
但是,以三從四德為代表的封建倫理綱常依然禁錮著華夏土地上的大多數女性,女性大部分只能在依附于大家庭生存,屈從于以父、兄、夫為代表的男性家長的威權之下,表演為家庭的他者角色。這使得中國的男女不僅在道德處境和社會地位上十分懸殊,而且在心理定勢與行為習慣上也具有很大的差異。
因此,很多海派小說中凝視女郎的男性主體,往往是一種“浮蕩少年”的形象。這種現象對女性的態度,以《傾城之戀》中范柳原最典型:“把女人看成他腳底下的泥。”[7]30年代的海派文人雖然看似摩登洋派,但是他們在思想上卻是根深蒂固地支持“舊”的男權制意識形態,對女性身體的獵奇和對女性身份的嫌惡癥一道成為早期海派寫作的景觀。他們將女性置放在“被看”的位置上,展現女性的身體與欲望,滿足男性讀者的窺視欲和權力欲。在這些作家筆下,女性被物化,成為“螳螂”(劉吶鷗《流》)、“無機的人體塑像”(穆時英《白金的女體塑像》)、“一九三三型的新車”(葉靈風《流行性感冒》)。而從施蟄存開始,作家們開始注意都市夫妻倫理中“夫尊妻卑”的不平等實質,并以更加先進的性別平等意識投入寫作中。
在父權制文化體系中,性禁忌是最為牢固、結實的營地,這也是父權用來挾制女性的障翳之法,導致女性對自我身體產生恥感和罪感,兩性性關系被女性視為一種褻瀆,對于性欲的排斥與憎惡,是封建文化影響下女性集體無意識里無法掙脫的夢魘。在張愛玲《沉香屑·第二爐香》中,主要人物雖然不再是在中國傳統庭院中長大,而是具有異域氣息的故事,但是其背后的父權制陰影是東西方共有的。羅杰和愫細的性愛悲劇,實則是蜜秋兒太太一手造成的。蜜秋兒太太替代了封建專制體系中的父親角色,雖然保證了自己的尊嚴毫無受損,卻以犧牲自己的女兒和他人的幸福為代價。這里的異域者名號,實際上完全可以換置為中國人的名字。張愛玲借西方人的稱謂,實際卻書寫了具有典型意味的東方故事。
魯迅曾說過:“人必須生活著,愛才有所附麗。”[8]婚姻中女性居于弱者位置歸根結底是經濟問題。恩格斯發現“婚姻都是由當事人的階級地位來決定的,因此總是權衡利害的婚姻。”[9]由此,恩格斯一語道破資產階層所謂“婚姻自由”的虛偽性:“現代的個體家庭建立在公開的或隱蔽的婦女的家務奴隸制之上。”[10]它的本質實則反映了私有制背景下在家庭兩性關系中統治階級的倫理。在《第一爐香》里梁太太把男人視為謀財或謀色的工具,她先是罔顧其兄葛豫琨的強烈反對,在成為粵東富商的第四房姨太太后坐等遺產,迨一獲得便“關起門來做小型慈禧太后”[11],交結“無數的情人”。這種例外實際是作為普通家庭女性的對立面來書寫的。在三四十年代,中國除了極少數自食其力的職業女性,絕大部分女性都生活于家庭中。更多的,則是像《花凋》里的鄭太太,積攢下的私房錢很快便被夫家吞噬得一干二凈。
處在新倫理與舊角色之間的新女性,成為張愛玲小說關注的焦點。無論是葛薇龍、白流蘇還是姜長安,她們都已具有“新女性”的某些特征:人格獨立、戀愛婚姻自由。但是,如同阮玲玉所飾演的知識女性韋明遭遇婚姻失敗后走上自殺之途的電影《新女性》,很多新女性難以突圍出敵意重重的世俗環境,最后往往不約而同地走進了晦暗的家宅之中。在張愛玲的《花凋》中,對于鄭家的女青年來說,做“女結婚員”是她們的必由之路。而在《心經》中,許家作為新式的家庭,卻沒有擺放一張許太太的照片,可以看出許太太在家中存在感極低并且毫無話語權。能如白流蘇在戰爭環境中結成愛情良緣的,確實如同“傳奇”。
面對傳統文化模式,張愛玲對夫妻兩性角色產生了深刻的質疑和反叛。《紅玫瑰與白玫瑰》并不是俗套的出軌故事,盡管丈夫一開始遭遇了友人之妻,但他最終舍卻這位具有“嬰孩的頭腦與成熟的婦人的美”[12]的紅玫瑰,娶了白玫瑰孟煙鸝,然而婚后她就勾搭裁縫。佟振保這個有始有終、有條有理的“最合理想的中國現代人物”,卻在婚姻與愛情面前進退維谷,頹靡沉淪。
這實際上正是對男權文化下男性通過社會性別秩序的保障,實現他們滿足情欲需求的性愛理想和符合社會功能的婚姻理想的巨大反諷。吉爾伯特和格巴曾一針見血地指出:“不管她們變成了藝術對象還是圣徒,她們都回避著她們自己,這就是那些美麗的天使一樣的婦女的最主要的行為,這種獻祭注定她走向死亡和天堂。因為,無私不僅意味著高貴,還意味著死亡。”[13]女權主義批評認為,天使型的女性形象是男性審美欲望的表現形式,作為父權制的美化策略,實際上體現了男性在文化上的霸權。而在中國傳統觀念中,也有著類似于“天使”“妖婦”的女性審判,王嬌蕊和孟煙鸝,如果以傳統社會性別視角來看,則分屬“淫”與“善”的典型。她們分別承載著男權社會中男性的性愛理想與婚姻理想,并由此確立著男性的自我認同。
但是作者偏偏與這種社會陳規開了玩笑。“兩朵玫瑰”分別從“淫”向“貞”和從“貞”向“淫”互相逆轉,顛覆了男性霸權文化對既定的社會性別話語及其權利的界定,使得男性認同陷入了危機。“對于姣蕊來說,他不過是一個負心的,不敢承擔責任的懦夫;對于煙鸝來說,他也不過是一個不忠而冷酷的丈夫;對于他本人來說,恰恰是一個無力駕馭自己生活的失敗者。”[14]佟振保的失敗,是張愛玲對男性兩性權力欲望的無情嘲諷,她以冷酷的現實書寫來抗衡男性話語。
三.浮世悲歡:“賢妻良母”的海派命運
在施蟄存《鳩摩羅什》中出現的“善女人”,本是指崇尚佛法、循途守轍的清白婦人,而在《善女人行品》中的“善女人”,則是從傳統中國家庭延續到現代都市里、新舊相雜的夫人或人母形象。這些女性符合了“新賢妻良母”的身份定位。她們既有具備現代意識、接受教育的新女性特征,又有以“溫良恭儉”為核心的傳統女性特質。
1928年,陳東原在《中國婦女運動史》中認為,“賢母良妻”一詞,是清末由日本輸進的,同傳統女性觀相距甚遠。可以說,“賢妻良母”作為一個“和制漢詞”,其中的“賢”“良”,超越了強調女性自我犧牲、服從父權的儒教,而包含了為國家培養有素質國民的國家主義精神。后來新文化人向“賢妻良母主義”開刀,然而,“母性”這一女性權利卻被遮蔽,乃至于五四新文壇對當時名聲大噪的女性主義理論家愛倫凱也只是選擇性接受,忽略了她的“母權女性主義”者的身份。她承認性別差異,認為家庭和母職是女性自我實現的主要場所和方式,母性是女性的權利。[15]在1930年代,輿論界也確實出現了對“新賢妻良母主義”的倡導,國民黨發起新生活運動,新賢妻良母主義也受到官方推許,這可以說是海派女性書寫轉變的時代背景。
施蟄存作為從傳統鄉土中走入上海都會的作家,他發現了傳統家庭倫理解體后,現代夫妻小家庭也并不牢固,這不利于社會的穩定和民族國家的建構。施蟄存描繪了“一組女體習作繪”,通過揭示家庭場景中展開的“私人生活瑣事”和女性心理,展露海派小說中難得一見的“妻子”形象,這與穆時英、劉吶鷗等人對女性的觀察角度全然不同。其中的“善”字說明小說集中大部分女性主人公都是典型的新賢妻良母身份。
在施蟄存的小說《獅子座流星》中,華夏銀行國際部主任的夫人卓佩珊,整日為婚后數年未生育而焦慮。在獨自乘坐公共汽車的回家路上聽聞晚上會有“獅子座流星”,一方面聽說“獅子座流星”就是掃帚星,另一方面又從門房私語中得知看到“獅子座流星”的人會生孩子,為此而糾結萬分。晚上她甚至拉著丈夫睡到窗戶旁邊,從而“看見那顆發著幻異的光芒的星在飛下來了,……一個大聲炸響著,這怪星投在她身上了。”[16]這樣的夢境讓夫人雖有遺憾,卻又暗下決定:“今天夜里再看。”卓夫人的表現,實際也是母性本能的體現。愛倫凱指出:“母性是個人幸福與全體幸福之間的自然之衡,自衛與自愛之間的自然之衡,肉欲與心靈之間的自然之衡。”[17]施蟄存所揭示的,正是與愛倫凱強調的一樣,“愛”從來是具體而非抽象的,需要經由個人行為來實現。卓佩珊的生育焦慮可以說是賢妻良母身份意識的表露,她的生育期待,既有傳統的“傳宗接代”意識的推動,實際上也暗合了隱藏作者對女性從事母職的體諒與認同。
施蟄存通過作品,對都市家庭中的夫妻倫理形式進行反思,表達了他對既肯定傳統家庭價值又體現女性意愿與尊嚴的夫妻倫理觀的回歸。在中國倫理中,倫理政治的倫理關系和社會關系的建構原理所形成的主體的精神形態是人情主義:“所謂人情主義,就是以人倫秩序為絕對價值,主張通過主體的德性修養和心意感通的生活情理來維護社會關系和人倫和諧。”[18]《善女子行品》中,對于夫妻二人間的人情冷暖,就進行了細微的人情主義刻畫。
《莼羹》里的妻子也是一個“善女人”,常常花心思為丈夫安排新鮮的菜肴,然而因一次誤解而遭受丈夫的“傷害”。在丈夫得知自己的誤會而安撫妻子后,丈夫翻譯出“意象派”詩人理查德·奧爾丁頓的詩歌:“我的愛情也這樣漂浮向你/消失了,又重新升起。”[19]這句詩實際也是小說的主旨,丈夫醒悟到女人一心一意地將品嘗丈夫的菜味作為愛情的美好象征,在這樣的日常風景里展現了夫妻雙方精微的人性世界,日常家庭里的賢妻良母形象在施蟄存筆下美麗動人,這也是作者認同女性家庭身份的體現。
張愛玲在談及中國已婚婦女的命運時,表達了她對人生的見解:
所謂“哀樂中年”,大概那意思就是他們的歡樂里面永遠夾雜著一些辛酸,他們的悲哀也并不是完全沒有安慰的。我非常喜歡“浮世的悲哀”這幾個字,但如果是“浮世的悲歡”,那比“浮世的悲哀”其實更可悲。因為有一種蒼茫變幻的感覺。[20]
在這里,“悲歡”取代“悲哀”,實際上更能體現日常生活的無常感。對于日常生活里的“飲食男女”而言,生存成為男人和女人面前的頭等問題。即使是《鴻鸞禧》書寫婚慶這樣的大喜日子,也通過一地雞毛消彌了婚姻的神圣性。從《善女人行品》到《傳奇》,施蟄存和張愛玲逐漸放大了日常生活在人生中的重要地位,二人都在不動聲色中將價值神話逐漸消解,肯定了男女的世俗生活訴求,并在夫妻倫理書寫中具有將欲望“日常生活化”的現代意識,其不再是過去卑弱渺小的文化特征,而能夠在新舊俱陳、華洋駁雜的時代環境里躍上歷史前臺。可以想見,海派小說中的賢妻良母——善女人們,她們的命運大多也會有“浮世悲歡”的注腳。
四.結語
20世紀三四十年代,施蟄存《善女人行品》與張愛玲《傳奇》前后相繼,在歷史劇烈轉型的時期,敏銳察覺了現代都市家庭中的倫理危機、精神危機,將世俗化的家庭題材發揚光大。他們在小說中探討家庭倫理問題,援引“飲食男女”作為主張書寫日常生活的旗幟,共同參與了海派小說“日常生活”敘事的整體性建構。他們敢于正視現代都市小家庭里夫妻雙方的不對等關系,發現了自由婚姻背后“夫尊妻卑”的實質,并對夫妻倫理關系進行深刻體察與書寫。
施蟄存創造的“善女人”所代表的家庭主婦的內心狀況被得以關照,她們也更能代表現代中國亦新亦舊的夫妻倫理中受到不平等對待的生存現實。而張愛玲以更深刻的筆力展現了日常夫妻生活背后幽微的人性,以“俗人”的立場消解理想的婚姻神話形態,為飛揚的傳奇書寫增添出人生安穩的底色。
正是他們對夫妻倫理關系的深刻洞察,影響了蘇青、予且、東方蝃蝀等一批海派作家,使得后來的海派小說更加關照日常家庭,更加注意夫妻關系的刻畫,這也為中國現代小說的書寫拓展了新的領域。
參考文獻
[1][英]雷蒙·威廉斯.關鍵詞:文化與社會的詞匯[M].北京:三聯書店,2005:225.
[2]施蟄存.鬼話[A]//燈下集[M].上海:開明書店,1937:111-120.
[3]張愛玲.燼余錄[A]//流言[M].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6:45.
[4]張愛玲.傾城之戀[A]//張愛玲集[M].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6:219.
[5]張愛玲.傾城之戀[A]//張愛玲集[M].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6:5.
[6]周作人.宿娼之害[A]//晨報副刊[N].1922年10月21日,署名子榮.
[7]張愛玲.傾城之戀[A]//張愛玲集[M].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6:184.
[8]魯迅.彷徨[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1:104.
[9]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9.
[10]同上.
[11]張愛玲.沉香屑:第一爐香[A]//張愛玲集[M].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6:260.
[12]張愛玲.紅玫瑰與白玫瑰[A]//張愛玲集[M].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6:52.
[13][英]瑪麗·伊格爾頓.女權主義文藝理論[M].胡敏等譯.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1984:66.
[14]李今.海派小說與現代都市文化[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264.
[15]楊聯芬.浪漫的中國[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6:307.
[16]施蟄存.獅子座流星[A]//施蟄存全集(第一卷 十年創作集)[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1:229.
[17]楊聯芬.浪漫的中國[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6:335.
[18]樊浩.中國倫理的概念系統及其文化原理[J].上海: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1993年第3期,第60頁.
[19]施蟄存.莼羮[A]//施蟄存全集(第一卷 十年創作集)[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1:252.
[20]張愛玲.《太太萬歲》題記[A]//流言[M].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6:266.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