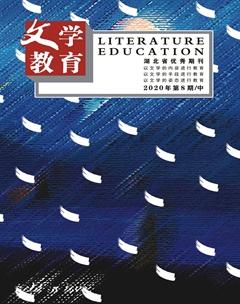《水滸傳》中潘金蓮的自我人格消解與建構
鄭琴
內容摘要:潘金蓮作為中國古典小說《水滸傳》中一位反面的女性形象,儼然成為了中國文化意蘊上“淫婦”的原型。即使到了現代社會,“潘金蓮”這一名詞仍然不斷地在文學、影視作品中煥發出新生機。本文從潘金蓮作為一名“獨立的人”的角度切入,運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從其個體人格的本我、自我、超我三個維度,對潘金蓮分別與武大郎、武松及西門慶三者的關系展開分析探究。潘金蓮的出軌行為不僅是隱藏在社會大背景下的個體的偶然悲劇,其中還蘊含著更為深層次的原因——個體人格本我的釋放、自我的協調以及超我的壓抑三個維度的建構與消解。
關鍵詞:潘金蓮 出軌行為 精神分析法 人格平衡
隨著馮小剛導演的電影《我不是潘金蓮》的播出,“潘金蓮”這一延續了幾千年的文化符號引發廣泛討論,包括對當下社會的熱點問題——婚姻內出軌行為的熱議與思考。對于“潘金蓮”這一形象的解讀,多從社會學和比較批評視角等外部視角,但從內部考察潘金蓮作為獨立個體的生存的精神分析也很有必要。時代在變化,而出軌行為依舊存在,并總能引發社會廣大關注。根據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從本我、自我、超我三個維度,從內在的人性角度對潘金蓮的出軌行為進行解讀與闡釋。
一.潘金蓮與武大郎:原欲壓抑下的超我
“清河縣里有一個大戶人家,有個使女。娘家姓潘,小名喚做金蓮,年方二十余歲,頗有些顏色。”潘金蓮原是清河縣一大戶人家的使女,只因不滿大戶糾纏遂被強制地倒貼與“身不滿五尺,面目丑陋,頭腦可笑”的三寸丁谷樹皮——武大郎。“超我”是“自我內部分化”出來的“自我理想”,具有個體獨立以其標準分辨好壞、善惡的特點。而武大郎作為婚姻的另一半,在潘金蓮看來顯然不符合理想對象的標準,反而身材短小矮粗、行為卑瑣且懦弱膽小,這也意味著她對于這缺乏自主控制而被強制的婚姻,從一開始即認為是不般配的,在這種情況下若想要使婚姻達到和諧則需要潘金蓮付出超越道德的犧牲。
而事實上這種犧牲在實際層面非常難得,在這一開始即不圓滿的情形下,武大郎自身也感受到壓力:“我近來取得一老小,清河縣人,不怯氣都來氣相欺負”。作為潘金蓮超我人格的化身,武大以丈夫的身份在社會倫理道義的高度對潘金蓮采取了監禁的策略,“自從嫁了武大,真個螻蟻也不敢入屋來”,在武松離開后,武大即每日只做一半炊餅出去賣,未晚便歸,一腳歇了擔兒便去除了簾子關上大門。這時化身潘金蓮人格“超我”的武大郎,便像一個監督者和警戒者,壓抑著潘金蓮的原欲,即本我。
“超我分為自我理想和良心,需要努力了才能達到,它是完美的而非快樂或實際的。”①從自我理想層面來說,武大郎顯然不是潘金蓮所渴求的對象,作為一名生理正常、力比多旺盛的女性,潘金蓮是追求快樂與欲望的釋放,“為頭的愛偷漢子”,欲望長此以往的被否便會引來內心一系列的厭惡與折磨,尤其在接觸親密的兩性婚姻關系中,潘金蓮的自我壓抑則會顯得更為深重,人格的磨損亦會顯得尤為嚴重。對于潘金蓮來說,欲望就像洪水被堵在了大壩急需一個理想的泄洪口。
二.潘金蓮與武松:原欲與倫理沖突中的自我
當超我被壓抑,人勢必會尋求新的寄托以達到人格協調的目的。潘金蓮不滿武大作為丈夫的形象,更不滿武大作為其超我人格所展現的監禁者的束縛姿態。力比多則轉移貫注于外界對象,開始他戀,首先的目標是家庭內的異性親長。武松與武大嫡親一母的兄弟,“武松身長八尺,一貌堂堂,渾身上下有千百斤力氣”,武大和武松的形象便形成了鮮明對比,作為女性潘金蓮的自我很自然的在比較之下產生情感轉移,“他又生的這般長大,我嫁得這等一個,也不枉了為人一世”,“不想這段姻緣,卻在這里。”。此時,潘金蓮是將“嫁”與“一世”相聯系的,是基于現實基礎、唯實原則上的理性分析綜合的結果,并不是力比多的純粹釋放。但武松與武大是嫡親一母的親兄弟,二人感情也極為親近。通過武大對于武松的一番“又恨又想”、“我的兄弟是金子言語”可以看到其視武松如子的關心、愛護及信任。而武松又是視武大如父,別有一番尊敬與保護,為避諱潘金蓮與武大告別時,武松一位錚錚鐵骨的打虎英雄居然眼中墮淚,由此亦可見二人的深厚血緣親情。
另外,《水滸傳》中的人物崇尚“忠義”,作為集體中的一份子,武松集體意識的深重更是其中代表。所以兩相綜合,武松直把潘金蓮做親嫂嫂相待,長嫂如母,別無他心。在欲入住哥嫂家時,武松向知縣請旨,知縣指出:“這是孝悌的勾當,我如何阻你。”知縣作為官府的代表自然是當時封建道德倫理規范的發言人,可見“孝悌之義”在當時社會中所處地位的分量。潘金蓮撩撥武松,武松決絕的羞辱道:“武二是個嚙齒戴發男子漢,不是那等敗壞風俗沒人倫的豬狗。嫂嫂,休要這般不識廉恥!”這番訓言有三個關鍵詞“風俗”、“人倫”、“羞恥”,官府之下的道德倫理規范可見深植于武松心間;長兄如父,兄弟情深,封建宗法倫理亦使他無法越界;最后,“嫁雞隨雞,嫁狗隨狗”的恪守婦道的觀念也使得武松斷言潘金蓮不識羞恥。
武松作為潘金蓮想要協調自我人格的轉移對象,卻注定無法滿足她想要達到解脫原欲壓抑的痛苦的目的。相反,武松在后來潘金蓮與西門慶的通奸中對二者挖心剖肝。在前面提到,武松是社會倫理道德規范的代言人,“在集體中,極端情況往往直接形成:假如對某事心存一絲疑慮,那么這種疑慮就會迅速升級為不容辯解的肯定……”武大郎死后,武松夜感武大郎托夢,“就懲罰本身來說,它也是欲望的一種滿足,只是它滿足的對象是檢查者的欲望”,②這說明在武松的潛意識中已經為潘金蓮作下判論;“在一個集體中是不需要承擔責任的。于是,一直以來約束者他的責任感就這樣被拋棄了”。③《水滸傳》中尋求的恰是一種集體意識下的忠義行為,于是才有了后來的懷疑與血腥的報復。所以當超我被壓抑的痛苦的情況下,潘金蓮尋求武松作為自我協調、情感轉移的對象這是注定無法成功的事情,因為這位對象不僅不是她的仰慕者,反而是她殘酷的復仇者與審判者。這也使得潘金蓮壓抑之后的現實挫折使得情感變得更為郁積,這樣長此以往,若無法尋得釋放口必然趨于毀滅,以消亡人格遁入精神疾病范疇來結束這無法協調的一切。
三.潘金蓮與西門慶:原欲釋放下的本我
超我的失敗與自我的受阻,使得潘金蓮的環境與身心更為壓抑,她每日只能叉開武大要求放下的簾子,尋求欲望滿足而不得的無奈等待,根據弗洛伊德的話來說就是:“盡快發泄由于內部或外部刺激所引起的興奮,本我的這一功能是實現生命最基本的原則”,其所遵循的是“快樂原則”。④等待與尋求總是有“回報”的,因掉叉竿的緣故,陽谷縣的財主西門慶看上了妖嬈的潘金蓮,經王婆牽線搭橋兩人一拍即合。
為何西門慶能與潘金蓮如此順利結合,而他和武松又有何區別呢?潘金蓮的超我受抑、自我受阻,本我的原欲沖動一再積郁堵塞,內心需要盡快釋放欲望以躲避痛苦。王婆告訴西門慶若想吸引潘金蓮需五事俱全方可,這實際上是借王婆這位經歷了作為一名根植于這個時代、了解這個社會的女性代表之口說出潘金蓮對于欲望釋放對象的基本條件:容貌、財物、時間及耐心等。相較武大,西門慶有財有貌、有社會地位,為人風流且沒有武大的對其在超我層面的壓抑;相比武松,西門慶身財等皆匹敵,只是西門慶不存在于武大之間的親情倫理關系及深厚的集體意識,西門慶和潘金蓮同樣屬于本我欲望意識強烈、急需擴張的人群,他們的特征是以個體的自我滿足為中心,以“快樂原則”為準繩。“心理器官最原始、最本質的作用就是把那些刺激著它的本能沖動結合起來,以繼發性心理過程取代占主導地位的原復發性心理過程,并使活躍的精神力量轉化為漸趨穩定的精神力量。”⑤當兩個類近的本我人格找到契機相遇的時候,這種服務于快樂原則的穩定本能沖動的未雨綢繆,它對快樂原則主導地位進行了確立。沒有道德觀念,更沒有邏輯推理,他們彼此共同的需要即是不顧一切代價滿足自己,于是干柴烈火,一點即著。
四.結論
潘金蓮的本我徹底背離道德,而逐漸消解了其自我的現實社會性、超我的自然道德性,人格結構處于失衡狀態。而這種失衡與社會平衡下的理想女性形象產生背離。所以即使社會背景不一,出軌仍會被關注、熱議的現象之一,出軌對象甚至包括處于男權社會中被條條框框牢牢束縛住的女性。從心理發展維度考察“潘金蓮”出軌行為的內在動機,以及這一文化原型的內在意蘊,進一步對現代婚姻有所啟示:婚姻中雙方的結合,應該在本我、自我、超我的人格層面,達到相對動態的平衡。在本我方面有所升華;在自我層面有所協調;而在超我方向有所追求,共同攜手構建和諧的婚姻。
參考文獻
[1]施耐庵著,金圣嘆批:《金批水滸傳》,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年,322-383。
[2]邱運華:《文學批評方法與按案例》第二版,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85頁。
[3][奧]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論》,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8年,第111頁。
[4]勒邦:《烏合之眾》,民主與建設出版社,北京,2015年,第33頁、第88頁。
[5][美]卡爾文·斯 霍爾等:《弗洛伊德心理學與西方文學》,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1986年,第23頁。
[6][奧]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自我本我與集體心理學》,戴光年譯,長春: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15年,第72頁。
[7][美]馬斯洛:《馬斯洛人本哲學》,成明譯,北京,九州出版社,2006年。
[8][奧]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性學與愛情心理學》,廖玉笛譯,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
[9][奧]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弗洛伊德心理哲學》,楊韶剛等譯,北京:九洲出版社,2003年。
[10]斯托爾,尹莉譯.弗洛伊德與精神分析[M].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7年。
[11]魯迅.中國小說史略[M].北京:人們文學出版社,1958年。
注 釋
①邱運華:《文學批評方法與按案例》第二版,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86頁。
②[奧]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論》,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8年,第111頁。
③勒邦:《烏合之眾》,民主與建設出版社,北京,2015年,第33頁、第88頁。
④[美]卡爾文·斯 霍爾等:《弗洛伊德心理學與西方文學》,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1986年,第23頁。
⑤[奧]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自我本我與集體心理學》,戴光年譯,長春: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15年,第72頁。
(作者單位:廣東省深圳市龍崗區東升學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