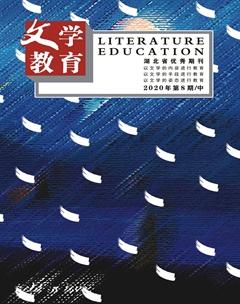文學史寫作的思想性原則和審美性原則
顧聳皓
內容摘要:王瑤的《中國新文學史稿》(以下簡稱《史稿》)和由錢理群、溫儒敏、吳福輝等人編寫的《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以下簡稱《三十年》)是最具代表性的現代文學史著作。本文通過比較《史稿》和《三十年》對趙樹理的述評,討論思想性原則和審美性原則在文學史寫作中的對立和統一。
關鍵詞:史稿 三十年 思想性原則 審美性原則
趙樹理的小說兼具思想性和審美性,《史稿》和《三十年》都給予了趙樹理很高的評價。王瑤受到新民主主義的影響,在寫作《史稿》時強調思想性原則,此舉不但忽視了沈從文、張愛玲、錢鐘書等自由主義作家的創作,而且也忽視了左翼作家身上的藝術性。經過80年代“重寫文學史”的討論,思想性原則和審美性原則從二元對立逐漸走向統一,到了90年代《三十年》對趙樹理的敘述兼具了藝術性和思想性。
一.趙樹理的評述差異
(一)作品的選擇和解讀
《史稿》把趙樹理歸入了“解放區農村面貌小說”,稱他的小說足以代表解放區小說的一般特點,并引用了周揚的評價“一位具有大眾風格的人民藝術家”。王瑤在介紹趙樹理作品時,《小二黑結婚》被一筆帶過,而給了《李有才板話》和《李家莊的變遷》大量的篇幅和高度的評價。《李有才板話》和《李家莊的變遷》的主題都是寫農民和地主的斗爭,是趙樹理根據當時的政策創作的小說,所以在主題上是符合新民主主義論的要求的,《史稿》具體介紹了兩部小說的內容,并稱“《李家莊的變遷》不但是表現解放區生活的一部成功的小說,并且也是延安文藝整風以后文藝作品多大道德高度水準之例證。”但是在《三十年》中,這對這兩部小說中農民地主斗爭的情節大寫特寫,反而把《史稿》中一筆帶過的《小二黑結婚》稱為趙樹理最具魅力的作品。
另外,《史稿》和《三十年》對趙樹理作品從不同的角度解讀,也會對作品主題有不同的闡釋。《史稿》習慣使用“改造”、“勞動”等詞匯,而在《三十年》中多使用“苦難”、“覺醒”等字眼。《史稿》中把《富貴》描述成一部寫二流子改造過程的小說,而在《三十年》中形容《福貴》是寫高利貸盤剝下農民悲慘命運的短篇。《史稿》中形容《傳家寶》是寫婦女也應該參加勞動的,而《三十年》寫稱《傳家寶》是寫農村婦女民主意識覺醒的短篇。
(二)趙樹理小說的藝術性
趙樹理小說的藝術性主要體現在他的人物塑造和對小說敘事結構和語言的探索,而這種藝術性恰恰是在《史稿》中被忽略的。《三十年》對待趙樹理小說中塑造的未覺醒的老一代農民,如二諸葛、老秦、金桂婆婆等,不再像《史稿》那樣把他們擺在階級斗爭的對立面,《三十年》評論“趙樹理筆下的這些落后的老一輩農民并不是一無是處的,作者只是寫出了他們具有的根深蒂固的舊意識、舊習慣阻礙著他們對新事物的理解。他們身上也常常表現出勞動人民的善良、樸實等優點,這正是他們轉變的根據和起點。”
《史稿》對趙樹理的小說敘事和語言只有一句話的敘述,并且與人民斗爭掛鉤,“在形式上,他運用了簡練豐富的群眾語言,創造了故事性和行動性很強的民族新形勢,適宜于反映群眾的斗爭和生活。”而《三十年》中對趙樹理開創的“評書體現代小說形式”有著很高的評價:“首先,趙樹理揚棄了傳統小說章回體的程式化的框架,而汲取了講究情節連貫性與完整性的結構特點:其次,在描寫與敘事的關系上,吸取傳統評書式小說的手法。”與《史稿》中把趙樹理的成功歸因于實踐了為工農兵服務、為人民大眾服務的文藝方向不同,《三十年》更強調了趙樹理小說藝術性與大眾性的完美的結合。
二.述評差異背后的文學史評價標準
(一)《史稿》寫作的思想性原則
王瑤的《史稿》寫作深受新民主主義論的影響,自覺地運用政治標準作為衡量文學作品優劣的標尺,過分強調文學作品的思想性,而忽視了文學作品的藝術性。王瑤在《史稿》的初版自序中介紹了《史稿》的成書因為是“工作分配”,新中國成立后,教育部把“中國新文學史”定位各大學中國語文系的主要課程之一,而國內還沒有一部正式的“中國新文學史”的教材,出于教學和政治的雙重需要,王瑤創作了《史稿》。[1]王瑤在《史稿》的自序分為開始、性質、領導思想、分期四節,在自序中深度解讀毛主席的新民主主義論,并自覺地把新文學和新民主主義論緊密聯系在一起,新文學的性質是新民主主義的,“我們的新文學是反映了中國人民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歷史要求和政治斗爭的,它的基本性質是新民主主義的。”新文學的領導思想也是馬列主義思想,“從理論上講,新文學即使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一部分,它的領導思想當然是無產階級的馬列主義思想。”因此,《史稿》在述評趙樹理時,重視趙樹理小說中反映農村中斗爭和改造的主題,以及文學為工農兵服務、人民大眾服務的文藝方向。
(二)“重寫文學史”的思想性原則和審美性原則之爭
80年代知識范型的一個本質特點,就是采用“二元對立”的方式去思考、分析問題。在“重寫文學史”專欄的發刊詞中,陳思和和王曉明開篇聲明的就是“審美原則”:“重寫文學史……它決非僅僅是單純編年式的史的材料羅列,也包含了審美層次上的對文學作品的闡發批評。”[2]后來又不斷強調“本專欄反思的對象,是長期以來支配我們文學史研究的一種流行觀點,即那種僅僅以庸俗社會學和狹隘的而非廣義的政治標準來衡量一切文學現象,并以此來代替或排斥藝術審美評論的史論觀”。[3]
“重寫文學史”最終以“審美原則”作為它的標準和方法論,并不是一個“偶然”的選擇,而是帶有某種歷史的必然性。一方面,它是“當代文學”全部歷史生成的結果,如李楊所言,沒有“十七年文學”與“文革文學”,何來80年代文學?[4]正是因為受到《講話》和《新民主主義論》影響的“解放區文學”、“十七年文學”、“文革文學”對小說語言形式及其他藝術性方面的過度排斥,才會在社會意識形態開始放松的80年代,開始對“純文學”和“審美性”的極端追捧,這是一種話語被長期禁錮后強烈反彈的表現;另一方面,它是80年代話語方式生成的產物,之前的文學史寫作都受到政治話語的訓誡,如王瑤的《史稿》就是以“新民主主義論”為指導思想的編寫,把文學創作納入政治書寫的范圍。作為現代化話語的內在要求,“審美性”原則對于現當代文學史研究的專業化起到了的積極作用,現當代文學史才在一定程度上擺脫“革命史”、“思想史”、“社會史”的模式,重塑了一個新的現當代文學。[5]
三.《三十年》-思想性和審美性的完美結合
1988年陳思和、王曉明等人主持《上海文論》“重寫文學史”專欄,該專欄從當年第四期開始,到1989年第六期結束,總計發表四十余篇關于探討20世紀中國重要文學現象和作家作品的論文,掀起“重寫文學史”的課題大討論。在這場大討論里,趙樹理也被推上了風口浪尖,如1988年戴光中的《關于“趙樹理方向”的再認識》就引起了學界的巨大反響,戴光中在文章中指出趙樹理“民間文學正統論”反映了中國整個文學界的精神萎縮,并且趙樹理在對待西方文學持保守和抗拒態度。[6]戴光中在“重寫文學史”中關于趙樹理的討論已經淡化了其小說的思想性和歷史性,轉而指出趙樹理小說藝術性的不足,這是對以往文學史重思想而輕藝術的反叛。在之后的十余年時間里,作為“重寫文學史”內涵之一的中國現代文學史研究方面,最能彰顯這一“重寫”課題業績的,是1998年7月由錢理群、溫儒敏、吳福輝合著的《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的出版。
陳思和曾提出“對于一個優秀的作家來說,他在文學上所構成的成就,不在于他寫什么,更要緊的是他怎么寫的,也就是他怎么運用他特殊的藝術感覺和語言能力來表述。”[7]《三十年》在前言里對現代文學內容與形式提出了兩方面的要求:“一方面,它要求文學的通俗性,使文化程度很低的普通人民可接受;另一方面,它又要求文學的現代性,既表現現代意識,現代思維方式、情感方式,采用與之相適應的現代藝術形式,以便于把無論是思想意識,還是思維方式、藝術欣賞能力都處于蒙昧狀態、低級階段的讀者提高到現代化水平。”[8]《三十年》對趙樹理的述評既肯定了其宣揚黨的政策方針和鼓勵農村階級斗爭等思想價值,又贊揚了其人物形象創造和現代評書體形式創造的藝術價值,突破了以往文學史討論中“審美性/歷史性”、“藝術性/思想性”、“形式語言/思想內容”二元對立的思維范式。
王瑤的《史稿》雖受政治形態影響痕跡太重,但是作為新中國后的第一部文學史,對現代文學學科的建立起了奠基性的作用。《三十年》的成功,是站在了《史稿》的肩膀上,既借鑒了《史稿》的思想性原則,又吸收了“重寫文學史”對于審美性原則的思考。
參考文獻
[1]王瑤.《中國新文學史稿》[M].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2.
[2]陳思和,王曉明.主持人的話[J].上海文論,1988年第4期.
[3]陳思和,王曉明.主持人的話[J].上海文論,1988年第5期.
[4]李楊.沒有“十七年文學”與“文革文學”,何來“新時期文學”?[J].《文學評論》,2001年第2期.
[5]楊慶祥.審美原則、敘事體式和文學史的“權力”——再談“重寫文學史”[J].文藝研究,2008年第4期.
[6]戴光中.關于“趙樹理方向”的再認識[J].上海文論,1988年第4期.
[7]陳思和.《關于“重寫文學史”》,《筆走龍蛇》,第117頁.
[8]錢理群,溫儒敏,吳福輝.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作者單位:寧波大學人文與傳媒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