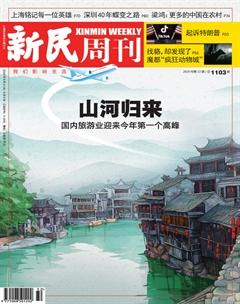追野生動物的年輕人
王仲昀

上海一批野生動物愛好者組成了一支近百人的公民科學家團隊。攝影/ 王放
夜深人靜,紅外線相機畫面中,一只體型嬌小、身手敏捷的小動物闖進了鏡頭。它顯然沒發現自己已經“入鏡”,短暫停留后,它又一蹦一跳揚長而去。它是華南兔,比一般野生兔子更小、耳朵更短,身體呈棕黃色。白天,它躲在自己的小洞里,直到夜晚才出來覓食。
這不是它第一次在此被相機捕捉。過去半年里,武亦乾和他的志愿者朋友們在上海各個公共綠地以及小區安置了近百臺紅外相機。本來,這是他們團隊針對上海貉生存狀況展開研究的一部分。沒想到,當相機回收后,他們在貉之外,還發現了很多其他野生動物。華南兔、赤腹松鼠,以及更常見的黃鼬(黃鼠狼)與東北刺猬,這些意料之外的收獲,令人感到驚喜。
今年,在復旦大學生命科學學院研究員王放等專業人士的指導下,上海一批野生動物愛好者組成了一支近百人的公民科學家團隊。像武亦乾與黃子馨這樣的“90后”與“00后”,也加入到這場對于上海野生動物的探索之旅。
去上海找貉
受疫情影響,經歷了將近三個月的閉園之后,武亦乾終于有機會和同伴一道回收安放在上海各大森林公園的紅外相機。他們等這一刻等了很久。
畫面打開一看,結果有點意外。相機原本主要用以追蹤野生貉,沒想到在所有被拍到的野生動物中,貉是出鏡率最低的物種之一。
“黃鼬,也就是人們常說的黃鼠狼,還有東北刺猬,這兩種是出現最頻繁的野生動物。和貉主要集中分布在上海閔行區、松江區不同,黃鼬與東北刺猬幾乎在上海各個機位都出現了,而且是非常頻繁的出現。世紀公園、上海植物園這樣靠近市區的公園會有,臨港這樣比較偏一點的也有。”武亦乾說道。那么,如此多的黃鼠狼和刺猬在與人類共生的過程中,是否會有意想不到的問題?
在武亦乾看來,對于黃鼠狼與東北刺猬,市民不用過多擔心。雖然數量眾多,但它們的活動軌跡完美地與人類避開:白天人們出門活動,它們在家睡覺;夜晚人類入睡,它們才外出活動。此外,這兩種野生動物相對膽小,會主動與人類保持距離。換句話說,大家彼此很難相見,即便數量多,遇到共生難題的概率也相對小。
上海市民可能更加熟悉赤腹松鼠。這種小松鼠,因其腹部呈紅色或橘紅色而得名。赤腹松鼠在整個華東地區都十分常見。市民之所以經常看見它們,一是它們會在白天活動,時常趴在電線上休息;二是這些小松鼠“沒那么怕人”。在辰山植物園踩點時,有工作人員告訴武亦乾,之前植物園曾舉辦南瓜展。沒想到那些長勢飽滿的大南瓜,成為植物園內赤腹松鼠偷吃的目標。這些小玩意兒,偷偷靠近,然后挖開南瓜,大快朵頤。
不過,不論是華南兔,還是赤腹松鼠,武亦乾過去幾年在上海都接觸不多。真正讓他不依不饒追尋的,是野生貉。
畢業于南京大學生命科學學院的武亦乾,最早和上海的野生動物結緣還要追溯到四年前。2016年,武亦乾還在讀大學,偶然間他得知上海動物園的樹林之中藏有不少野生貉。于是趁著來上海游玩之際,到動物園果真看到了野生貉。一發不可收,此后的幾年里,每當有機會來到上海,他都會找時間再去動物園尋找野生貉的蹤跡。

2016年, 武亦乾還在讀大學,偶然間他得知上海動物園的樹林之中藏有不少野生貉。于是趁著來上海游玩之際,到動物園果真看到了野生貉。攝影/ 武亦乾
這幾年除了在上海,武亦乾還去其他地方追蹤野生動物的腳步,比如在杭州參與一個與松鼠有關的項目。去年,武亦乾大學畢業。沒有急著找工作的他,進入山水自然保護中心成為一名研修生,以此度過自己的“間隔年”。
等到他第二次來時,保護小貉的不只有貉爸爸貉媽媽,還有這個小區的老老少少。
“一方面,根據前人的研究發現,在上海的野生動物中,貉具有代表性;另一方面,上海動物園里的野生貉近幾年數量不斷減少,但原因尚不清楚。這些因素綜合起來,貉就為我們的項目提供了切口。”
去年年底,由王放領銜的研究團隊與山水自然保護中心達成合作,決定共同完成一項計劃。該計劃旨在完整地調查野生動物在城市的分布、習性,和人類的關系,以及它們對于環境變化的適應性。貉是該計劃的重點追蹤對象。
在疫情開始之前,該團隊便成功啟動了監測網絡。疫情期間,人們宅在家,公園關閉,但這些相機能夠在無人值守的情況下一刻不停地記錄。近百個機位,包括了共青森林公園、濱江森林公園、上海植物園、上海動物園、閔行體育公園、虹旭社區、復旦大學校園、上海海洋大學校園、南匯城郊、浦江郊野公園、顧村公園等區域。
專跑郊區小區的大學生
去年夏天, 19歲的黃子馨正在非洲大陸上看斑馬和獅子。黃子馨目前就讀于華盛頓大學。正是這段非洲草原追尋野生動物的經歷,令她在去年下半年選擇了野生動物保護專業。
“如果說去年的經歷讓我選好了專業,那么今年在上海追尋貉,則更加堅定了自己在這條道路上走下去的念頭。”黃子馨說。公民科學家團隊于年初在上海各地安放了近百個機位,而隨著時間推移,機位也需要更新。從6月加入到志愿者項目后,黃子馨所做的工作,就是幫助團隊重新確認這些位置信息。而這些信息,都是她一個個居民小區“跑出來的”。
“從6月開始,我根據之前的信息去這些小區,跟保安或者居民打聽,確認這里有沒有人看到過貉。有的話,我就記錄人們提到的精確位置,以便讓團隊成員后續來放置紅外相機。”
一個多月里,她確認了將近140處地點,其中大部分是上海閔行、松江與青浦的居民小區。令她印象最深的是這些小區居民知悉她的來意后展現出的熱情。“最熟悉小區情況的人,肯定是每個小區的保安。一開始,我總擔心小區保安會不會兇,會不會不好說話?但接觸下來,發現絕大部分都非常愿意幫助我。有的怕我不認識路,還會領著我去。”由于大部分時間都花在了路上,黃子馨笑稱自己“在上海生活了一個多月,對路況的熟悉程度已經超過了生活近20年的北京”。
黃子馨也覺得,保護城市里的野生動物需要市民的參與。“這不應當只是專業的研究與保護團隊的事情。在城市中,環境復雜,牽扯的因素非常多。因此,確實需要廣大公民的共同參與。”
普通人影響普通人
王放如此解釋這支志愿者團隊建立的初衷:“在研究城市野生動物的過程中,組織者把復雜的自然科研工作分解為一個個具體的項目,邀請市民志愿者承擔紅外相機安裝、植被變化記錄、社區調查等。當傳統的城市野生動物研究變為公民科學家項目后,團隊不僅能夠調查城市中野生動物的生存狀況,還能從市民代表的熱烈討論中收集人們對于城市生態建設與社區管理的寶貴意見。我們相信,把可持續的城市動物調查同公眾意見整合起來,就會有更多機會了解人與野生動物共存的期待與要求,從而促進二者的友好共存,創造更加美好的城市生活。”

2020年7月,黑龍江省哈爾濱市,一只松鼠媽媽帶著兩個孩子在樹蔭中悠閑漫步、吃食。
由于自身有一些專業知識基礎,武亦乾成為這支團隊的技術指導。成立之初,他承擔起教授專業器材使用與數據搜集處理的工作。隨著時間推移,武亦乾發現:公民科學家團隊除了提供“公眾意見”,也在實踐中對上海的野生動物保護作出了貢獻。
6月底,武亦乾根據團隊搜集的信息來到松江某個小區。在這里,他見到了一窩剛剛出生的小貉。可能是在打斗中受傷,3只小貉的父母都只有一只耳朵,不過他們依舊堅守在幼崽身邊。離開之后,武亦乾心中一直牽掛著這一窩小貉。后來每次路過附近,武亦乾都會來這里看看。沒想到,等到他第二次來時,保護小貉的不只有貉爸爸貉媽媽,還有這個小區的老老少少。原來,公民科學家團隊中有一位阿姨居住于此。了解到小貉情況后,阿姨便時常來到這里,對路過的居民進行科普:“不要靠近,也不要隨意投喂。”如此一來,大家都學會了合理地保護小貉。
8月武亦乾又一次來到這里時,他想拍一些小貉長大后的最新照片。剛掏出相機,旁邊就有小朋友走上前告訴他,“不能靠近,會打擾到它們!”“我覺得太欣慰了,我們的公民科學家們,很好地發揮了他們的作用。”武亦乾對《新民周刊》說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