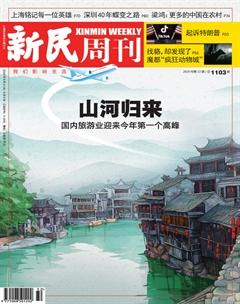中東2020:摧毀多于創建
吳健
黎巴嫩爆炸發生后,“雞湯文”潮水般充斥網絡,“我們都是黎巴嫩人”的呼聲幾乎淹沒一切,可理性的旁觀者都明白,如不深刻反思并行動起來,新的災難將為時不遠。“看到黎巴嫩的傷口,卻看不到中東的傷痛,是最大的悲劇。”沙特阿拉伯《阿拉伯新聞》駐迪拜記者弗蘭克·凱恩認為,2020年的中東,遍布黎巴嫩這樣因大災難、大動蕩或大戰爭而深陷泥潭的國家,這不是特定現象,而帶有普遍的共性,那就是經濟上“有增長無發展”、政治上“嘗試多條道路卻難覓良方”、文化上“國家認同出現危機”。這都表明,被西方大肆鼓吹并積極促成的“阿拉伯之春”之風勁吹九年后,坐擁豐富資源和龐大年輕人口的中東依舊“摧毀多于創建”。誰之過?怎么辦?數以百萬計的阿拉伯人在追問,在思考。
“食租寄生”比比皆是
嚴格來說,2020年之于中東,應算相對和平。持續多年的敘利亞、也門、利比亞和伊拉克戰爭似乎走向尾聲——成千上萬的人們已經喪生,數以百萬的人口背井離鄉,一座座城市淪為廢墟后,那里開始出現被各方勢力公認(或默認)的勝利者,敘利亞總統巴沙爾已宣布啟動國家重建,也門胡塞民兵與哈迪政府大致分清“楚河漢界”……
然而,動亂的因子并未因生靈涂炭而遠去,甚至在“阿拉伯之春”運動中幸免內戰的國家——約旦、黎巴嫩和埃及出現“第二輪發作”。由于無力徹底改革的政府解決不了飆升的年輕人失業率和其他深層次問題,數以百萬的年輕人失去經濟和政治參與資格,漸漸變成難以捉摸的“烏合之眾”。約旦分析人士阿米爾·薩拜利赫說:“我認為2020年是非常具有挑戰性的一年。”他的國家盡管為避免新冠病毒傳播頒布過禁止聚集活動的規定,可失業者與低收入人群仍堅持2018年以來的反對現行經濟政策的每周集會,這場集會已在2018年趕走一位總理,現任總理也似乎來日無多。
客觀而言,中東各國(除以色列外)經濟大體分為“石油經濟”和依附于此的“打工經濟”或“服務經濟”。眾所周知,工業革命令石油成為世界經濟“血液”,而中東油氣儲量占全球總量的60%以上,超大型油田60%以上都在中東。而1973年“贖罪日戰爭”后的“油價革命”,讓阿拉伯產油國享受了整整20年的“黃金時光”,據統計,僅1973-1980年,沙特、科威特、阿聯酋、伊拉克的外匯儲備都有30-50倍的增幅,哪怕是21世紀頭十年,這些國家(即便遭受戰爭摧殘的伊拉克)都能維持相當的景氣,特別是2011年依靠國際油價達到每桶107美元,以沙特為首的海灣產油國逐漸取代非產油國埃及,成為中東新的財富中心及地區經濟發展的“火車頭”,這也是為什么產油國是“阿拉伯之春”中受沖擊較小,大把撒錢緩和階級矛盾是重要原因。
正因為石油經濟高度依賴國際市場,注定了中東經濟整體上依附于西方主導的國際經濟秩序。
石油經濟的繁盛,更給那些非產油國造成“扭曲”,在集中于波斯灣的產油國“財富效應”誘惑下,依托語言文化相通的優勢,埃及、約旦、也門、黎巴嫩等非產油國被其表面繁華所吸引,掀起“去海灣國家打工賺錢”的熱潮,黎巴嫩更因絕佳的“自由港”地位成為中東貨物中轉與金融服務的集散地,大批資本涌入貝魯特股市債市,成為該國的“搖錢樹”。
然而,照經濟學家熊彼得的話形容,這種“有增長無發展”的經濟模式必然產生“食租寄生”效果,尤其是中東經濟“去工業化”。事實上,多數阿拉伯國家依托高油價帶來滾滾美元,使昔日貧困落后面貌一夜消失,奇跡般地跨入資金過剩、生活優裕的“后工業時代”,從阿聯酋、卡塔爾到科威特、沙特,對石油出口的依賴占到各國外匯收入的80%,不僅使其深受油價漲落影響,政府財政難以預期,更重要的是,過分依賴石油收入,抑制了其他產業發展。有人戲稱,沙特等國能出口創匯的,“除了石油,就剩下椰棗、駱駝和馬了,這些國家幾乎造不出世界市場所需的任何東西”。即使在能源工業領域,由于技術落后、資金匱乏,石油產能不足,一些國家甚至要從國外進口精煉汽油,出現“產油國進口油”的怪現象。
至于那些寄生于產油國的阿拉伯國家,隨著2011年之后國際油價進入下行區間和政治風波沖擊,更如雨中浮萍,任由拍打。最典型的莫過于埃及與黎巴嫩。其中黎巴嫩70%的人口從事服務業,還有大批勞工進入海灣國家謀生,一旦外部風云起來,就會造成國內就業壓力驟增。
要強調的是,正因為石油經濟高度依賴國際市場,注定了中東經濟整體上依附于西方主導的國際經濟秩序。產油國將大量外匯投資于美國等西方大國,使美國可以通過美元貶值和匯率調整,不斷榨取石油輸出國的財富,2011年中東劇變中,海灣國家之所以與美國結成“同盟”,其中一個關鍵原因是,海灣國家無論石油出口還是剩余資本投資,都明顯依賴美國市場。這種看似你情我愿的“利益綁定”關系,實際是海灣國家財富不斷流向西方國家的過程。“在某些觀察家看來,中東的石油與16世紀南美洲的銀子非常相像,后者流向歐洲,去創造富有活力的歐洲經濟。”即便流向黎巴嫩之類的阿拉伯國家,也大多以地產、旅游、期貨等“快進快出”的領域居多。
因管理不善被毀
凱恩發現,2020年的中東抗議活動竟集中在躲過2011年“阿拉伯之春”的國家,像黎巴嫩、伊拉克、阿爾及利亞以及蘇丹。有人覺得,這是那些“老動亂國家”經歷多年戰亂后精疲力竭,人心思定,這種說法經證明是錯誤的。因為在2020年,埃及等經歷“第一波沖擊”的國家里,要求獲得就業以及電力、水、教育和醫療等體面的公共服務的大批普通民眾依然紛紛走上街頭。
在中東,不滿的根源主要是缺乏經濟機會。1999年,一名年輕的黎巴嫩大學畢業生可以合理地期待一份體面的工作,但現在,他有可能得不到。多年來,阿拉伯青年向歐洲移徙,提供了一個安全閥以及匯款形式的收入來源,但隨著歐洲對敘利亞戰爭難民越來越不容忍,這種情況已經不復存在。
事實上,針對生活無望的抗議浪潮,2018年底首先在阿爾及利亞開始,當時布特弗利卡總統誓言競選第五個任期,結果失業的年輕人喊出了“只有香奈兒才有五號”的揶揄口號。僅僅幾周后,由于一名將軍被解職,伊拉克抗議者加入了這場沖突,到了2019年10月,黎巴嫩人也上街游行,原因是當權的薩阿德·哈里里政府增收乏術,為應對即將到期的債務,決定對互聯網用戶征稅,特別是對WhatsApp電話征收新稅,頓時點燃了火藥桶。
在2020年,中東示威運動出現更多系統性改變的目標口號,而不僅僅是一個或多個高級人物下臺,特別是禁止前政權領導層在國家過渡時期發揮作用。貝魯特大爆炸后,黎巴嫩的抗議者說:“他們(政府)所有人指的就是他們所有人。”塔赫里爾中東政策研究所高級研究員蒂莫西·卡爾達斯說:“這不是針對總理或總統的示威,這是一場要求整個統治階級下臺的抗爭。”
但到目前為止,幾乎沒有證據表明抗議活動正在迫使政府作出改變。在擁有石油財富的政治勢力面前,抗議活動仍顯得底氣不足,最典型的是黎巴嫩總理哈桑·迪亞卜已經辭職,但他所處的政府和所參與的體制仍然牢牢掌權。布魯金斯學會的中東問題專家維特斯說:“這是需要一代人去解決的問題。又一代阿拉伯人——受過更好的教育、與世界有更多聯系——正在走向互聯網。他們希望自己的生活自己作主。他們想要作出選擇。他們是大多數。他們迫切要求政治和社會變革。”
美國中東論壇和倫敦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員戴維·P·戈德曼更擔憂的是,除開影響穩定的新因素,造成“阿拉伯之春”的舊問題仍然時時發作,特別是沒有改變的錯誤農業政策更給中東國家穩定埋下“定時炸彈”。由于厄爾尼諾現象和新冠疫情肆虐,2020年的全球食品價格持續上漲,中東主要人口大國紛紛出現貿易逆差失控,而糟糕的農業政策尤其對水資源的管理不善導致了數以十萬計的農民喪失土地,許多人被逼到準備打仗的地步。眼下,埃及糧食狀況危急,該國現有夠兩到四個月使用的進口小麥供給,但它其實應當擁有超過6個月的供給量。據世界糧食計劃署說,在這個國家,40%的成人因粗劣的飲食而影響身體發育。而在敘利亞,先是政府稀少的水資源錯誤地導向小麥和棉花灌溉,以追求自給自足,接著戰亂中,地方割據勢力濫用水資源去開采石油天然氣,非法水井讓地下水位大幅降低,300萬敘利亞農民(該國總共有2000萬人口)成為貧民,數十萬農民離開農莊,住到各城市郊區的帳篷營地。經濟學家保羅·里夫林在為特拉維夫大學摩西·達揚中心撰寫的一份報告中指出,不少阿拉伯國家存在“因管理不善被毀的風險”。
重視四個方面
盡管中東歷史上從來不乏地區戰爭、民族矛盾、教派沖突,但當前動蕩程度之深、范圍之廣、時間之長前所未有。這一年,中東整體政治形勢仍未出現好轉跡象,戰亂地區局勢甚至更加惡化、混亂、恐怖,中東仍是全球最動蕩、最危險、最復雜的地緣板塊。
歷史上,中東各國曾嘗試過阿拉伯社會主義、國家資本主義、政治伊斯蘭等多條發展道路,但始終未找準對癥“藥方”。“阿拉伯之春”大潮過后,證明最新一輪中東政治嘗試再次失敗,各國、各派、各階層仍在政治苦悶之中,找不到可靠的政治出路。
突尼斯作為“阿拉伯之春”的“起點”,其“民主轉型”一度是中東政治轉型的唯一“成果”,可突尼斯駐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前代表、政治哲學博士米茲里·哈達德卻強調,同媒體神話般的表述相反,在社會現實上,面對呼喊饑餓的人民,突尼斯奉上的“民主”這道湯里沒有面包、住房、工作等等“主觀權利”,而這些恰恰是社會動亂的主要訴求。
“突尼斯此前是世俗化的、安全的、寬容的國家,而它現在卻變得社會失范、宗教原教旨主義、安全脆弱、經濟一片廢墟,我們能說的就是突尼斯出現‘大規模倒退”。“在中東各地,所謂‘阿拉伯之春要么演變為宗教極端主義的噩夢,要么帶來廢墟和破壞,西方人把突尼斯當作‘革命范例,還被授予了諾貝爾和平獎,可在不到十年里,我們的外債激增讓人目眩,經濟垂死掙扎,毫不夸張地說,‘阿拉伯之春滋生至今的成果是——摧毀的多于創建。2011年,知識分子、記者、人權活動者和其他學者鼓吹這些起來造反并宣布文明民主的‘阿拉伯人的誕生,而歷史卻任性地誕生出一個‘原教旨主義者,它先是以溫和宗教主義的虛假面目出現,接著就露出了野蠻的極端組織的真實面孔。”
歐洲中東學會副會長、英國中東學會副會長蒂姆·尼布洛克強調,關于中東問題的解決和未來,需要重視四個方面。第一,沖突的解決需要沖突各方的介入,舍此別無他法。第二,中東需要逐步建立區域性集體安全體系,區域各國有責任確保該地區的和平與安全,從而擺脫外部大國對區域安全的干預。第三,國際社會要支持擁有廣泛政治基礎的政權,保證盡可能多的民眾參與政治決策。第四,盡力減少外部軍事干涉。歷史證明:來自外部的軍事干涉只會導致局勢更趨惡化,它所帶來的問題遠遠多于可以解決的問題。他特別提到,西方國家在過去的20多年對中東的每一次軍事介入,都起到了適得其反的作用,有時影響甚至是災難性的,可至今都沒有正確認識到自己所起的破壞性作用。
幸運的是,中國并未走上這樣的錯誤道路,“中國可以扮演不同的角色,以不同的方式參與中東事務,從而使中國和中東國家雙方都能受益”。與西方國家不同,中國已與所有中東國家都建立了友好關系,這是西方國家無法企及的,中國就此擁有了特定的機遇,可以努力促使沖突各方做出妥協和達成和解。俄羅斯《軍工信使》周報記者康斯坦丁·斯特里古諾夫稱,自中國宣布“一帶一路”倡議以來,黎巴嫩視其為國家發展的重要契機,連紛爭不息的各教派也在參與新絲綢之路項目沒有異議,“中方支持黎巴嫩的主權和獨立,欣賞黎巴嫩的和平勢頭,希望這一勢頭不會因任何突發事件而中斷,這是所有域外大國中最富善意的立場,也最適合黎巴嫩乃至別的中東國家的現實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