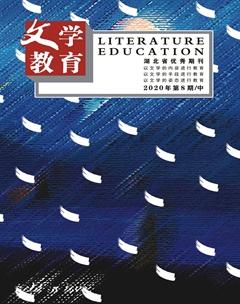回憶我的邪子嘎嘎

我的嘎嘎,也就我的外婆,是個邪子。在我們保康山區,都把瘋子叫做邪子。我的嘎嘎應該屬于那種間歇性的神經病患者。
嘎嘎姓陶,和嘎公住在離我家三四十里外的南漳板橋王家灣。小時候每次過年時,我總要隨爹媽一起去給他們拜年,一開始坐在娃娃兒背籠里背著我,后來我長大了就獨自一人去。正月十一是嘎嘎的生日。
去嘎嘎家的路特別難走,要翻竹杖坡、張道埡、樊家寨,再過摩天埡、萬丈坡、大竹坪……每次去,都要給嘎嘎帶些禮物,兩斤白糖,三升黏米。嘎嘎那里是不產水稻的,所以每年去都會帶點兒。有時也帶十幾斤黃豆,那是嘎嘎春上撒種用的。
我每次去嘎嘎家,翻過她家房子旁邊的山洼,總聽到一陣狗叫,有時還不止一只,我嚇得連忙站在她屋旁邊的田坎上,大聲疾呼:嘎嘎——嘎嘎——給我攔狗子!這時,身材瘦小的嘎嘎,一顫一顫地趕過來,一邊拖著竹條,一邊吆喝訓斥狗,又急急叫到,虎娃兒!你是個稀客呀!滿滿的喜悅之情,含在她滿臉的褶皺中,讓人心暖,也讓人心疼。
一陣噓寒問暖后,她從火房里沖杯糖茶,邊走邊用一根倒筷子在杯子里來回攪動。我剛接過杯子,她連忙又從屋里柜子中給我端一葫蘆瓢的柿皮、柿餅、核桃、花生之類的零碎食果,偶爾也有一些別人送給她,她舍不得吃的橘子、糖果。
嘎嘎和嘎公的院子,孤零零地坐落在山坳里,黃土墻,屋頂蓋著從附近撬來的薄石板,層層疊疊,因為年代久遠,石板縫里生出了幾根狗尾巴草,在風中搖曳。門前也是用石板鋪成的場子,場子外面有幾根高大的泡桐樹和楸樹,上面有幾個喜鵲窩。喜鵲總會趁人不備之時,落下來偷啄屋檐下的玉米粒。嘎嘎家四周有許多柿子樹、核桃樹,她每年都會為我們這些外孫、外孫女準備一大堆好吃的。
嘎嘎家門前不遠有個山包,山包上有座高大的古寨,一面臨崖,寨墻上的垛口清晰可辨,我曾經一度堅信,它就是課本上長城的縮影。據母親講,嘎嘎的娘家就在寨子那邊。寨子是以前附近村民為躲兵而修的寨子,具體的年代誰也說不清,厚厚的寨門需要幾個人才能推開,寨子里有股泉水,可供躲難之時飲用。每次看到那座古寨,我都想登上山頂去看看,卻不敢張嘴對嘎嘎說,一是上寨子的路不好走,再者,感覺對于她來說,寨子早已司空見慣了,一點不稀奇。
據說,嘎嘎一次意外生病,隨后就得了間歇性的神經病。那時,嘎公是大隊的糧食保管員,也是老裁縫師傅,長期不落屋。再加上,當時醫療技術也不發達,只能任其病情加重了。
我發現,一旦沒有別人時,嘎嘎嘴里總是嘀嘀咕咕不停地念叨什么,全是些無中生有的事兒。要么,誰家某某又偷了她家的糧食;要么,是嘎公背著她,跟某某村婦好上了,等等。還好,嘎公是個通情達理的人,一般都不會跟她計較的,確實忍不住了也會大聲訓斥幾句,嘎嘎或許能消停幾分鐘,不久又繼續了,大家都知道她有病,也聽之任之了。
記得小時候,嘎嘎有次來我家玩,深夜,爺爺在睡覺前,見家里的大黃狗趴在屋角落里,不肯出去,爺爺掄起拐杖,大聲呵斥,趕狗出門。嘎嘎在隔壁屋,聞聲披衣而出,硬說爺爺攆她走,并吵著找他評理。平時脾氣火爆的爺爺,氣得臉紅脖子粗,但始終沒有發一言。
有一年,嘎嘎來我家玩時恰逢落雪,到處都是白茫茫的一片,地上約摸三四寸深。嘎嘎卻急著要回家,任憑爹媽怎么勸說都不聽,最后,硬是杵著竹棍,深一腳淺一腳地要回家。父親無奈,只好跟在后面,走了一段,路滑雪厚,確實不敢再走了,父親忽生一計,以帶路為由,帶著嘎嘎在山林里兜兜轉轉,最后,天快黑時,又把嘎嘎帶回到了我們家。
嘎嘎有五個女兒,雖然也曾先后招了二姨父和幺姨父,但兩個上門女婿后來都因各種原因搬遷他鄉,不能真正為她和嘎公養老。幸虧大姨嫁得不遠,在嘎嘎生病時,和另幾個姨經常輪流回來照顧。嘎嘎臨走前,除幺姨外,另外幾個都來給她送了終。
那年過年,我與弟騎摩托去給嘎嘎上墳。在大姨夫的帶領下,我們走在曾經熟悉的小路上,路邊的許多樹木已經將這條羊腸小道遮得密密麻麻。偌大的埫田,長著齊腰深的雜草,埫中間那塊葫蘆狀的深井也已干枯,田邊的大桑樹,只剩下深褐色的主干,像一只抓向天空的枯瘦的手。遙想當初,嘎嘎背著熟睡的姨們,在地里春播秋收,在深井里舀水背水,在桑樹上采桑喂蠶,心中不由感慨萬千。
我們穿過荊棘,來到嘎嘎的墳場前,一片枯黃的茅草,幾乎掩蓋了整個墳塋。一場噼里啪啦的大火之后,我們才靠近墳前,一塊大姨夫親手打鑿的碑,立在墳前,這時我方知道,嘎嘎的真實姓名。
上墳完畢,我們轉身離去。這時,我才發現嘎嘎門對面的那個深褐色的古寨,雖然依然屹立不倒,可是垛口已經不復存在了。
張道虎,現代農民,在鄉村從事瓜果養殖和文物保護,業余寫作。現居湖北保康縣馬良鎮峽峪河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