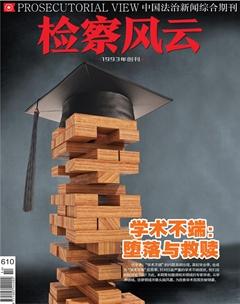學術“扶正”之路

近年來,我國學術界風起云涌,有人嘗到科研成果的甜,也有人自食“學術不端”的苦。
面對學術界愈演愈烈的“學術不端”現象,學術界如何從嚴治理?核心期刊在遴選論文中有嚴格的審核流程,所以很多學者以自己論文可以在核心期刊中發表為榮。那么核心期刊的審核流程有多“嚴”?核心期刊是否衡量論文“含金量”的唯一標準?
為探討以上問題,本期策劃特邀復旦大學副教授胡安安,請他解讀高校如何嚴于律己端正學術態度,同時分析國內外核心期刊遴選體系,為如何提高國內學術質量建言獻策。
端正學術態度? 高校如何嚴于律己
《檢察風云》:近年我國對學術論文的審核管理越發嚴格。請問復旦大學在審核本科、碩士以及博士學位論文時,相比過去推出哪些更嚴格的審核規定?
胡安安:以復旦大學為例,目前對研究生學位論文的要求主要體現在三個“嚴格”上。
一是嚴格規定提交時限。如果是秋季畢業(每年7月)的學生,則最晚要在3月31日前完成學位論文的預審。這里的預審意味著導師和2—3位專家要完成對學位論文的審閱,給出修改意見,并進行至少一輪的修改。如果晚于提交日,則無法申請相應學期的畢業資格,這對一些有“拖延癥”的研究生來說是極大的壓力。完成預審后至6月初學位論文答辯前,至少還要經過導師最終審核、文字相似度檢驗、明審(或盲審)等三個重要環節,任何一個環節出現延誤都可能造成當期失去畢業資格。
二是嚴格規范文字相似度比例。對學位論文進行文字相似度檢驗(俗稱“查重”)是目前最常用也是最有效的審核手段。復旦大學要求研究生學位論文統一由校方進行相似度檢測,在檢測報告的“去除引用”項目中,如果相似度小于等于10%為通過;如果在10%—20%(含)之間,則需出具專家鑒定報告證明論文無學術不端行為,在規定的時間內修改論文后重新檢測,符合小于等于10%為通過;如果在20%以上則提交學位委員會認定,若屬學術不端行為交由學校處理,不屬學術不端行為須進行3個月以上論文修改再提交檢測。
三是嚴格審核論文質量。以碩士學位論文為例進行說明,首先需要完成導師和至少兩位專家的論文預審,然后才可以進行論文相似度檢驗。通過相似度檢驗后,學位論文進入送審環節。碩士學位論文有一定的“盲審”比例,如果被確定為盲審對象,則盲審版學位論文會由2—3名副高職稱以上的專家進行匿名審核;如果不屬于盲審對象,則由導師牽頭,將論文送交2—3名副高職稱以上的專家進行公開審核。需要指出的是,目前國內重點大學碩士、博士學位論文審核基本都包含“盲審”環節,即評審專家不知道學生和導師的信息,學生和導師也不知道由哪位專家評閱。這樣既充分發揮了同行專家評議的作用,也規避了“人情面子”,最大限度地保證了學位論文的質量。各個高校每年都有一定比例的碩士生、博士生無法通過盲審,不得不申請延期修改論文,在下一個畢業周期重新提交論文。
審核結果也有非常嚴格的規定。同樣以碩士學位論文為例,在所有評審專家的論文學術水平評價一欄中,只要出現“一般”的打分,則須修改論文并提交修改說明,經學生、導師簽字后,再請分委員會委員一人及相關方向兩位教授(共3人)簽名后才可以申請答辯。如果出現“不合格”的打分,則直接至少延期三個月畢業,修改學位論文后在下一個畢業周期重新進行論文審核流程,且修改版論文將發送至給予“不合格”評定的專家處進行再次評定。
《檢察風云》:您認為審核論文環節,還可以在哪些方面進行改進?
胡安安:客觀來說,國內高校研究生(尤其是博士研究生)的學位論文審核機制是能夠保證質量的。同時,近幾年教育部和各省教育機構都在加強學位論文審核要求,社會各界公開監督的力度也在加大。
從改進的視角來看,我個人認為研究生學位論文審核環節在專業碩士領域還有進一步的提升空間。目前國內碩士研究生培養分為科學學位碩士(簡稱“學碩”或“科碩”)和專業學位碩士(簡稱“專碩”)兩類。根據教育部發布的數據,2018年國內專業學位碩士研究生在讀139.73萬人,科學學位碩士研究生在讀94.45萬人,專碩人數遠高于學碩;招生人數同樣如此。除了在讀規模外,專碩與學碩區別還體現在培養目標上,專碩更加強調應用性,側重培養理論結合實踐的專業人才。但需要看到,現有碩士研究生的學位論文審核機制源自學碩,在實際操作層面難免出現“適用性”問題。從近幾年公開報道的學位論文事后抽檢結果來看,專業碩士學位論文是“重災區”。在加強專業碩士論文質量把關的同時,也有必要反思相應的審核機制是否需要進行微調,可以針對學生人數更多的專業碩士設定更為細化的學位論文審核標準,以便更好地解決上述問題。
期刊種類繁多? 論文如何自證“含金量”
《檢察風云》:在國內,很多學術論文要求必須發核心期刊。那么什么是核心期刊?
胡安安:目前,越來越多的高校取消了碩士研究生就讀期間發表學術論文(也被稱為“小論文”)的要求。2020年2月,教育部、科技部聯合印發了《關于規范高等學校SCI論文相關指標使用、樹立正確評價導向的若干意見》的通知,明確指出:“不宜以發表SCI論文數量和影響因子等指標作為學生畢業和學位授予的限制性條件。”可以看到,我國研究生的科研培養目標將更加側重水平“質”的提升而非論文“量”的增加。
過去經常見諸報端的“中文核心期刊”說法,實際上可以簡單看成是一個期刊的列表,與國際上的科學引文索引(Science Citation Index, 簡稱 SCI)和社會科學引文索引(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簡稱SSCI)標準類似,是一套動態調整的期刊目錄。簡單地說,國內“核心期刊”是一種泛指,在實踐過程中主要指三個定期更新的期刊目錄,分別是: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研究評價中心發布的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簡稱CSSCI或南大核心)、北京大學圖書館發布的核心期刊目錄(簡稱北大核心)、中國科學院文獻情報中心發布的中國科學引文數據庫(簡稱CSCD)。
需要特別說明的是,除了上述定期發布的期刊目錄外,國內還有其他期刊索引目錄發布,不同學科也有體現學科自身特色的期刊列表,不能簡單通過“核心期刊”四個字來評定期刊質量。以高校為例,不同學校(或院系)通常會制定屬于自己的期刊列表,在期刊數量上少于上述列表,發表難度也更高。
《檢察風云》:我國主要有哪些核心期刊遴選體系?
胡安安:新時期,國家更加強調“科研評估體系”的優化與完善。除了上述期刊目錄外,學術代表作、論文影響力、同行評價、服務國家和人民的實踐性等因素都是重要的科研評估標準。在此背景下,近幾年國內高校不斷調整研究生學位審議過程中的評定依據和質量標準,對于碩士研究生,不再硬性規定就讀期間發表學術論文,更加側重學生基礎能力和創新能力的培養。
《檢察風云》:如學術論文想刊登在最具代表性的核心期刊上,需要經過怎樣的審核流程?
胡安安:以人文社會學科為例,一篇學術論文的初稿提交到期刊信息系統中,通常要經過系統形式審核、編輯部初審、同行審核(含匿名審核)、編輯部第二輪審核、論文修改與說明、第三輪審核、主編確認等多個環節,其中任何一個環節都有可能被拒稿。從發表周期來看,一篇論文從投稿到在高質量期刊印發出來,超過一年時間是常態。能夠在本領域最權威、排名最佳的期刊上發表學術論文,絕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檢察風云》:國際上普遍被認可的核心期刊遴選體系有哪些?
胡安安:國際上評價期刊質量有多種標準,簡單地說,至少有三套遴選體系。
一是看期刊是否被SCI、SSCI、A&HCI(Art and Humanities Citation Index,藝術與人文引文索引)等數據庫檢索,這是評判一個期刊學術聲譽最為簡便的標準。
二是看期刊的各類影響因子指標,指標越好的期刊往往意味著聲譽越好,相應的發表難度也越大。
三是看所在學科的具體期刊列表。一個期刊是否在列表上、評級如何,這是具體學科評判期刊聲譽最為重要的標準。以管理學科為例,目前以“UTD期刊”排名最為權威,其由美國德克薩斯大學達拉斯分校定期發布,涵蓋管理科學、會計學、金融、市場營銷、戰略管理等24本國際頂級刊物,被公認代表國際管理學研究水平的最高排名。

論文量產豐富? 研究成果如何飄香國內外
《檢察風云》:浙江大學鄭強教授曾說,日本東京大學和京都大學任選一所大學,每年發表在《科學》和《自然》上的文章,是中國前10所大學發表文章的總和。您認為我國優質大學的學術文章難以發表在國際核心期刊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胡安安:我個人認為這個問題需要辯證地看。
首先,與國際學者相比,我國學者在國際頂級、權威學術刊物上發表的論文數量確實存在差距,其原因可以簡單概括為天時、地利、人和。改革開放前,國內學者科研基礎較弱,參與國際科研合作少,很難有機會在國際頂級期刊上發表論文;改革開放后,國內學者的追趕速度加快,差距在縮小,但“溝壑”仍然客觀存在,此為天時。
就像每個高校都有自己較為優勢的學科一樣,大量從事前沿學術研究的“老牌勁旅”集中在海外科研院所,這種“地利”優勢最直接的表現就是國際期刊成果多。隨著互聯網時代的到來,區域間的“地利”差距正逐步被稀釋。
與天時、地利相對應,過去我國學者參與國際學術研討、合作、交流的機會確實有限,無論在視野還是在發表經驗上都欠缺“人和”,造成在國際頂級期刊上成果較少的情況。
其次,在承認客觀不足的同時也要看到,近幾年我國學者在國際最權威學術刊物上發表論文遞增的趨勢沒有變,在國際科研學術界的發言權越來越大。這里以2020年4月底《自然》雜志剛剛發布的2020自然指數年度榜單(Nature Index 2020 annual tables)為例簡單加以佐證。“自然指數”由《自然》期刊定期發布,是一個體現學術論文作者單位信息和機構關系的數據庫,涉及82種高質量自然科學期刊,這些期刊均由在職科學家所組成的獨立小組選出 ,相關排名被公認為評價一國科研水平的重要指標。
榜單數據顯示,美國依然是2019年自然科學領域高質量科研產出最多的國家,中國居第二位。從指數的貢獻度來看,2015年至2019年,美國經調整后的貢獻份額下降了10%,中國增加了63.5%,是增長最快的國家。具體到科研機構,榜單中前十名有三所中國院校:排名第一的中國科學院、排名第八的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排名第十的北京大學。此外,在今年的自然指數年度榜單上,還增加了機構上升之星榜單(Fastest movers since 2015),中國穩居第一,前44家機構上升之星全部來自中國。
數據不會說謊,可以看到新時期的中國科研正在實現高速追趕,在為世界作出更大的貢獻。
《檢察風云》:如何提高我國核心期刊以及學術文章的國際影響力?
胡安安:我個人認為國際影響力不是呼吁出來的,而是靠科研工作者的扎實奮斗、靠全社會的大力支持來逐步提升的。未來有四個層面值得各方重點關注,我簡單歸納為十六個字:“扎根本土、開放合作、規范操作、側重實效。”
首先是扎根本土。中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也是面積最大的國家之一,有著最為復雜的自然環境,對社會治理體系、商業運作規則的要求極高。這次新冠疫情引發學術界深度思考,無論是自然科學還是社會科學,結合中國實際情境展開研究,就是對世界科研最大的貢獻。
其次是開放合作。習總書記多次強調,“中國開放的大門只會越開越大”,未來學術刊物、學術論文的國際合作定會越來越多,應實現“引進來”與“走出去”同步發展。
第三是規范操作。一方面,科研工作者需要努力追趕國際前沿;另一方面,出版工作者也需要盡快與國際接軌,在學術倫理道德檢測、審核流程設置、預錄用與出版周期等環節實現進一步的規范操作。
第四是側重實效。近期國內管理學界最頂級的兩本期刊《管理世界》和《經濟研究》分別發出了“研究中國問題、講好中國故事”的號召,指出“優秀成果應當具備思想啟迪性、理論創造性與政策參考性”。這種務實求真的做法為國內學術期刊作出了表率,為提升中國期刊的國際影響力邁出了一大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