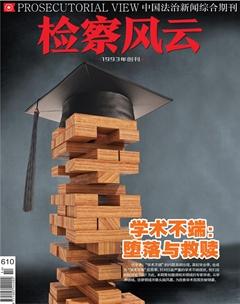那些年,那些驚世駭俗的女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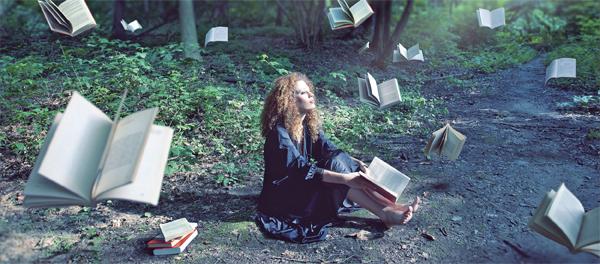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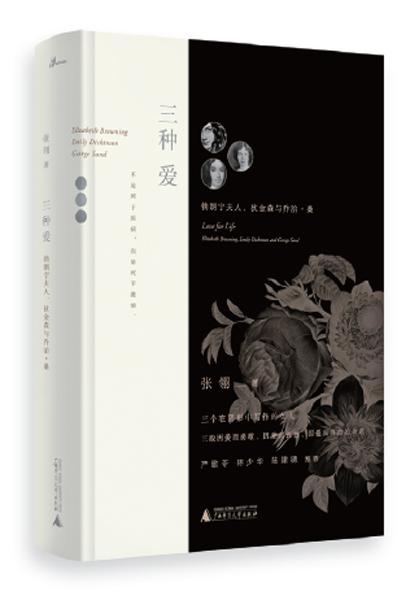
書名:《三種愛:勃朗寧夫人、狄金森與喬治·桑》
作者:張翎?
出版: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一
小說寫得久了,我的大多數熟人朋友都理所當然地以為我畢業于某某學院的中文系。少數幾位真正了解我背景的,在向他們的朋友介紹我時,則會說我畢業于復旦大學的“外語系”。每當此時,我總會不厭其煩地糾正他們:是“外文系”不是“外語系”。“語”和“文”在別人看來只是皮毛級別上的一字之差,不值得一個頭腦正常的人為此糾結。但對我來說,這一字之差的背后,是一個巨大的觀念差別。實用主義者已經把一門語言從它蘊含的人文背景里剝離開來,把它制作成一樣簡單的勞動或貿易工具。我忍不住要為此發出點類似于嬰兒不適時發出的嚶嚶聲——那是我的微弱抗議,即使我的聲音聽起來微不足道,甚至有那么一點矯情。
多年前我考入的那個學科,全稱是“復旦大學外文系英美語言文學專業”。那個年代的外文系,課程設置環環相扣,相當細致全面。除了專業英美文學的必修和選修課,還有古代漢語、現代漢語、哲學、歐洲文學史課,駱玉明、豐華瞻、索天章、葛傳椝等諸位先生,都曾經是任課或講座課的老師。他們別具一格的授課風格,在我記憶中烙下了永久印記。我的大學時代,原版英文資訊非常貧瘠,學生只能依賴從外文書店購買的紙質粗劣的影印本原著和文學史料(那時大家都毫無版權意識),以及學貫中西的老教授們的口授中,漸漸進入一個由許多振聾發聵的名字組成的偉大文學系統。喬叟、彌爾頓、莎士比亞、狄更斯、哈代、巴爾扎克、雨果、霍桑、惠特曼……他們都是清一色的男人。
我在這一串熠熠生輝的名字中尋找女人,女人的名字是后來才出現的,稀少且彼此間隔遙遠,正應了一句英文成語“few and far in between”。
二
女人的名字雖少且間隔遙遠,但一旦出現,便帶著響亮的不可復制的獨特回聲,立刻抓住了我的心。她們在文學史上炸開了一條狹小卻深刻的溝壑,固若金湯的男人世界于是就有了裂縫。女人隨時有可能掉落淹沒在縫隙中,所以她們得奮力攀緣,以求在男人的世界里立住身子,于是就有了各種奇聞逸事。比如那個帶著女兒來到巴黎,用一根雪茄和一桿羽毛筆將半個法國文壇收編到她的男式馬褲下,又讓另外半個文壇用唾沫淹沒自己的喬治·桑;那個與有婦之夫公開同居,使整個倫敦社交圈子避之如瘟疫,只能以男人筆名發表作品的喬治·艾略特;那個對每一個經過她生命的有頭腦的男人寫盡曖昧奉承之語卻終身未嫁,生前沒有署名發表過任何一首詩作,死后卻被冠上和惠特曼、愛倫·坡齊名的“美國夜鶯”之稱的艾米莉·狄金森;那個連下樓梯都需要弟弟背抱,卻膽敢以一場異國私奔在英國文壇上炸起一地飛塵的伊麗莎白·巴雷特·勃朗寧;還有那個讓徐志摩驚若天人,在男人和女人的懷抱里輪番索取溫暖卻最終心懷寂寞地死去的曼殊菲兒……
這些女人在她們生活的年代,被歸入有傷風化的圈子,大多處于聲名狼藉的境地。即使依照今天相對寬松的社會標準,她們依舊是驚世駭俗的異類,但毫無疑問她們創造了歷史。她們師承了男人們創造的文學傳統,卻沒有中規中矩地行走在男人踩踏出來的道路上。她們從男人的源頭走出來,走入了一個分支。這個分支漸行漸寬,漸行漸遠,最后成為和源頭相映生輝的另一條河流。假如從世界文學史的版圖上抹去這條分支,河流將不再是河流——至少不再是完整的河流。
有過她們,文學不可能再退回到沒有她們的時候,一切都已經不同。在和男人博弈的過程里,寫書的女人創造了獨屬于自己的聲音,情愛的、欲望的、文學的、社會的、政治的。
她們在風花雪月的書寫中,魯莽地插入了對貧窮不公、性別差距、黑奴貿易、戰爭、獨立等社會問題的見解,瓜分了慣常屬于男性的話題。男人們一夜醒來,突然發覺那些他們一直以為是花瓶和飾物的女人,除了對詩歌的韻腳、小說的橋段略有所知,居然也懂得邏輯和哲思。男人的心情非常復雜——震驚,疑惑,贊嘆,嫉妒,仇視,不屑……各種情緒紛沓而至,兼而有之。夢醒之后的男人迅速分化,有的成為女人最堅定的盟友,有的成為女人最堅定的敵人,有的冷眼靜觀事態的發展。分化的過程很長,一路延續至今。
三
對這些文學女子的好奇,引發了我想在她們的生活表層撕開一個缺口,借以窺視她們心靈真相的欲望。這個欲望由來已久,卻因故遲遲未能付諸行動。直到幾年前我辭去全職的聽力康復醫師職業,贏得了時間的支配權,才慢慢開始了對她們生命軌跡的漫長探索旅途。
這個旅途始于喬治·桑、艾米莉·狄金森和勃朗寧夫人。在動筆書寫這本書之前,我都專程去過她們的故居——法國的諾昂鎮,意大利的佛羅倫薩,美國麻省的艾默斯特鎮。我在她們的臥室里憑窗站立,借她們曾經的視角,想象她們眼中曾經的世界。在她們的舊居,在她們身世的記錄中,我驚異地發現了一個事實:遠隔著大洋而居的女人們,一生中也許有機會見面,也許永遠沒有,但她們都知道彼此的存在,心里藏著一份惺惺相惜。勃朗寧夫人曾經以羸弱之軀,冒著感染致命肺炎的危險,在寒冬里穿越半個巴黎去尋找喬治·桑;艾米莉·狄金森臥室墻壁上掛著的唯一飾物,是勃朗寧夫人和喬治·艾略特的畫像……原本素不相識的她們,從世界看待她們的目光中,認出了彼此是知音。在男人的世界里,她們是數目稀少卻忠貞不渝的盟友。
在她們故居采風途中,我也曾探訪過她們的墓地,在她們的棺槨或墓碑上留下了我的密語,有時是一張紙條,有時是一塊石頭。她們遺留在這個世界上的舊跡,使我飄浮在半空的靈感砰然落地。站在她們墓碑前,我感覺自己觸摸到了她們的靈魂。我猜測著她們在今天的世界里會怎樣生存。是略微容易一些?還是更為艱難?
離開她們墓地,我知道我的路還會持續下去,我還會走入曼殊菲兒、喬治·艾略特、弗吉尼亞·伍爾夫、簡·奧斯汀等女作家的人生。在未來的日子里,我也會在她們的墓碑放上我的紙條,我的石頭。或許,還有我的書——關于她們的書。
(選摘:謝靜雯)
編輯:黃靈? yeshzhwu@foxmail.com
新書速遞
美國硅谷是當今世界高新技術創新和發展的翹楚。20世紀60年代,當硅谷還處在初步發展之際,馬薩諸塞州128號公路已被稱為“美國科技高速公路”,但從20世紀80年代起硅谷取代128號公路成為美國科技創新源頭。那么,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書中,作者通過上百次的訪談,結合豐富的案例分析后認為,這兩個地區盡管有著相似的歷史和技術,但硅谷建立了一個分散而又相互合作的工業體系,而128號公路則是由相互獨立、自給自足的公司所主導;要具有區域競爭優勢,必須具備順應時代潮流、適合自身發展的制度優勢和文化優勢。本書研究時間跨度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至20世紀90年代中期,從某種角度上講,這也是一部美國高科技產業的發展史。
(文/曉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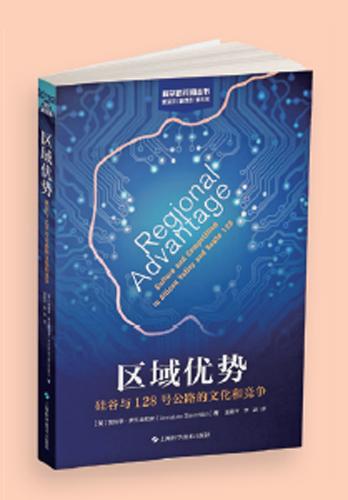
書名:《區域優勢:硅谷與128號公路的文化和競爭》
作者:安納李·薩克森尼安 [美]
譯者:溫建平 李波
出版: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