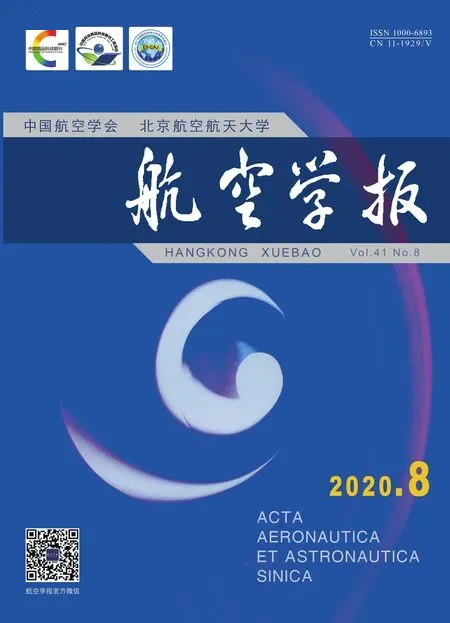民機極限飛行狀態的動態氣動力試驗與建模
岑飛,李清,劉志濤,蔣永,張磊
1. 清華大學 自動化系,北京 100084
2. 中國空氣動力研究與發展中心 低速空氣動力研究所,綿陽 621000
飛行安全是大型商用運輸機設計研究中備受關注的核心問題。按照國際民航組織(ICAO)和商業航空安全委員會(CAST)分類標準[1],飛行事故按類型分為:可控飛行撞地(CFIT)、空中失火(F-NI)、燃油泄漏(FUEL)、飛行失控(Loss of Control-in Flight, LOC-I)、空域沖突(MAC)、沖出跑道(RE)、動力系統故障(SCF-PP)等。按事故類型統計商用航空運輸中人員傷亡飛行事故顯示[2],飛行失控在2008—2017的10年間共造成14起事故、1 131人 死亡,在所有飛行事故類型中,無論事故數量還是死亡人數均占比最高。對飛行失控事故的飛行記錄數據分析表明[3],因惡劣天氣、系統故障或機組人為因素等使飛機進入超出正常飛行包線的極限飛行狀態,是造成飛行失控的重要原因之一。近年發生的波音737MAX事故進一步說明,在一些特定的民用飛機設計約束之下,飛機迎角的快速增加,并進而進入失速或過失速狀態,是民用飛機在節能、減排等多種約束目標優化的情況下可能會出現的問題,而目前波音737MAX的處理方法存在很大的風險,因此需要從飛機本體特性和新飛行控制律的角度加以研究。事實上,按線性、定常條件設計的飛機遭遇非線性、非定常的動態氣動力環境, 一直存在潛在的風險,如果對其動態氣動特性缺乏足夠的認識,沒有建立精確的動態氣動力模型以支撐駕駛員進行應對此種意外情況的應急培訓,其結果往往是災難性的。通過開展民機極限飛行狀態的動態氣動力特性研究, 來改善飛機飛行失控預防、極限狀態改出、飛行模擬訓練和飛行事故分析等,以減少或杜絕類似事件再次發生,無疑是今后減少和避免國內外諸多空難事故需要探索的一個重要技術途徑。
飛機不慎進入超出正常飛機包線的極限飛行狀態時,有兩個顯著特征[4]:一是迎角、側滑角變化范圍廣;二是飛機處于運動快速變化狀態。這種復雜的非常規運動環境與人們熟知的定常、直線飛行有著本質區別,這不僅體現在飛機的氣動力特性本身——氣動力具有完全的動態特征,即非線性、非定常性質;而且體現在氣動力風洞試驗設計與動態氣動特性研究的關系方面,即這種情況下的動態氣動特性研究究竟需要怎樣的風洞試驗數據,以及風洞試驗數據如何用于構建氣動力模型的問題[5]。近30年來,關于飛機的大迎角與動態氣動特性研究,主要圍繞戰斗機大迎角過失速機動的氣動力試驗與建模開展,發展起來的動導數、大振幅振蕩、旋轉天平等動態氣動力風洞試驗方法[6-7],已經在戰斗機過失速機動與尾旋研究中得到廣泛應用。相應的,發展了多種建模方法,包括以氣動導數模型[8]、非線性階躍響應模型[9]、狀態空間模型[10]、微分方程模型[11]等為代表的數學建模方法以及以神經網絡模型[12]、模糊邏輯模型[13]和支持向量機模型[14]等為代表的人工智能建模方法,這些方法應用在戰斗機布局飛機氣動特性研究與建模中,使得戰斗機大迎角機動過程中的動態氣動力問題得到相當充分的認識和不同程度的解決[15-17]。但是,動態氣動力特性與飛機布局形式密切關聯[18],而目前對于運輸類布局飛機極限飛行狀態氣動力試驗與建模研究仍然有限,對于民機失速,尤其是過失速動態氣動特性尚缺乏深入的風洞試驗研究;目前飛行模擬器中對于超出正常迎角/側滑角包線范圍的數據,一般是在正常包線數據基礎上外推[19],存在定性的誤差,也難以支撐應對極限飛行狀態的飛行模擬訓練。
本文針對典型民機布局飛機模型,主要關注極限飛行狀態中動態氣動力的非線性與非定常特征,從風洞動態試驗方法中蘊含的假設和應用條件出發,結合極限飛行狀態特點和動導數、大振幅試驗結果,分析大迎角區域動態氣動力參數影響規律和非線性模型結構,在此基礎上探討極限飛行狀態動態氣動力的風洞試驗設計和非定常氣動力建模問題。
1 飛機模型
考慮到布局典型性,選擇NASA通用運輸機標模(Common Research Model, CRM)作為研究模型。CRM是NASA發布的代表典型雙發、遠程、雙通道寬體商用運輸機布局的標模,飛機三維數模及數據面向國際合作公開發布[20]。該標模對機翼進行全新設計,采用現代先進的超臨界翼型,飛機機翼展弦比為9.0,根稍比為0.275,機翼1/4弦線后掠角為35°;而飛機的機身、平尾和垂尾等部位的關鍵尺寸、布局參數與波音777-200保持一致[21],設計巡航馬赫數Ma=0.85(設計點升力系數CL=0.5),飛機氣動布局如圖1所示。值得一提的是,在NASA發布的CRM原始標模中,飛機不帶操縱面,本研究中為了后續開展極限飛行狀態操控特性研究需要,參考波音777-200操縱面設計了升降舵、副翼和方向舵。

圖1 CRM布局
采用2.45%縮比模型開展動態氣動力風洞試驗,模型主要參數如表1所示[22]。

表1 CRM動態試驗模型參數[22]
2 試驗方法
2.1 動態氣動力數學模型及其簡化形式
飛機受到的氣動力可以嚴格地表示為飛行狀態變量的泛函:
Ci(t)=Ci(M(t),h(t),δ(t),α(τ),β(τ),
p(τ),q(τ),r(τ)) -∞≤τ≤t
(1)
式中:i=L,D,Y,Mx,My,Mz,分別表示升力、阻力、側向力和三軸氣動力矩;Ci(t)表示在給定t時刻的氣動力和力矩,其不僅與t時刻的飛行狀態參數有關,而且與飛行狀態參數變化的歷史有關。這個表達式能夠反映空氣流動產生的氣動力的非定常、非線性實質,但顯然并沒有簡單的途徑可以得到這種泛函的數值[23]。為此,目前的工程實踐中通常引入3個假設對這一泛函做如下準定常化、線性化處理[7,23]:
假設1假設較遠歷史狀態對t時刻的氣動力影響可以忽略,以飛行狀態參數α(τ)為例,在t時刻附近展開為泰勒級數:

(2)
則可以用t時刻的α及其各階導數值代替式(1)中的α(τ),其他飛行狀態參數作類似處理:

(3)
引入該假設后,氣動力變成關于飛行狀態參數的準定常、非線性模型,大部分實際問題中,只保留到飛行姿態角速度,就可以保證足夠的精度,即
(4)
不失一般性,式(4)可以分解為兩部分,即靜態氣動力Ci1和動態氣動力Ci2,Ci1是關于飛機平動運動參數的非線性函數(與飛機姿態角相關),Ci2是關于飛機轉動參數的非線性函數(與飛機姿態角速度相關):
Ci(t)=Ci1(M,h,δ,α,β)+
(5)
假設2假設動態氣動力中,各運動參數對氣動力影響可以相互解耦,即
Ci2(M,h,δ,α,β;p)+…
(6)
假設3假設動態氣動力中,氣動力隨飛機姿態角速度是線性變化的,即
(7)

為無因次角速率。
由此,可得
(8)
綜上,準定常條件下氣動力線性化模型表達式為
(9)
基于上述假設的數學模型以及發展的與之相應的風洞動態試驗方法,一般都嚴格限制在小到中等迎角時氣動力非線性、非定常現象很弱的范圍,對于極限飛行狀態,上述假設是否仍然適用及其所帶來的影響,以及如何進行試驗設計和建模需要結合特定飛機布局特點進行分析。
2.2 試驗內容與方法
結合2.1節分析,盡管在大迎角條件下,上述準定常化、線性化方法,難以嚴格描述復雜非線性特征,但是實際上任何的非線性氣動力現象都是從線性氣動力出現異常發展而來的[23]。基于這個認識,針對極限飛行狀態動態氣動力試驗與建模,本文基本思路是:利用已經發展成熟的動導數試驗方法,開展包含大迎角在內的不同頻率、不同振幅的動導數試驗,分析不同迎角區域參數影響規律和動態氣動力的非線性特征,建立非線性動態氣動力模型;利用大振幅試驗結果,對比線性和非線性氣動力模型,對動態氣動力的非線性特征和非線性建模結果進行分析和驗證,并進一步研究氣動力的非定常特征,進行非定常氣動力建模。
動導數試驗通過強迫振蕩方式進行,分為俯仰強迫振蕩、偏航強迫振蕩、滾轉強迫振蕩試驗。試驗在中國空氣動力研究與發展中心(CARDC)FL-14風洞開展(圖2)。試驗時,模型繞相應體軸在不同迎角作不同振幅、頻率的正弦振蕩,按照飛機的短周期或荷蘭滾運動模態特征,或者飛機飛行運動中涉及的飛行狀態參數典型范圍,確定參數模擬范圍。試驗風速為30 m/s,試驗迎角范圍為-10°~60°,振蕩頻率范圍為0.5~1.5 Hz,振幅范圍為3°~10°。

圖2 俯仰振蕩和滾轉振蕩試驗
大振幅振蕩試驗在同一套試驗裝置上開展,在不同迎角區域作振幅分別為10°、15°、20°的運動,頻率范圍在0.25~1.25 Hz之間。
3 動態氣動力非線性特性
3.1 非線性特征分析
以通過俯仰振蕩獲取俯仰動導數為例進行分析,在俯仰振蕩中,飛機運動的數學描述為
(10)

(11)
圖3給出了-4°≤α≤60°范圍內不同振蕩頻率f、振幅A下俯仰阻尼導數試驗結果,試驗參數如表2所示。

表2 俯仰動導數試驗參數

圖3 不同頻率、振幅俯仰阻尼導數
在常規飛行條件下,利用縮比模型開展動導數試驗時,主要考慮減縮頻率相似[23],以表征全尺寸飛機和模型之間關于剛體運動和繞流流體運動在時域上的同時性,形如:
(12)
圖4中分別給出小迎角(α0=4°)、中大迎角(α0=16°)、大迎角(α0=40°)下,以振蕩頻率f=1 Hz、 振幅A=5° 開展動導數試驗時,繪制的俯仰力矩系數Cm關于迎角的遲滯回線,圖中不同“截止頻率”指的是數據處理時的濾波截止頻率。例如,截止頻率為1 Hz(與強迫振蕩頻率相同,即通常說的保留1階量),即認為繞流流場變化頻率與飛機剛體運動頻率一致,遲滯回線為標準橢圓。眾所周知,基于小擾動線性化假設的動導數就是由該1階量計算得到的。可以看出,在常規小迎角范圍或者在迎角特別大時,保留到高階量(如6階)與只留1階量相比遲滯回線是比較接近的,即表示此時用動導數就可以比較準確地描述飛機的動態氣動力,俯仰力矩隨俯仰角速度是接近線性變化的;但是,如圖4(b)所示,在該中大迎角范圍時,氣動力存在明顯的高階量,因此,俯仰力矩隨俯仰角速度變化有明顯的非線性特征,此時,常規的線化導數不能精確反映動態氣動力特性。從對氣動力的頻譜分析也可以看出,對應的數據含有1~6階量(7階以上基本沒有),一方面說明了該區域動態氣動力存在顯著非線性,另一方面該結果也表明對于氣動力遲滯回線的計算,保留到6階(當強迫振蕩頻率為1 Hz時,截止頻率為6 Hz)是比較合理的。

圖4 不同平均迎角下強迫振蕩時俯仰力矩隨迎角變化的遲滯回線
上述結果說明了在10°<α<35°范圍內,式(7)所示的線性化假設不成立,必須對動態氣動力的試驗方法和數學模型進行改進。為了進一步分析動態氣動力與角速率之間的關系,圖4(d)給出了振幅和頻率均不同,但是在強迫振蕩平均迎角處(α0=15°)最大俯仰角速率相同的兩條俯仰力矩遲滯回線。可見,盡管強迫振蕩振幅和頻率不同,但在最大角速率相同的位置,遲滯回線是非常接近的。這也是3.2節中把最大角速率引入到非線性動態氣動力建模中的一個依據。
3.2 非線性氣動力模型
由于在飛機的振蕩運動中,角速率不僅與頻率相關,而且振幅相關,式(11)定義的最大無因次角速率作為反映飛機動態運動的特征參數,可以同時體現頻率和振幅對飛機動態氣動特性的影響。為此,在本研究中引入最大無因次角速率作為阻尼導數的一個影響因子,以俯仰阻尼導數為例,即
(13)
用α0=15°、A=10°的俯仰大振幅振蕩為例對上述氣動力模型進行分析和驗證。俯仰大振幅運動如式(10)所示,根據表2的動導數試驗結果進行關于角速率的線性或非線性建模,線性數學模型表達式為
(14)
非線性數學模型表達式為

(15)
圖5、圖6給出了不同大振幅振蕩頻率(對應于不同的角速率區間)下,俯仰大振幅振蕩試驗結果和線性、非線性建模計算結果的對比。為了清楚識別圖中氣動力曲線特征,先對圖中曲線形態、標注及其物理意義進行說明:以圖5為例,圖中靜態試驗對應飛機俯仰角速度q=0(°)/s;在大振幅振蕩運動中,由于動態氣動力貢獻,出現典型的“遲滯回線”,箭頭表示對應曲線中飛機角運動的方向(箭頭指向α增大的方向則q為正,反之為負);對于俯仰力矩回線,氣動力曲線隨飛機運動沿著逆時針方向變化表明俯仰阻尼導數為負,飛機是動穩定的,反之則動不穩定,顯然若回線出現交叉表明飛機動穩定性的突變,預示飛機可能會出現俯仰極限環振蕩、機翼搖滾等非線性飛行力學現象。

圖5 f=0.25,0.5 Hz時氣動力建模結果和大振幅振蕩試驗結果對比(α0=15°,A=10°)

圖6 f=1,1.25 Hz時氣動力建模結果和大振幅振蕩試驗結果對比(α0=15°,A=10°)

4 動態氣動力非定常特性
從第3節大振幅試驗結果可以看出,加入非線性影響因素后,可以捕捉到飛機主要的動穩定性特征,但僅考慮非線性特性仍不足以精確定量描述運輸機在進入極限飛行狀態后可能面臨的大迎角、快速運動時的氣動特性,特別是在飛行失控運動中角速率較大時,氣動力將呈現出較強的時間相關性。因此,在具體分析特定快速運動過程中的動態氣動力時,還需考慮非定常特性影響。為了描述氣動力的非定常特性,這里采用Goman-Khrabrov狀態空間建模方法(G-K模型)[10],通過引入描述流場狀態的內部變量即氣流分離點位置,來描述分離流流場的動態發展過程,從而建立氣動力響應的非定常模型。該模型已經成功應用在戰斗機布局飛機非定常氣動力建模中[15,24]。
本文以G-K模型以及Fan和Lutze等[25]對該模型的發展為基礎,以升力系數為例展開分析,模型表達式為
(16)
式中:
CLα(x)=a1+b1x+c1x2

對于該非定常氣動力模型,表征非定常特性的時間常數τ1、τ2的確定是關鍵。針對該問題,文獻[10]推導了通過動導數來辨識時間常數的關系式,從而可以利用動導數試驗數據確定時間常數。本文給出了另一種方法,即利用靜態測力和大振幅振蕩試驗結果確定模型時間常數的方法,如下所述。
1)δ、αm、CL0、a1、b1、c1只與靜態氣動力有關,因此,利用靜態測力試驗結果,用最小二乘擬合進行上述參數辨識。
2) 利用大振幅振蕩試驗結果,對τ1、τ2、a2、b2、c2同樣采用最小二乘擬合進行參數辨識。

按照這組參數建立非定常氣動力數學模型,與靜態測力和大振幅試驗結果對比如圖7、圖8所示。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參數只用了f=1 Hz時的大振幅試驗數據進行模型中與非定常特性有關的參數辨識,圖7給出了辨識的非定常氣動力模型計算結果與試驗結果對比,圖8中給出了使用該同一組參數(即τ1、τ2等參數保持不變)其他大振幅運動頻率時的非定常氣動力模型預測結果,與試驗結果均吻合良好。可見,對該民機布局飛機,使用上述非定常氣動力模型可以準確描述氣動力的非定常特征。

圖7 非定常氣動力建模與大振幅試驗結果對比

圖8 非定常氣動力模型預測與大振幅試驗結果對比
綜上,本研究表明,一方面,采用Goman-Khrabrov狀態空間建模方法,可以準確描述典型民機布局飛機極限飛行狀態下動態氣動力的非定常特性,表明該模型適用于運輸機布局飛機的非定常氣動力建模,同時該模型基于流動機理進行建模,物理意義清晰,從而揭示了民機極限飛行狀態下非定常氣動力背后的流動結構演化和流動機理;另一方面,該研究為非定常模型時間常數的辨識提供了一種相對簡便的通過大振幅振蕩試驗數據進行確定的方法。總體而言,利用第3節所述的非線性試驗設計與建模方法可以獲得飛機的主要動態氣動力特征,預示出現非線性氣動力的迎角范圍,在此基礎上,再針對特定的飛機運動過程,進一步開展大振幅或多自由度動態試驗,進行非定常建模,可更準確獲得運輸機特定極限飛行狀態的動態氣動特性。該流程與方法為開展極限飛行狀態動態氣動力試驗設計與建模研究提供了可行的技術途徑。
5 結 論
1) 在飛機超出常規迎角的極限飛行狀態下,特別是在飛機開始失速到初始尾旋階段(如對CRM布局而言,10°<α<35°區域),常規動態氣動力試驗的線性化、定常化假設不成立,需要考慮動態氣動力的非線性與非定常特征。
2) 在動導數試驗設計中,除了減縮頻率,將一個振蕩周期中的最大無因次角速率作為影響因素,形成關于迎角和角速率的非線性動態氣動力模型,可以更好地捕捉飛機關于動穩定性的關鍵特征。
3) 采用Goman-Khrabrov狀態空間建模方法,可以準確描述典型民機布局飛機極限飛行狀態下動態氣動力的非定常特性,表明該模型適用于運輸機布局飛機的非定常建模。同時也揭示了民機極限飛行狀態下非定常氣動力背后的流動結構演化和流動機理。利用大振幅試驗數據進行模型參數辨識,可以得到一種相對簡單的通過動態試驗確定Goman-Khrabrov模型中時間常數的方法。
4) 對于極限飛行狀態的動態氣動力研究,盡管動導數作為線性氣動力參數已經不能用來描述飛機的運動形態,但仍可以預示非線性氣動力的迎角范圍。在此基礎上,再針對特定的飛機運動過程,有針對性地進行大振幅試驗及非定常氣動力建模,可以更準確捕捉特定極限飛行狀態的動態氣動特性。因此,所建立的試驗平臺、方法、數據處理與建模等為民機極限飛行狀態動態氣動力風洞試驗設計與建模研究提供了一個可行的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