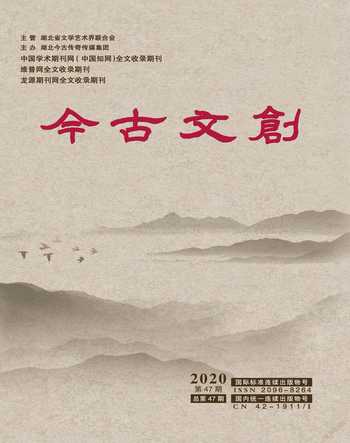鄉土書寫的異途同歸
黎淑怡
【摘要】 賈平凹與路遙同為陜西作家,兩者創作中顯示出一致的黃土文化心態,體現出對時代變革的關切深思。從賈平凹的《浮躁》與路遙《平凡的世界》對比視角出發,兩者雖在內容、手法方面有所差異,但其間深層次的思想表達、精神內涵卻具備一致性。
【關鍵詞】 《浮躁》;《平凡的世界》;話語方式;城鄉交叉地帶敘事;傳統倫理;路遙;賈平凹
【中圖分類號】I207? ? ? ? ? 【文獻標識碼】A? ? ? ? ? 【文章編號】2096-8264(2020)47-0004-02
一、話語方式:傳統啟蒙與積極生存
《浮躁》中,“金狗”是一個鄉村啟蒙者形象,改革中體現出“新”的趨向。首先表現為對傳統的質疑與破體。在“老一輩子的人都在本分地侍弄著幾畝土地,其理想退居于五十年代初”情景下,金狗作為年輕一代,起頭開始在州河重造梭子船搞運輸,“兩岔鎮鄉河運隊”應運而生。對待傳統勢力、官僚主義,他沒有伏低,而是發起猛攻。無論是對鄉村霸主田中正、虛偽奸官田有善,還是官僚的東陽縣書記、專員鞏寶山,都表現出一致的抗爭姿態,最后使其一一落馬。再者,他迸發出的主體意識也具有“國民性”的啟蒙作用。身居記者之位時,他敢于利用權力、承擔職責,真實揭露改革中隱秘的污陋;他參與河運隊的組建、放棄城市生活回鄉興搞機動船,在發揮個人價值的同時,對鄉村其他人具備側面鼓舞性質,吸引他人努力實現自我。[1]這不僅是他剛強的個性使然,更是作為一分子對廣大鄉村、社會責任感的體現,雖然有著與州河一般的“浮躁不安”,但依舊能夠從中獲取深沉力量,走向光明。
《平凡的世界》架構出一派基于人性的生存話語。孫少安成績優異,但因家庭經濟狀況、為弟妹的讀書之路只好放棄學業;與田潤葉本是兩情相悅,但因境況差異無法成眷屬;貸款創業紅火之時又突生變故……孫少平出生“爛包”家庭,困苦校園生活中遇見惺惺相惜的郝紅梅,但“初戀”又敗于物質;異地礦區工作,與田曉霞感情融洽,可女方意外身亡;關懷師娘被誤會,礦難中又毀容……兩兄弟人生的起點都是“苦”,成長歷程也都被“難”包裹,每當出現轉機時,挫折又常突至。李向前、田潤葉等人盡管家境充裕,但仍因情愛之殤嘗遍荊棘,痛苦和無奈也是常伴他們的。無論光景如何,苦惱是普遍存在的,每個人都是平凡的個體,都需要在自己的“平凡世界”中掙扎生存,這是小說中主要人物的共通性,也是對社會人生的寫實性描寫。
與極力凸顯生存艱難的作品不同,路遙呈現出的是積極向上的生存態度。作品中人物盡管受挫,但依舊不服輸地站起,體現出《老人與海》“一個人并不是生來要給打敗的”的主體意志,譜寫了一套積極的“苦難學說”。如孫少平在艱苦環境中的心路:“恰恰相反,他現在倒很‘熱愛’自己的苦難。通過這一段血火般的洗禮,他相信,自己歷經千辛萬苦而釀造出的生活之蜜,肯定比輕而易舉拿來的更有滋味”,給妹妹的信中說:“不要怕苦難!如果能深刻理解苦難,苦難就會給人帶來崇高感。”金波也有類似感悟:“生活不能等待別人來安排,要自己去爭取和奮斗;而不論其結果是喜是悲,你總不枉在這世界上活了一場人。”在路遙看來,苦難不僅是成長必經的、成功必備的,還可建立堅固愛情:“他不僅是和她在肉體上相融在一起,而是整個生命和靈魂都相融在了一起。這就是共同的勞動和共同的苦難所建立起來的偉大的愛。”他打破了苦難敘事中的循環陳規,從人性角度對苦難進行了哲學性深化,苦難表面上是個體發展的絆腳石,實際對人的成長生活具有重要推動力量。他沒有拒絕苦難,也非全然贊美,而是使其不過度悲劇化,彰顯人在苦難中挺背昂首的拼搏氣概。
二、敘事空間:城鄉交叉地帶
路遙認為:“我國當代社會如同北京新建的立體交叉橋,層層疊疊,復雜萬端而在農村和城市的‘交叉地帶’,可以說是立體交叉橋上的立體交叉橋。”“城鄉交叉地帶”作為一個交混的差異空間,聚合了不同生存個體。既有苦謀生計的鄉下人群體,又有體面優渥的城中人階層,落后與先進、卑微與權力在交叉中相互碰撞,是社會變革時期最佳反應體。[2]
《平凡的世界》中,作者對外化世界的設置可見一斑。開篇選取“縣立高中”作敘事地點,“縣”是典型的城鄉中間地帶,學校則完成了兩方人物的交叉。校園中既有家在本城的走讀生,又有所謂的鄉下人,食堂的菜又用甲、乙、丙三個等級將農村青年分出不同光景,這樣的小型社會空間足以映現大環境氛圍。上學期間,孫少平是自卑與自尊的結合體,“雖然他在班上個子最高,但他感覺他比別人都低了一頭”,一邊又為“他現在已經從山鄉圪嶗來到了一個大世界”而欣喜。作為鄉下人,他獲得了在城市中拓寬視野的機會,封閉意識展現出初步開化:“他突然感到,在他們這群山包圍的雙水村外面,有一個遼闊的大世界。”環境也給予了他尋求精神讀物的能力,加注對未來的憧憬。其內心的搖擺感受,對自身環境的認知抑或對廣闊世界的渴望,相較處于單一群體空間來說,顯然更為深刻。
《浮躁》中,“金狗”的內心自成一方“城鄉交叉地帶”。作者序言中勾畫了強烈的州河形象,直言是“全中國的最浮躁不安的河”。金狗身世離奇,母親州河淘米溺死,他卻在米篩中奇跡存活,承繼了州河的“浮躁”、活力與力量。身為畫匠兒子,地道的農村人,參軍離鄉數年后復員回鄉;波折中成了州城報社記者,最終卻又返回鄉村。呈現出“離鄉——還鄉”的搖擺行為模式,根源即為內心“城鄉交叉地帶”的游走。既向往城市的繁華光景,又在虛偽的打擊中體現出自由純樸的鄉戀情結,對城市與鄉村交雜的傾慕、厭惡,使他的肉體與精神在城鄉空間輾轉,難以安定,因而長久浮躁。他一邊強烈愛著“菩薩”小水,一邊又生發“時間長了,他倒十分喜歡甚至是愛慕起石華來了”的情感傾向。小水是“土”的鄉村代表,石華為“洋”的城市風貌,其情愛也在城鄉女性之間有過徘徊。
三、思想維度:集體倫理觀
兩書都從儒家文化以集體為核心的“和”出發,主要人物形象展現出一致的“重集體”傾向。《平凡的世界》中,孫家兩兄弟等人都具備基本的道德倫理意識,這也是路遙本人汲取儒家傳統中人性道德標準的體現。[3]孫少安六歲開始砍柴干農活,十三歲讓弟、妹上學,高小后不繼續學業:“我回來,咱們兩個人勞動,一定要把少平和蘭香的書供成。只要他兩個有本事,能考到哪里,咱們就把他們供到哪里。哪怕他們出國留洋,咱們也掙命供他們吧!他們念成了,和我念成一樣。”個體、集體利益在他的思想中是同根同源的,集體的勝利便是個人的勝利。無論是為姐夫王滿銀打點,還是創業謀富,本質都是為了家庭。作為單薄的個體,他也有過迷茫痛苦:“一切都太苦了,太沉重了,他簡直不能再承受生活如此的重壓”,但最后又是被“雙水村星星點點的燈火”,被“親愛的家”“親人們的臉龐”,被父親的相抱痛哭與傾訴衷腸治愈。他為集體愁苦,但更為其奮力前進。
孫少平亦是。從他對田潤葉給的五十斤糧票處理方式看“另外的十五斤白面他舍不得吃,準備明天帶回家去,讓老祖母和兩個小外甥吃”,“至于那五斤‘歐洲’票,他是留著等哥哥來一起吃的”能夠無時無刻想及家人,是融于集體的體現。首次領到礦區工資后,他除伙食、鋪蓋費外,將剩下的五十元悉數寄給父親;自己并不豐裕,仍堅持每月寄給妹妹十塊錢。“孫少平每天竭盡全力,首先是為了賺回那兩塊五毛錢。他要用這錢來維持一個漂泊者的起碼生活。更重要的是,他要用這錢幫助年邁的老人和供養妹妹上學。”他與少安一樣,集體的考量始終高于自己,具備濃厚的倫理觀念。
《浮躁》中,金狗等人的集體觀念更多體現在他與小水、大空形成的無血緣關系的“雜姓”家庭中。[4]小水拒絕鞏家子弟婚事,嫁入孫家卻遭急喪,后被鞏毛毛家恥笑、張揚是非;田中正侄女英英充當了她與金狗愛情的破壞者,而田中正本人對她意圖不軌。大空向鄉黨委書記告發田中正的通奸丑事,憑“我愿意去那是我的人情,我不愿意去這是我的本分”的說辭拒絕幫田中正蓋房,但仍未扳倒田中正,反在其另升高枝下被迫漂泊;為小水報輕薄之仇時,他本著正義教訓田中正,卻因公安局“破壞改革,毆打傷害堅持改革的領導干部”之由含冤入獄。金狗更是長期以來作為對抗者,與傳統宗法勢力斗爭。從對外關系看,它們組成的集體是田、鞏兩個傳統家族權力體系的對立面,代表長久受壓迫、聚力反擊的平民群體。
著眼內部,金狗與小水存在一段愛情外的親緣關系:“小水爹出生的時候,正在‘犯月’,小水的奶讓人卜卦,說是要一生平安,必認干親……金狗爹就一生做了小水爹的干爹。”兩人前期未生情愫時,融洽相待都是出于認定的親緣。他們與大空之間也同樣具備這種家庭式溫情,大空為小水報仇而入獄;金狗奮力解救獄中的大空;小水為兩人在磚墻下嘶唱行船號子……三者體現出的關切與互助,儼然超越普通朋友,不是親人卻勝似親人。無論是由于一致對外體現出的同一立場,還是個體之間蘊含的脈脈溫情,都是傳統倫理中集體概念的外化。
參考文獻:
[1]董文華.熔惡的真火 淘金的圣水——試析《浮躁》的社會意義[J].新疆石油教育學院學報,1988,(01):128-131.
[2]段建軍.路遙:在交叉地帶探索人生的意義[J].中國文學批評,2020,(01):11-17+157.
[3]趙學勇.“老土地”的當代境遇及審美呈現——路遙與中國傳統文化[J].陜西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1,40(03):105-115.
[4]劉一秀,孟繁華.主體立場:現代理性與傳統倫理的糾結——賈平凹《浮躁》新論[J].安徽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1,35(03):66-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