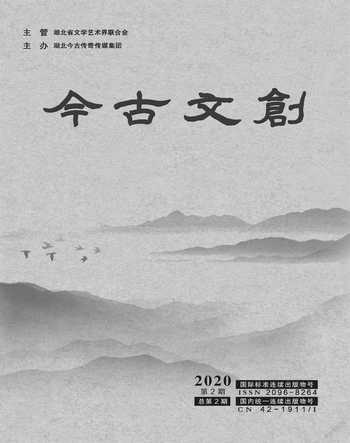《論曲絕句》評《鳴鳳記》之考辨
張宇凡
摘? 要: 凌廷堪《論曲絕句》認為《鳴鳳記》過于拘泥于歷史真實,有悖于戲曲本真。通過將《鳴鳳記》中所涉史實與史書進行對比,可以發現無論是在單個人物形象的塑造、具體情節的安排還是全戲時間脈絡的設置上,都與正史有著較大差異,可以看出《鳴鳳記》的作者并非一味求真。在對《鳴鳳記》的史傳筆法進行分析之后,不難發現該劇作者不但沒有事必求真,拘于史實,還在有限的空間內對歷史進行了大量地加工。結合凌廷堪戲曲理論著作中流露出的崇元曲、賤傳奇的復古傾向,參考他對其他戲曲的評價,認為凌廷堪對于《鳴鳳記》的苛責是有失公允的。
關鍵詞: 《鳴鳳記》;凌廷堪;《論曲絕句》
中圖分類號: I206? ? ? ?文獻標識碼: A? ? ? ?文章編號: 2096-8264(2020)02-0018-04
清人凌廷堪在《論曲絕句》中對于如何處理戲曲歷史真實與歷史真實的關系有所涉及,所謂“若使硁硁征史傳,元人格律逐飛蓬”。
他認為對待戲曲首先要“明其為戲”,不必征之于史書,他明確指出創作者不應將戲曲與史實的“無隙可指”作為單一的評判標準。
如章學誠《丙辰札記》所說:“全實則死,全虛則誕。”歷代小說、戲曲中最具生命力的往往是能夠實現藝術與現實完美融合的作品。
縱觀凌廷堪三十二首論曲絕句可知,其曲學觀點較為開放,確有可取之處。他在“明其為戲”的基礎上,對元明清三代戲曲作品廣泛品評,不乏精當之語,卻也有片面之處。
其中第十七首:“弇州碧管傳《鳴鳳》,少白烏絲述《浣紗》。事必求真文必麗,誤將剪彩當春花。”認為《鳴鳳記》拘泥歷史真實,有悖戲曲本真。
通過將《鳴鳳記》中所涉史實與史書進行比對,可以發現無論是在單個人物形象的塑造、具體情節的安排還是全戲時間脈絡的設置上,都與正史有著很大差異,可以看出《鳴鳳記》的作者并非一味求真。
探究這些差異背后的原因,對于更好地理解《鳴鳳記》的創作思路,正確看待凌廷堪《論曲絕句》及其曲學觀念大有裨益。
一、《鳴鳳記》之史實考辨
郭英德認為《鳴鳳記》:“以千鈞筆力塑造了一批前仆后繼與嚴氏集團進行殊死斗爭的忠臣義士。”揭示了全劇的故事主線與主要人物。與嚴黨的斗爭貫穿了嘉靖朝后期近二十年,所涉人物駁雜,《鳴鳳記》中的主要人物就有“雙忠八義”、嚴氏父子及其犬牙十數人等。受篇幅所限,難以對其人物、史實一一梳理。下文將從劇中關鍵人物與其歷史原型的比較,戲劇情節與史傳記載的差異以及時間脈絡上的虛構嫁接三個方面具體論述。
夏言作為《鳴鳳記》中“雙忠”之一,自《夏公命將》出場以來便是一副心憂國事,一心只為收復河套失地的賢相做派,第六出《二相爭朝》上場時更是將“志存報國,力恢河套”的唱詞掛在嘴上,在與嚴嵩爭辯的過程中始終表現得剛正不阿,可謂全忠全節的治世能臣,與嚴嵩一味迎合君王的奸相嘴臉形成鮮明對比。據《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南宮奏稿”條載可知:
(言)后以主復河套,為嚴嵩所構,坐與曾銑交關,棄市。隆慶初,追復原官,謚文愍。事跡具《明史》本傳。言初以才器受知世宗,而柄用之后,志驕氣溢,傲愎自專,卒以致敗,其事業殊無可稱。
夏言因主張收復河套一事為嚴嵩所構陷,其人恃寵而驕,剛愎自用,治國更是“殊無可稱”。其處世方式與宦官“一旦擢高官,恃君恩獨掌朝權,況他性存剛愎把汝被土視塵看”的背后攻訐一致,《明史》不僅記載夏言“久貴用事,家富厚,服用豪奢”,還認為夏言力主收復河套有著“思建立不世之功”的政治目的。清人昭梿《嘯亭雜錄》對于《鳴鳳記》中夏言的形象有較為深刻的判斷:
桂洲居相位時,亦復貪婪倨傲,原非賢佐。不過為分宜所陷,死非其罪,人多憫之。今《鳴鳳記》演《河套》劇,居然黃發老臣,可與葛氏、姚、宋并列者,亦未免過褒也。
可見與凌廷堪同時的昭梿已經意識到《鳴鳳記》的創作者在塑造人物形象時并非還原歷史,而是根據需要對人物進行了藝術加工,使人物更具典型性。如果說劇中的夏言比史書上的更加光彩照人是因為傳奇創作者受個人認知所限,無意為之。那么《鳴鳳記》中另一重要角色郭希顏的形象與史實出入之大,就更能體現出作者的主觀創造。
郭希顏是劇中關鍵角色鄒應龍、林潤之師,是二人的精神向導。他不僅學識出眾,“經學忝魁江右”,還不顧自身仕途搭救被陷害的易洪器,上疏彈劾嚴嵩,最終死于嚴黨之手。史書中的郭希顏卻遠不如角色光彩。《明史》并無郭希顏本傳,他被記入史書與兩件事有關:一是嘉靖二十三年四月上疏請立四親廟,一是嘉靖三十九年上《安儲疏》觸怒嘉靖。二者都是嘉靖朝重大的政治風波,史書俱載,茲不贅述。《曲海總目提要》對郭希顏上疏請立四親廟一事有載:
九廟災,廷臣議廟制,請復同堂異室之舊。希顏見張璁、夏言輩以議禮驟貴,心揣帝意,欲崇私親而薄孝、武二帝,乃獨請建四廟祀高、曾、祖、考,斥孝、武二宗別祀。疏出,舉朝大駭。禮部尚書張璧等斥希顏悖戾,議終不用。希顏由是得罪清議。
“議禮”初期張璁、夏言因支持嘉靖,深得皇帝信任,得以晉升。郭希顏上疏的目的也是希望憑借恭迎上意獲得升遷。這一投機行為雖換來嘉靖短暫的青睞,卻也得罪了言官群體以致罷官,《鳴鳳記》中郭希顏則是因彈劾嚴嵩而罷官。至于其死因更是無中生有,嘉靖三十九年,閑居在家的郭希顏上《安儲疏》,希望嘉靖妥善處理儲君事宜。此舉并非忠臣直諫,而是又一次投機。《曲海總目提要》評論此事:“無故上書,用自取死。非由嵩作,傳奇中未免惡皆歸焉。”即便隆慶皇帝即位后為郭希顏平反,后人對他評價也并未轉變。沈德符《萬歷野獲編》“恤贈諫官之謬”條評價郭希顏:“隆慶登極恩詔,恤錄故臣,以建言被僇為第一等,以故中允郭希顏遂與員外楊繼盛并列。既而郭贈翰林光學,以詞林故事也,而贊善羅洪先、修撰楊慎止得光祿少卿。希顏何如人,乃出羅楊上耶?”
可見真實的郭希顏是一個為人所不恥的投機者。《鳴鳳記》的作者大抵是因為隆慶即位后的平反將郭希顏與楊繼盛并列,由此認為郭希顏是因諫言獲罪的忠臣。創作于萬歷初年的《鳴鳳記》,在處理郭希顏這一人物時不僅沒有“事必求真”,反而與史實相去甚遠。
除人物與歷史原型差異較大外,《鳴鳳記》在具體情節的設置上也并未處處與史實相合。從第三十六出鄒應龍上疏彈劾嚴嵩前的自白:
下官監察御史鄒應龍是也。巡視邊衛,復命還朝,可耐嚴嵩父子濁亂朝政,殺戮忠良,且聞他私自票本,口傳圣旨,為此諫官多受其害。今日下官將他罪惡,一一條陳。必要痛哭君前,感動天聽。倘有不虞,何惜一死。
可知鄒應龍上疏之時,嚴黨氣焰滔天,他是抱著必死之心的。而據《明史》記載,鄒應龍上疏之時嚴嵩圣眷已弱:“嚴嵩擅政久,廷臣攻之者輒得禍,相戒莫敢言。而應龍知帝眷已潛移,其子世蕃益貪縱,可攻而去也。”
鄒應龍是在看清政治形勢之后,謹慎挑選了嚴世蕃作為其彈劾的對象。且鄒應龍在嘉靖帝下手札“嵩已退,其子已伏辜,敢再言者,當并應龍斬之”之后深感自危,并不如《鳴鳳記》中這般一往無前。《鳴鳳記》中的鄒應龍上疏的經過明顯經過了作者的加工,用以刻畫其不畏強權的忠臣形象。
學界對《鳴鳳記》作者及其創作年代未有定論,故而難以判斷《鳴鳳記》的時間線索是否是作者有意為之。然而劇中存在若干細節之處在時間上與歷史不符卻是不能忽略的。如第四十一出最末特意交代了“皇明圣治稱嘉靖,遇明良喜起同聲,始信朝陽有鳳鳴”,點明是嘉靖帝頒布了為忠臣平反的詔書。
然而詔書中“故相夏言追贈紫金光祿大夫,仍賜遺腹子襲蔭。曾銑、郭希顏并贈榮祿大夫。楊繼盛謚忠愍太中大夫,妻劉氏贈節義淑人”卻發生在隆慶年間。郭希顏、楊繼盛其事見前文所引沈德符《萬歷野獲編》“恤贈諫官之謬”條。至于夏言與曾銑《明史》均有詳述。《明史·夏言傳》載:“隆慶初,其家上書白冤狀,詔復其官,賜祭葬,謚文愍。”
《明史·曾銑傳》載:“隆慶初,給事中辛自修、御史王好問訟銑志在立功,身罹重辟,識與不識,痛悼至今。詔贈兵部尚書,謚襄愍。萬歷中,從御史周磐請,建祠陜西。”
作者將發生在隆慶、萬歷朝的事情移植到嘉靖朝,既顧全了嘉靖帝的形象,也符合《鳴鳳記》懲惡揚善的道德導向,可見作者的創作并非以史為準,而是進行了充分的藝術加工,使人物與史實為劇作的感染力服務。
二、《鳴鳳記》之史傳筆法
凌廷堪認為《鳴鳳記》是“事必求真”之作,與劇作本身的題材及其運用的史傳筆法也有一定的關系。鄭振鐸說:“傳奇寫慣了的是兒女英雄,悲歡離合,至于用來寫國家大事、政治消息,則《鳴鳳》首為嚆矢。”
作為時事劇發軔的《鳴鳳記》相較于其他傳奇故事,更加注重所述事件本身的傳播,獨特的創作目的使得作者必須尊重基本史實。相較于凌廷堪《論曲絕句》第十二、十五首提及的于史無憑的元雜劇《王粲登樓》《梅香》《包待制智斬魯齋郎》,《鳴鳳記》本身就帶有更強的真實性,所謂的“事必求真”是其題材決定的。
除此之外,《鳴鳳記》借鑒史傳文學的筆法,使得作品的觀感與史書相近。其中較常出現的是從《史記》中借鑒而來的互見法以及對于《左傳》敘事藝術的學習。
《鳴鳳記》展現的是嘉靖朝忠臣志士反抗嚴黨的全過程,所涉人物眾多,情節線索復雜,難以單獨呈現。因此在交代很多角色的處境時,往往采用互見法,例如作者對于郭希顏事跡的處理,并沒有單獨篇幅的呈現,而是將郭希顏融入到描寫其他人物的場景中去,第二出《鄒林游學》、第二十三出《拜謁忠靈》、第三十二出《易生避難》主要描寫的對象是鄒應龍、林潤、易弘器,郭希顏起到的只是連接三人行跡的作用。在交代郭希顏全劇最重要活動“上本諍諫”的時,也只是在對話中一語帶過。整出戲主要還是講如何搭救易弘器,然而郭希顏做出的重大決定,以及他其后命運走向都在三言兩語之中交代清楚。
錢鐘書曾說:“《左傳》記言,而實乃擬言、代言,謂是后世小說、院本中對話、賓白之椎輪草創末蘧過也。”《左傳》在敘事寫人上往往使用詳盡、生動的細節,為事件增加大量的情節,即小說化的屬辭比事。如《左傳·襄公二十五年》崔杼弒君一事,《春秋》只有“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弒其君光”一句,《左傳》則增加了大量的情節,將弒君之事刻畫得極其生動。《鳴鳳記》也借鑒了這種手法。第五出楊繼盛拜見趙文華時,有一段關于茶的對話尤為精彩:
【喫茶介、丑】楊先生,這茶是嚴東樓見惠的,何如?【生】茶便好,只是不香。【丑】香便不香,到有滋味。【生】恐怕這滋味不久遠。
《曲海總目提要》評價吃茶片段:“此劇所演多系實跡,繼盛晤、趙文華借吃茶諷切,乃是增飾未嘗有此事。”雖無此事發生,但從楊、趙二人因吃茶這一小事所表現出的不同態度,觀眾可以直觀地感受到二人對于嚴黨態度的差異,忠奸自然相形。
同樣的手法在第十四出中也有運用,楊繼盛在上疏前遇到祖先顯靈,這一情節明顯是作者編造附會而成,且不說這一情節所蘊含的迷信色彩,果有其事,也并非發生在楊繼盛身上。《明史·蔣欽傳》載:“方欽屬草時,燈下微聞鬼聲。欽念疏上且掇奇禍,此殆先人之靈欲吾寢此奏耳。因整衣冠立曰:‘果先人,何厲聲以告。’言未已,聲出壁間,益悽愴。欽嘆曰:‘業已委身,義不得顧私,使緘默負國為先人羞,不孝孰甚!’復坐,奮筆曰:‘死即死,此稿不可易也!’聲遂止。”顯然,作者是將蔣欽之事嫁接到楊繼盛身上,以凸顯楊繼盛的義無反顧,劇作的感染力更強。
三、凌廷堪之復古主張
明代戲曲理論家王驥德認為:“劇戲之道,出之貴實,用之貴虛。”強調創作既要忠于史實,也要充分發揮藝術創作。正如王驥德所提倡的,《鳴鳳記》在創作中并非以史為綱,而是“有意駕虛”,對歷史人物進行調整,并借助史傳筆法豐富劇作細節,使觀眾聞之有身臨其境之感。然凌廷堪仍認為《鳴鳳記》是“事必求真”,對其提出批評。綜合其作《論詞絕句》三十二首及《與程時齋論曲書》所流露出的“宗元”傾向,不難看出凌廷堪戲曲史觀中的復古意識。
凌廷堪在《論曲絕句》中多次贊揚元雜劇和北曲,而對明朝傳奇作品評價不高。絕句第二十六首:“前腔原不比幺篇,南北誰教一樣傳。若把笙簧較弦索,東嘉詞好竟徒然。”認為《琵琶記》也無法與北曲中的末流相比。這種傾向在《與程時齋論曲書》中體現地更加明顯:
自明以來,家操楚調,戶擅吳歈,南曲浸盛,而北曲微矣。雖然,北曲以微而存,南曲以盛而亡……若夫南曲之多,不可勝計,握管者類皆文辭之士……
于是悍然下筆,漫然成篇,或詡秾艷,或矜考據,謂之為詩也可,謂之為詞亦可,即謂之為文亦無不可,獨謂之為曲則不可。前明一代,僅存餼羊者,周憲王、陳秋碧及吾家初成數公耳。他將元曲是為戲曲的典范,南戲、傳奇這些戲曲體式體格代降,認為元曲雖面臨著式微的現狀卻足以生存,而南戲、傳奇的興盛卻會走向消亡。同時他還認為同代的戲曲創作已經“不可救藥”,并為其提供了取法元人的解決辦法。
凌廷堪的戲曲批評指向現實創作。他想要糾正戲曲創作的風氣,在品評中難免會矯枉過正。凌廷堪推崇元曲,加之對傳奇抱有成見,在品評作品時自然就有失公允。他甚至認為《牡丹亭》遠不如湯顯祖為數不多的北曲。因此《論曲絕句》中對《鳴鳳記》的品評失當就不難理解了。
四、結語
詩分唐宋,世人獨尊唐詩,而少識宋詩之妙。凌廷堪《論曲絕句》苛責《鳴鳳記》背離戲曲文體,正是因其崇元曲,貶傳奇的觀念太過強烈。作為時事劇發軔的《鳴鳳記》在結構和具體情節的設置上確有缺陷,并非一流作品。但整體來看,作者有意凸顯史實本身,在尊重基本史實的前提下,充分發揮自己的藝術創造力,并非考據史料所成。
凌廷堪不滿當時戲曲創作中矜于考據的風氣,未能認識到《鳴鳳記》一劇對戲曲題材的開拓,批評其“事必求真”是有失公允的。
參考文獻:
[1](清)凌廷堪.凌廷堪全集第四冊[M].合肥:黃山書社,2009.
[2](清)凌廷堪.校禮堂文集卷二十二[M].北京:中華書局,1998.
[3](清)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上)[M].北京:中華書局,1965.
[4](明)毛晉.六十種曲第二冊.鳴鳳記[M].北京:中華書局,1958.
[5](清)張廷玉等.明史卷一九六[M].北京:中華書局,1974.
[6](清)昭梿.嘯亭雜錄[M].北京:中華書局,1980.
[7](明)沈德符.萬歷野獲編卷十三[M].北京:中華書局,1959.
[8](明)王驥德.曲律卷三.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四)[M].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50.
[9]郭英德.明清傳奇史[M].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
[10]鄭振鐸.插圖本中國文學史(下冊)[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11]許大年編.曲海總目提要(上)卷五[M].天津市古籍書店,1992.
[12]張軍德.《鳴鳳記》創作年代初探[J].文學遺產,1986,(06):50-51.
[13]伏滌修.《鳴鳳記》所涉史實問題考辨[J].南京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02):130-136.
[14]駱兵.論凌廷堪的戲曲理論[J].藝術百家,2007,(03):28-31.
[15]徐海梅.論清代曲家凌廷堪的戲曲思想[J].齊魯學刊,2016,(04):123-127.
[16]相曉燕.論清中葉揚州曲家群的“崇元”傾向[J].戲劇藝術,2015,(01):84-91.
[17]郭英德.明清之際時事劇的思想藝術特色[J].中州學刊,1985,(02):79-83+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