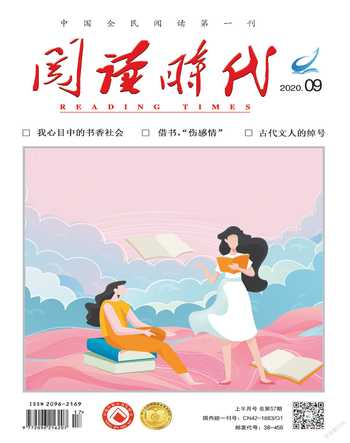這就是作家阿城
張群
01
阿城是誰?
阿城的身份不少,會的事情很多——是編劇,是電影美術指導,也做過電影評委,還會木工,能做木匠。
但阿城成名卻是因為文學。
1984年,鐘阿城的短篇小說《棋王》首發在《上海文學》,這一部14000多字的小說引爆全國,接下來《樹王》《孩子王》,生生震動中國文壇,一時洛陽紙貴,鐘阿城開始變得炙手可熱。全國各地的編輯紛至沓來,紛紛向他約稿。有時一天要來好幾撥,有時一撥要來好幾次。
那段時間的鐘阿城約稿太多,甚至沒有時間做飯。每次吃飯都是吃方便快捷的面條。他更是迷戀上了香煙。一個大陶瓷碟做成的煙灰缸中總是滿滿的煙頭,以致于有朋友看不過去了,告誡他不要抽太多的香煙,對身體不好。但是一貫對朋友言聽計從的鐘阿城,這一次卻沒有聽朋友的忠告,依舊一只手寫著約好的稿件,一只手夾著香煙,樂此不疲。
多年之后有人請他談創作《棋王》的經過。他平靜地說,其實那只是一篇隨意的作品,自己根本沒有耗費過多的精力,只是花費了三到四天就完成了創作,自己也沒有想到會引起轟動。而據后來鐘阿城的妻子回憶,《棋王》的創作阿城甚至還沒有花費到四天的時間。
后來得了諾獎的莫言,那時還在讀書,眼里沒幾個看得起的,但是阿城把他徹底征服:那時他在我的心目中毫無疑問是個巨大的偶像,想象中他應該穿著長袍馬褂,手里提著一柄麈尾,披散著頭發,用朱砂點了唇和額,一身的仙風道骨,微微透出幾分妖氣。他是個想得明白也活得明白的人,好話與壞話對他都不會起什么反應,尤其是我這種糊涂人的贊美。當時文學系的學生很想請他來講課,系里的干事說請了,但請不動。我心中暗想:高人如果一請就來,還算什么高人?
02
阿城的人生選擇似乎總是出人意料。
第一條,就是當紅之際,飄然歸隱美國。
80年代成了炙手可熱的紅人,評論界、讀者好不熱鬧。他自己呢,卻一點不貪戀名利,悠然飄往美國。
原因其實非常簡單。阿城自己事后說,不過是因為當時在美國更容易找工作,比較好養活自己。
安身立命,阿城說安身在先。
結束十一年知青生活,回城之后,好多知青發現城市容不下他們。十多年不在這個城市,沒有人脈,哪里找得到工作?三十多歲的人,什么都沒有,在父母家搭個行軍床,每月還要父母給一兩塊錢零花。不能自立,在這個城市生活的恥辱感特別強。阿城到美國去了,一看,唉,這地方好,打工不必認識誰,好活。于是就留下了。

到美國做的是什么工作呢?打短工,給有錢人家遛狗、刷墻……因為不需要用腦,回家之后留著腦子繼續“摸摸想想”。哲學家維特根斯坦也是如此。
遠離華語寫作圈的阿城,不受諾獎、國內評論界、文學圈的裹挾,沒有為了養活自己,努力寫出暢銷書的壓力。這種超脫使得他的語言、思想都抱持著自己獨有的風格。你一看就知道,這是阿城的東西。
03
至今提起阿城,大家知道的多還是他的小說。阿城自己卻不怎么看中這個。他覺得小說就是講故事,人人都能講,只是講得好不好的問題。所以,阿城心里從來沒有把自己當成過作家,而是稱自己“失足文學青年”,更沒想靠小說揚名立萬。阿城寫小說,大概是偶然來了閑情雅致,才會把他腦子里的故事寫出來。
馮唐一直嚷嚷著要用文字打敗時間;阿城卻可以因為自己的電腦壞了,說不寫就不寫了,這得看得多開啊。
可以說,這些年阿城筆頭真正出來的,不及他腦袋里閃過靈光的十分之一。他也似乎根本不珍惜自己的才力,總是將靈機妙語就那么隨意講出。
王朔、陳丹青、朱天文心心念念,口口稱贊的莫不是:聽阿城聊天,那真是一種天大的享受!
王朔講過一個故事:在美國的時候,大家經常聚會,阿城叼著個煙斗,即使低著頭不說話,也總是人群的中心。等到他一開始講話,那個精彩,同去的女生笑得神魂顛倒,幾個星期還心心念念。而且阿城可以十幾年夜夜講,絲毫不帶重樣。
04
日本作家村上春樹自29歲決定寫小說起,他的一切就為了寫作而存在。他跑步、戒煙、每天早上五點起床寫作,雷打不動。陀螺一樣地一直轉了幾十年,一直到現在。阿城的活法和村上不太一樣,他更重視活著的這個過程,寫作只占據了一小部分。他做自己喜歡做的事,織布、種植、木匠、攝影,都達到了可以養活自己的地步。平時也研究青銅紋理、東北薩滿、大麻與巫術、龐德和艾略特。對物質這方面也看得很淡,基本都是夠用就行:“我的生活指標要求也不高,我也不需要有個房子,或者有個多好的車,跟我在鄉下插隊的生活比,這已經是非常好的生活了。”
王朔的一句話一針見血:“這個人對活著比對寫文章重視。”
05
許多和阿城接觸的人說,阿城最吸引人的除了博學、睿智,還有他的心態——從他的言談中真的可以感受到一種叫“Inner Peace”的東西。
《八十年代訪談錄》里,查建英問阿城出國后有沒有經歷過這樣一個階段——國內別人都知道你,你很出名了,國外一個人都不認識你。查建英問的是得失心。
阿城說,不啊,我還高興,因為常識還在。到了美國才知道,邊緣是正常的,沒人理你是正常的,大家都尊重對方的隱私,這是個常識。所以在外國,我反而心里踏實了。他說自己的生活軌跡跟大部分中國人一樣:找工作,結婚,生子。這樣的經歷不超出任何中國人的想象。
“大家怎么活過,我就怎么活過。大家怎么活著,我也怎么活著。有一點不同的是,我寫些字,投到能鉛印出來的地方,換一些錢來貼補家用。但這與一個外出打零工的木匠一樣,也是手藝人。因此,我與大家一樣,沒有什么不同。”
有記者采訪他,問了這個問題:即使您過去一度因為家庭背景無法考進大學,等到考試恢復了亦不動心,仍舊選擇過著“閑時寫寫畫畫”的日子,我們很好奇您的生命態度或價值觀是什么?
阿城回答說:“我過日子的方式是過程形態而不是目的形態──目的形態常常會造成所謂的死不瞑目。其實你看得多了,看事情就比較寬、不會那么絕對,你也就不會變成任何觀念的人質。”“我知道什么是底線。無非是,如果現在天下又亂了,我又回去種地去,不就是這樣嗎?沒有什么可怕的。而我是有受得了的苦,有享得了的福。”
06
他看得就是這么通透。
阿城說:“知識結構決定你。”他練的是童子功,從琉璃廠的舊書店就開始了。
怎么才能達到這樣的通透境界呢?我們現在開始還有可能嗎?阿城的建議是“素讀”,就是不帶你的意見去讀。就是認真聽別人把話說完了,理解了其中的意思,之后再去批判。
我們現在都習慣批判性地聽別人的話。別人說了沒兩句,你就說:“哎,你這個說的不對。”急于表達,這樣并不利于彼此的理解與溝通。交流的前提是必須知道別人完整的東西,否則我們學到的東西就會少。
讀阿城真正的意義,大概就是能開闊你我的眼界,讓人知道文學、藝術這些東西跟人生之間的關系,它是可以依賴的。
如果能像阿城一樣“游于藝”,你可能會把人生過得更好。
責編:何建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