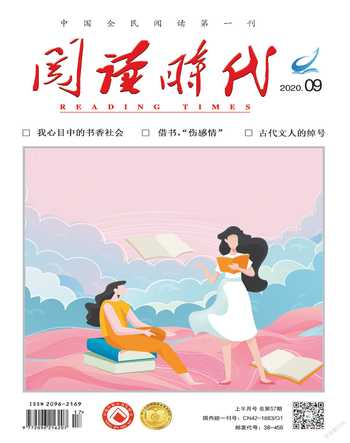借書,“傷感情”
【德】施皮南
被借出的書
斗膽說盡人皆知的大實話:一個人要想看書的話,不一定非得去買。從某種意義上講,書籍甚至算得上是一種公共品。這里指的不單是圖書館里的藏書,就算是私人收藏的書籍,同樣也具有某種獨有的特質。當一個人張口向朋友借用餐具或割草機之前,他八成已向對方借過十來本書(用于收藏的古董書自然另當別論)。雖然都是私有物品,但和書籍相比,餐具和割草機顯然要更“私人”一些。更何況,因為書里的字都是事先印好的,所以對書的主人而言,真正屬于他的并不是書里的文字,而不過是那一沓紙。再說了,如果一個人的選書品位能夠以如此方式得到賞識,他該感到受寵若驚才對!
人們在借用這些物品時,通常都會講好送還的時間。書卻不一樣,它可以延遲,也可以中斷;它可能耗時漫長,也有可能永遠都不會開始。所以,出借人總是這樣說:看完再還,不急!
這話自然是出自好意。可是,它卻讓書的命運從此踏上了自己的軌道。如果借書人患有拖延癥,這本書就會變成壓在他心中的重負。時鐘開始嘀嗒作響:哎,該把書還回去啦!但從另一方面講,借書人也許并不愿意逼自己太甚,更不愿被別人催促不休,而且說到底,不過就是一本書嘛,還能怎樣?可是,如果不看就把書還回去,也終究不是辦法。一來是因為借書人可能不等人問,就不自覺地說了實話;二來如果這樣做,會讓借書人顯得很小氣。其實這時候,出借人自己也已陷入了兩難。書遲遲不還或許早讓他怒火中燒,可他卻刻意回避不問,以免讓自己看上去像是個小氣鬼。而且他畢竟親口說過:不急!
于是,許多借出去的書就這樣經年累月,守候在等待閱讀的中間地帶。還沒看,不過,馬上;還沒還,等看完就還,一定!對借出去的書來說,最壞的情況是,借書人壓根不準備再讀它。而且為了不讓自己太糾結,他刻意把書塞到了一個視線不及的角落。也許有一天,這些借來的書會被裝進搬家用的紙箱,隨其他家當一起離開這個城市,這個國家,這片大陸,最后被借書人昧著良心或出于大意,歸入了自家的收藏。
再往后,當出借人和借書人都已相繼故去,這本借出去的書卻依然完好。可是,只有當它有一天在舊貨市場上被賣掉——哪怕標價只有一角錢——它才能有機會洗刷身上的污點和恥辱。如今,它終于又有希望被人閱讀啦!
直到有人把它借走。
被偷竊的書
想當年,在我剛進大學念書時,從書店里偷書還是一種富有個性的叛逆行為。在一些圈子里,文字常常被看作是公共品。在這些人看來,文字在現實生活中之所以總是以商品和私有物——書籍的形式出現,是資本主義制度為達到統治目的所采取的卑劣伎倆。面對這種伎倆,只能以不順從的姿態作為回應。
那時候,我只偷過一本書。一場白費力氣的行為表演,一次青春期后遺癥式的愚蠢冒險。那本書是克勞斯·曼的《梅菲斯特升官記》。在被禁多年之后,它又重新出版上市,盡管圍繞書的官司還沒有了結。我覺得,對這樣一本書下手實在再合適不過,況且它就擺在書店靠近門口的位置,高高地堆成一摞。
這次偷書行動雖然得了手,可我的內心卻為此糾結不已。我草草讀完了書,一心指望能通過閱讀來彌補之前的過失。這當然是無稽之談。于是我只好又花錢買了一本,還讓店員開了發票,然后在離開書店時,悄悄把書放在了門口依然高聳的書堆上。一場行為主義風格的資本主義大批判,就這樣狼狽地收了場。
可是到后來,在迷上收藏的幾年里,我卻屢屢陷入一種境地,讓我不得不認真去思考偷書的問題。在我眼里,有些書和我的書架還有架上的藏書是那么相配(簡直是天作之合),以致讓我覺得,為了得到它們,就算做下犯法的事也是情有可原的。現有的物權關系確實很不公平,不過這并非是對政治和社會全面思考后的認識,而是在我看來,我對這些書籍的權利訴求,要比舊書店或公共圖書館來得更迫切,更有根有據。
偷書賊是一類既有魅力又充滿矛盾的人物。從一方面講,他擅自竊取他人之物,這著實不妥,要是聽任其發展那還了得?但另一方面,他是竊賊中的文化人,是精神世界里的羅賓漢。或許我們可以指望他們,為書籍的世界打造全新的物權關系,以取代單純的商品所有權。最好的辦法是按照讀者的真實需求和內在素質來分配書籍,具體該怎樣操作,則另當別論。
自從投身寫作之后,我對偷書賊的浪漫幻想也漸漸消散。誰敢偷我的書,就是不尊重我的勞動,是貪圖私利而害我吃虧。人類經過了幾百年的時間,才終于建立起一套文化經濟體制,好讓人們至少有機會依靠寫作來養活自己。假如沒有“知識產權”的理念和司法實踐,這條路就會被徹底堵死,所以務必要想辦法保住它。當然,要做到這一點,首先要抵制“知識產權”盜竊,無論其存在的形式是哪一種。
其實,書籍本身就是一種防盜裝置。它給文字套上了權威和官方化的外殼,即使不能徹底杜絕偷盜和剽竊,至少也能讓偷竊更容易辨認。我曾在本書開篇中寫到:書籍是文字世界里的房子。我想在這里再補充一句:書籍是文字的房子,也是文字的身份證。它標明了文字的所有權關系,也為文字的原創性提供了擔保。
盡管有各種法律條款的保護,但偷盜文字的案件迄今仍時有發生。最受爭議的一起大概要數1970年的柏林大學生盜版案。這些學生私自印刷了阿爾諾·施密特的小說《紙片的夢》,并拿到市場上售賣。當時的正版書售價是三百馬克,而盜版書的標價卻只有一百馬克。與那個時代的常見情況一樣,這一行為也被看作是一項有利于文字傳播的公益活動。但實際上,它和“公益”毫不沾邊,因為它讓一位窮作家的收入嚴重受損。每一本盜版書的問世,都讓正版書的銷售少了一分機會。
被丟棄的書
近十五年的時間里,我曾有過一個很大的地下室。其實我并不需要它,也就是說,它本來很有可能被閑置。結果不然。因為有了這間屋,好多東西明知用不上,我卻不肯把它們拿去送人或扔掉。比這更甚的是,這間地下室總是鼓動我,準確地講是蠱惑我,把一些并不真正令我心儀的物什帶回家,一樣樣積攢起來,直到被堆得滿滿當當。
在這些儲藏物中,當然也有書。每當家里或辦公室的書架沒了地方,我都會拿下幾本書,放進地下室。這些書有的我已經讀過,但不想再放在身邊;有些我一時還不想看,以后或許也不會看。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念大學時用過的所有教材,為雜志寫專欄時點評過的經濟學書籍,淘貨時被打了眼的假古董書,還有副本、發票簿以及各種不中意的禮物,統統被我塞進了地下室。到最后,這些“次等”收藏品的規模大約是三個“畢利”(計算私人藏書量的通用標準)。
我這輩子從來沒想過,除了把這些書存在地下室,我還能拿它們做什么。對這些舊物或無用之物來說,這間地下室就像是一家管理有方的收容所。可于我而言,它卻漸漸變成了一個令人傷感的危險之地。有時候,我連續幾周都不會下去一趟。一想到要面對那堆記錄著失望和挫敗的貨色,我都會心生畏懼。話說,有誰愿意去參觀一座品類齊全、展示個人失敗史的博物館呢?
后來,某年9月11日,“洪水”來了,不是從上面,而是從地下。在這秋高氣爽的日子里,我家的地下水泵就這樣沒來由地把整個地下室泡了湯,浸濕了屋里的各種家什,書架最下面一層自然也未能幸免。
一般情況下,如果遇到這種事,我一定會氣得跳腳。說不定因為這次事故,我和那些讓人傷心的藏書也會從此和好。可是,就在水災前一個禮拜,我剛剛決定搬家。從那時起,我已經知道,我就要和地下室堆積的大部分物品分道揚鑣了。
就在地下室淹水幾個星期之后,我把堆在里面的一部分書扔掉了;一部分交給了廢品收購商。
后來,又發生了更糟糕的事。就在我收拾完東西,眼看就要搬家時,我從地下室一處沒被水淹的角落,發現了兩只紙箱。我完全不記得,那里面竟然裝滿了書。于是,我想出一個主意。我在小鎮教堂門口擺了一只書架,把各色書籍在上面一一碼好,然后又在旁邊貼了張紙條,對情況做了說明。
一個月后,當我把書架取回時,它已經空了,徹徹底底地空了。一時間,我的心情變得比之前更糟了。
被虐待的書
筋瘤并不是瘤,而是一種生長在關節部位的囊腫,里面包著膠凍狀黏液。治療筋瘤的一個土辦法,是用一本厚實的書用力拍打患處,注意,不是用木板、錘子或卷起來的報紙,而是書。據說這個辦法一方面可以讓囊壁破裂,加速身體對黏液的吸收,另一方面,用書來拍打相對安全,不會給身體造成更大的損害。
除了治療筋瘤,書籍也可以在其他時候充當重物之用,分量隨人挑選,比如說制作樹葉標本,把弄濕的紙幣壓平等等。這時候,書籍變成了材料,進一步說,是一種潛在的工具。
另外,人們還可以用書作為支撐物來防止搖晃,或用它讓窗戶保持固定的縫隙,以便空氣流通;再有,人們還可以把書當作杯墊,或者在心理治療時把它放在病人頭頂,作為意念練習的輔助工具。當然,你也可以從書中扯下幾頁,以解某種難以啟齒之急。
可是對那些提出、采納和容忍這些建議的人來說,這些做法難免會讓他們臉上無光。事態得多么危急,才會讓一個人把書當成工具或者廢料?依我看,這樣做的人要么是傻瓜,要么是惡人。一個人就算是長了筋瘤,也該想想其他法子,而不是拿本書去拍。
說到底,人類對待書籍的態度標志著人與文化之間的關系。一個人如果覺得一篇文字寫得太爛,可以討厭它,也可以大聲說出自己的觀點,甚至索性撕掉它。但是,只要裝裝樣子就好!對待書籍,我們還是該多些敬畏才是。
(本文摘自《書情書》)
責編:馬京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