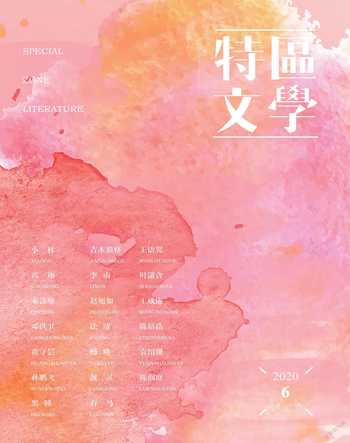“大灣區文學”:作為對象和方法
王威廉 陳培浩
陳培浩:《特區文學》的“大灣區文學地理”欄目一晃就快一年了,回顧起來挺感慨。這一年期間發生了至今仍影響著世界的新冠疫情,當然,我感慨的不僅是時間和世事,而是一件當初我們并不知道會呈現為什么形狀的事情,就這樣做下來了。在我看來,重要的倒不是我們梳理了哪些“大灣區文學”的作家作品、文學現象和審美價值,而是我們找到了什么樣的方法去面對一個新生的概念。我們都清楚地知道“粵港澳大灣區文學”概念的提出乃是“粵港澳大灣區”這一經濟規劃概念推動的產物。換句話說,“粵港澳大灣區文學”并不是一個自明地成立的概念。因此,如何找到有效地面對此一概念的方式就非常重要。找不到正確的打開方式,很可能就是跟在一片鑼鼓喧天中熱熱鬧鬧,但沒有提供任何有價值的東西。比如有人就很擔心這是一個政治先行的概念,不過是換個帽子把珠三角文學和港澳文學再炒一遍。這種擔心當然不無道理,但也并非必然如此。所以,我想最后一期討論面對“大灣區文學”這樣概念的方法,也是很有價值的。稍微回顧了一下,我覺得這個欄目事實上用到了四種處理“大灣區文學”的方法。其一就是最常規的存量盤點的思路,就是以城市為單位,檢視“大灣區”地理范圍內重要的作家作品、文學現象和歷史源流。這是一種最基本的思路,我們邀請的嘉賓絕大部分用這種思路來面對所在的城市文學現象。這種方法的好處是盤點了存量,建立了目錄,對不熟悉“大灣區”的讀者來說,它具有某種閱讀指南的作用。這種方法的局限,就在于它較少觸及“大灣區文學”這個概念的可能性和應然性,從而也就喪失了與這個概念的生產性迎面相逢的機會。
王威廉:存量也是重要的,如果我們不知道存量,就完全不知道在這片地理上的文學是以怎樣的形態存在著的。不妨說句殘酷的話,不是每片土地上都是有文學的。的確,如你所說,可能一開始我們覺得“大灣區”與文學的距離特別遙遠,因而這種并置顯得有些生硬。粵港澳大灣區跟文學之間有什么關系呢?其實我也是困惑的,我跟你做“大灣區文學地理”這個欄目,實際上也是在不斷回應自己的這種困惑。“大灣區”首先是一個政治經濟概念,這自然不可否認,但是,我在意的是一個重要概念的誕生所具備的那種能量。一個概念的提出,它首先一種凝視、一種照亮。概念便是一種不可回避的視角,向左、向右,或是向上、向下,從而重新看待乃至定義了世界。因此,如果沒有一個有力量的新概念的加入,那些所謂的“存量”也就喪失了一次又一次得到“照亮”的機會,這至少意味著缺失了一種創造的可能性。
陳培浩:我之前就說,討論“大灣區文學”,不能忽視這個概念與一般區域性概念的差異。大灣區不同于北京、上海、廣東、廣西這樣的行政區域概念,不同于西北、華東、華南這樣的泛區域概念,也不同于江南、嶺南這樣帶有鮮明文化指向的文化區域概念。大灣區作為一個區域概念,超越于一般的行政區域概念,是一個跨行政區域的生產性概念。所謂生產性概念區別于一般的描述性概念,后者對既存事實做出描摹和概括,而前者則帶著前瞻性和建構性,在準確把握事物發展規律的前提下,創造性地催生尚未顯形的事物。因此,討論“大灣區文學”不應停留于存量層面,還應進一步拓展到增量層面,也即更加重視“大灣區文學”概念所打開的獨特經驗領域和審美價值領域。不僅著眼于區域歷史文化,更關注技術迭代和時代新變賦予“大灣區”的新質。以對文明轉型的預判,把握“大灣區”將為中國當代文學創造的前所未有的“可能性”。如此,作為增量的“大灣區文學”才具有更加建設性的意義。這種討論“大灣區文學”的方法,指向的不是“大灣區”地理范圍內無差別的文學現象總體,而是希望此一概念能發揮更有效的價值建構功能,因而更強調的是能彰顯大灣區文學經驗特殊性、可能性和典型性的作品。在我看來,這種討論方法其實是有價值的本質主義,相比無差別的描述,它更具立場。做得好的話,便能通過它顯影某些真正有價值的東西。
王威廉:增量就是在存量的基礎上做創造性的聯系,從而發現乃至發明一種文化的語法。聯系便是在差異當中展開的。比如說,粵港澳三地作為地理事實本來就是客觀存在的,但是它們之間的差異性是比較大的,我們接納這樣的差異性,但我們沒有去思考這種差異性內部的更多關聯性與可能性。所以說,這是一次契機,“逼迫”著我們必須尋找到差異性文化之間的那些有機聯系。歷史的“逼迫”是不容忽視的,有多少的歷史必然性是從這樣的機制當中誕生的。粵港澳三地在文化話語中顯示出了各自的差異性,但這種差異性恰恰只有文學才能理解和包容。因為文學所面對的不是那些比較外在的事物,文學所審視的是細微的生活肌理,比如說我們的日常生活本身。在大灣區的不同城市里面,我們的確可以尋找到一些相似的生活方式,還有相似的方言、相似的民間信仰,這些構成了一種近似于文化共同體的基礎。但目前我們還不能直接說它們是一個文化共同體,因為可能同樣的生活、同樣的現象,在不同的話語框架的闡述下,所得出的意義是不同的。但是,我們畢竟還是擁有了這樣一套比較相似的文化模式,作為不斷對話的基礎。在這種既相似又疏遠、既疏遠又相似的過程當中—有點像當下中國與世界的微妙關系—新的文化是有可能被創造出來的。
陳培浩:在欄目的推進過程中,我們其實也在踐行著一種“從灣區發現世界史”的方法,特別是在對中山、江門、肇慶、香港、澳門的討論中,這種思路幾乎是不期然之間就涌現了。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之所以特別,就在于它們恰恰是在近代全球史背景下開始浮出世界歷史地表的。假如沒有15-17世紀的世界歷史轉型,香港、澳門就永遠都是那個小漁村。假如沒有澳門的存在,香山可能就走不出鄭觀應、孫中山這樣的人物。在討論肇慶、澳門時,我們一再談到利瑪竇、羅明堅、金尼閣等傳教士。將這些傳教士的行為理解為“國際主義精神”顯然是一種誤判,但卻不能不看到他們把某種世界性元素帶進中國的事實。利瑪竇的故事是一個典型的近代的故事,是一個拓荒者攜帶著一種文明的種子,執著地要在另一種異質文明的腹地種下,并讓其生根發芽的故事。所謂傳教,就是要把根植于另一種文明中的信仰體系進行空間移植。它要挑戰的就是已經獲得了制度、文化等加持的觀念系統。在金尼閣的故事中,我們看到在歷史條件尚不具備的情況下,這種挑戰的悲劇性,金尼閣耗盡心力的“西書七千部”翻譯計劃隨著他的去世便告流產。在世界史視野下回眸這些留在大灣區的文化蹤跡,給我們非常重要的啟示:很多事情的滄海桑田背后,可能有某個正在發生或轉型的歷史邏輯。因此,今天談論大灣區文學,其實是要求我們去預判和面對未來正在展開的世界歷史邏輯。
王威廉:在“大灣區”這個語境之中我們回望這塊區域的歷史,尤其是以更加開闊的全球視野乃至文明模式來探究細部,就會有新的視角。比如,以往我們指代廣東文化,一般會用“嶺南文化”這個概念,這個地理概念是很有意思的,是用山的分界來作為地理的劃分,不僅隱藏著陸地的視角,而且與“中心”相對的某種“偏遠”也從中一覽無遺。但現在這個“大灣區”所蘊含的地理視角無疑是指向海洋的。但它又不像是20世紀80年代之際那種比較主流的說法:“從黃土文明走向深藍文明。”我們當然知道“深藍文明”的意思,但那太過浪漫化,還是會顯得比較空洞。而“大灣區”是不空洞的,它指向了一個具體的地貌:灣區。從全球來看,經濟最發達的幾個地方都是灣區,從美國的紐約灣區、舊金山灣區,到日本的東京灣區,再到粵港澳大灣區,都是經濟特別發達的地區。這不是一種偶然,而是由當代世界的經濟模式與結構所決定的,那就是以海洋運輸為主體的全球化貿易體系,這給灣區提供了其它地區無法媲美的機遇。所以說,灣區本身就帶有當下世界根本特征的隱喻色彩和象征色彩。如果我們打開世界地圖,或是拿出地球儀,我們甚至可以說,整個人類所居住的大陸相對于浩瀚的海洋來說,實際上都構成了一種灣區式的存在。這就提醒我們,一定要以一種更加宏闊的視野來審視“灣區”的存在。
陳培浩:探討大灣區文學,還有一種方法就是將“大灣區文學”這一概念命名背后的文化邏輯也作為一種探討對象。就像你說的,“大灣區文學”和“嶺南文學”這兩個概念在外延上有一些重疊,但它們的命名邏輯卻完全不同。“嶺南文學”強調的是“嶺”,這是一種土地文明的劃分標準;“大灣區文學”強調的卻是“灣”,是一種基于海洋文明的劃分標準。換言之,我們必須留心到“大灣區文學”這個概念背后的精神價值。在做了一整年的“大灣區文學地理”之后,我現在想說兩點:其一是灣區是一種近代世界史的產物,灣區的精神遺產就是文化對話和文明融合。不久前看到樂黛云
教授說“我依然相信跨文化對話的可能性”,這句話顯然是針對當下某種逆全球化潮流和文化對抗主義的。跨文化對話不是為了取消文化主體性和差異性,而是為了多種文化的共存,因此文化對話遠比文化對抗要有意義得多;其二是任何概念都可以被談論,關鍵是談論它的方式。每個概念都有其匹配的打開方式,打開方式不對,也可能誤入歧途。
王威廉:我們現在特別容易看到兩種最極端的話語在爭辯:一種是西方的現代性話語觀念,一種是中國的民族主義思維。這兩種話語遭遇在一起,必然會產生交鋒。我想,這一點是毋庸諱言的:大灣區恰恰就處在復雜話語此起彼伏的核心地帶。不妨說,這樣的爭論所帶來的別扭,才是一種現實的常態。那么,如果說能直面這樣的困境,便不僅僅是大灣區所面臨的一個困境,更是中國本身亟待走出的困境。我們如何來表達自我,我們如何來跟世界進行對話,我們如何讓中國文化獲得一種世界性,都是我們要認真思考的。從這些角度出發,大灣區文學它所具有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這恰恰是我們這個時代最尖銳的、最不可回避的一個區域,這才是我們這個時代真正的現實主義,一種世界視野下的現實主義。在這樣的難度之下,一個作家去創作,雖然有極大的挑戰性,但也是在真正回應著歷史,是在直面歷史的契機。像置身于深圳的作家鄧一光先生,他的長篇小說《人,或所有的士兵》,就是我所期待的那種大灣區文學的方向,至少他讓我們看到了一種可能性,他召喚著更多的可能性。這就像是盡管我們現在強調“內循環”這個概念,但同時也一直在強調“外循環”的同等重要性。因此,寫作不能變成籠中敘事,依然要在一種大視野中來實現文學回應時代的能力,以及文學創造文化的那種造血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