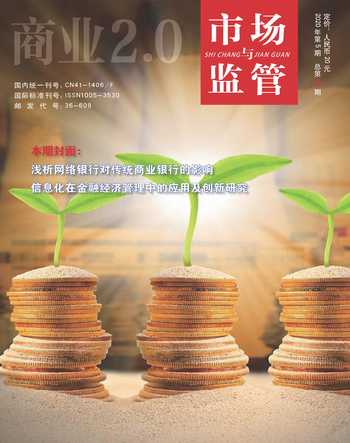致特殊體質被害人死亡案件中刑法因果關系的判斷
黨婉晴
摘要:目前,在司法實踐中致特殊體質被害人死亡的案件時常發生,且已經類型化。但是,由于理論界對于刑法因果關系的認識的不同,導致在司法實務中各地的審理結果不一,甚至出現了同案不同判的現象,司法的公平和正義也受到影響。本文基于對刑事司法實踐中的104個相關案例的分析,分析出在此類案件中司法裁判中在因果判斷中存在的問題及原因,進而得出在司法實務中如何進行因果判斷的合理路徑。
關鍵詞:特殊體質;因果關系;條件說;客觀歸責論
1.問題的提出
對于刑法中因果關系如何判斷的問題,通說是將其作為不成文的要素納入司法判斷的客觀事項的范圍之內的。正是由于這一“不成文”的特點造成在司法實踐中因果關系的判斷模棱兩可,尤其是在處理疑難案件中更是遭遇困境。如本文所探討的致特殊體質的被害人死亡案件中因果關系的判斷就是刑法中因果關系的判斷遭遇困境的代表,因為這類案件幾乎涉及了刑法中關于因果關系判斷的方方面面,對于該類案件因果關系的合理的判斷路徑對于其他類型的案件極有可能也具有適用性。因此,導致特殊體質者被害人死亡案件中刑法因果關系的判斷就有非常大的研究價值。
所謂特殊體質者,指的是因為患有嚴重疾病或者其他原因導致身體狀況和正常人相異的人。在司法實踐中,常常會發生這樣的案件:行為人對被害人實施了諸如語言謾罵、推搡、撕扯、輕拍等危險性較低的傷害行為,這些行為通常情況下不會造成被害人死亡的嚴重結果。然而,由于被害人所具有的不同于正常人的特殊體質,使得行為人的危險性較低的行為在本不該導致被害人死亡的情況下誘發其疾病發作,最終導致了被害人死亡。所以,在司法實踐中,涉及到致特殊體質被害人死亡案件,產生的問題就是傷害行為與死亡后果之間是否具有因果關系?被害人死亡的結果是否歸責于行為人?這個問題也是實務中處理該類案件的爭議焦點所在。同時,對于這個問題的回答,關系到刑法因果關系理論、歸責理論是否全面合理。本文以在中國裁判文書網收集到的104份涉及致特殊體質被害人死亡案件的司法文書為樣本進行研究[1],得出此類案件的司法裁判的結果差異很大,甚至出現同案不同判的現象,并且本應是入罪率較低的案件卻有著很高的入罪率。
2.致特殊體質被害人死亡案件因果關系存在判斷困境的原因
2.1必然因果關系說與偶然因果關系說
必然說認為,刑法中的因果關系必須是危害行為與結果之間存在必然聯系。只有必然因果關系才能成為刑事責任的客觀根據。與之相對的是偶然因果關系指的是行為人所實施的危害行為與危害結果之間存在外在的、非必然的聯系。必然因果關系與偶然因果關系之間的區別在于:行為本身是否蘊含著危害結果發生的根據,或者說,行為是否內在地包含了導致某種結果發生的客觀定律。[2]舉例來說,被害人因為行為人的辱罵導致冠心病發作死亡的案例中,行為人的辱罵、推搡行為不可能導致被害人死亡,先行為不能導致危害結果的發生。而在介入了被害人具有特殊體質即冠心病這一因素之后,被害人的特殊體質與危害結果就具有了因果關系。這是偶然因果關系說理論的運用,偶然因果關系的學說在實務中被廣泛應用。
必然因果關系學說與偶然因果關系學說都有其理論弊端:一是必然因果關系學說,從該學說的主張來看,刑法上的原因,還必須是其所具有的可能性在一定條件合乎規律的變成現實。也即是說,必然原因的作用需要一定的條件相結合。但是,不能把條件認為是原因。這么一來,實踐中也會出現問題。當結合這種原因行為對危害結果產生作用的“條件”正好是某行為人實施的危害行為,就無法讓行為人承擔這一危害結果產生的刑事責任了。這是有損法律的公平正義的。“必然說”要求危害結果的產生必須是行為中所包含的產生結果的現實性合乎規律的轉變而來。人們很難判斷行為是否會產生危害結果,該結果的產生是否會合乎邏輯規律,因為許多規律還并沒有被人們認識和掌握。[3]這就有可能使得一些利用人們還沒有掌握的規律進行犯罪的人逃避應有的法律制裁。如果適用必然說,本文所提及的致特殊體質被害人死亡案件中的因果關系就無法進行判斷。被害人具有特殊體質,在一定外因作用下,引發自身疾病的發作,導致死亡這一危害結果的發生。按照必然說的理論,則主張內因的絕對作用,死亡這一危害結果的發生是由自身疾病的發作導致的,則自身疾病時內因。當行為人不知道被害人具有特殊體質的情況下,外在的原因只是條件,對危害結果的產生沒有實質影響;當行為人不僅知道被害人具有特殊體質,而且還故意利用被害人特殊體質這一要素的情況下,此時依據必然說的理論,行為人的行為不是原因,而只是條件,那么就會使行為人利用特殊體質作為犯罪工具,從而逃避法律制裁。二是偶然因果關系學說,該學說主要時針對上述“必然說”追究范圍過于狹窄而提出的。因為“在特定的場合,在特定的條件下,外因也能起到決定作用。”[4]但是從“過于偶然的因果關系進行歸責是否妥當?根據何種具體的規則,在偶然因果關系的范圍內確定哪一個原因是最終負責的原因?”[5]可見,如果實務中運用偶然說又很容易導致因果關系的判斷過于隨意,導致刑事處罰范圍擴大。
2.2條件說
條件說是奧地利刑法學者Glaser提出,其基本內涵是:如果沒有這個始作俑者,結果并非即不發生,并非流程中中間因素的序列就會變動,則行為與結果顯然都不能歸溯于這個人。相反地,如果沒有這個始作俑者,結果即不可能發生,或者即循完全不同的路徑發生,則有充分理由認為結果是這個行為人的行為所造成,應歸責于這個人。[6] 由此,條件說指出,如果要認定危害行為是危害結果產生的原因,則二者之間的關系應當符合“若無前者,即無后者”的公式。羅克辛稱這個公式為“想象中不存在”公式,即導致一個結果的各種條件,在具體結果沒有被取消就不能想象其不存在時,都應當看成時是原因。因此,作出原因就是各種不能不考慮的條件(condicio sine qua non),就是各種沒有它們本來就不會出現這種結果的條件。[7]
條件說與其他刑法因果關系學說的優勢在于能夠有效避免在判斷因果關系時將個人的主觀因素摻雜其中,由此做到了堅定秉持因果關系的客觀屬性。雖然條件說為刑事責任的確認了一個客觀范圍,但是這一范圍過大是其難以克服的弊端。因為條件說將產生于結果之前的一切必要條件都看作是刑法上的原因,這樣就可能不當擴大刑法因果關系的范圍,從而不當擴大刑事責任的追究范圍。[8]
2.3相當因果關系學說
相當因果關系說,是為了限制條件說,認為應從必要條件中挑出部分條件作為法律原因。該學說主張“以行為當時一般人能夠認識的事實和行為人特別認識的事實為基礎,判斷是否存在相當因果關系。”[9]該學說是以條件說為基礎并對條件說予以限制,即僅承認部分條件與結果之間具有因果關系,對該部分條件的要求是要符合“相當性”的標準。“相當性”的判斷標準是一般社會觀念或者社會經驗法則。相當因果關系一方面排除條件說中的非相當的條件,以達到給因果關系“瘦身”的效果;另一方面,相當因果關系“相當性”的判斷標準為行為人實施行為時正常人民的認識水準。[10] 相當因果關系學說根據相當性德判斷標準不同,分為主觀說、客觀說以及折中說。主觀說以行為人行為當時認識的事情以及可能認識的事情為基礎。客觀說主張所謂客觀的事后預測,該說站在裁判官的立場上,認為對行為當時存在的一切事情以及行為后產生的事情,只要它們對一般人來說曾是可能預見的,都必須考慮。折中說認為要以行為時若是一般人就曾經能夠認識的事情以及行為人特別認識了的事情作為判斷的基礎。[11]
3.客觀歸責理論在該類案件中的具體應用
3.1歸因:以條件理論來進行事實上因果關系的判斷
因果關系畢竟在特定條件下的一種客觀聯系,所以盡管條件說受到眾多批判,然而不能離開客觀條件認定因果關系。而且從嚴格意義上,被害人的特殊體質并不是介入因素,而是行為時已經存在的特定條件。只要堅持條件說,就可以做到堅持因果關系的客觀性,防止了因果關系在判斷中介入主觀因素,這也是條件說的最大優勢。如本文導致特殊體質被害人死亡的案件中,行為人對被害人實施了毆打等行為,雖然毆打行為本身不會導致死亡,但是毆打行為導致被害人因為自身疾病發作而死亡,沒有毆打行為就沒有死亡結果。在這個層面上來講,條件說解決了客觀歸責理論的第一個層面即歸因層面。
3.2歸責:加入規范性的歸責進行責任范圍的確定
客觀歸責理論以因果關系的“條件說”為前提,所以該理論和因果關系相當性的判斷類似。但是客觀歸責理論關注的是行為與結果的動態判斷、進行實質性的考察,是否制造了法所不容許的風險,風險的實現是否數以構成要件的效力范圍,因果流程是否在構成要件的效力范疇內。客觀歸責理論以事實與價值的二元界分的方法論為基礎,通過遞進的兩個判斷層次序先進行事實因果關系的判斷,再在確定事實因果關系的基礎上依據前述三個步驟進行價值評判上的規范歸責。[12]
具體到本文,在致特殊體質被害人死亡案件中,對于能否將被害人死亡的結果歸責于行為人,通過客觀歸責理論首先在事實和形式層面上判斷行為人的行為與被害人的死亡的危害結果之間是否存在事實因果上的關聯,在確定二者之間存在事實上的因果關聯后,再通過規范評價循序漸進地對行為人地行為進行價值判斷和實質判斷,首先判斷行為人地行為是否制造了法律所不容許的風險,其次要分析行為人的行為是否實現了法律所不容許的風險,最后要深究行為與結果之間的關系是否屬于構成要件的效力范圍之內。進一步對客觀歸責理論的三個步驟來分析:首先行為人對被害人實施諸如言語刺激或者輕微肢體行為并沒有制造法所不容許的被害人死亡的風險,其次行為人的行為人并沒有實現被害人死亡的風險,客觀歸責理論的前兩個判斷步驟都否定了張某的行為可以客觀歸責,也就沒有必要進行第三個步驟來判斷危害結果是否在構成要件的效力范圍之內。
參考文獻:
[1]張明楷著:《刑法學(上)》(第五版),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175頁.
[2]蘇惠漁著:《刑法學》,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124頁.
[3]吳建國著:《唯物辯證法對偶范疇論》,江蘇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5頁.
[4]周光權:《刑法因果關系:從哲學回歸刑法學──一個學說史的考察》,載《法學》2009年第7期,第119頁.
[5]陳興良:《從歸因到歸責:客觀歸責理論研究》,載《法學研究》2006年地2期,第82-83頁.
注釋:
[1]以上樣本均來源于中國裁判文書網,在“刑事案件”中以“特殊體質”為關鍵詞進行搜索,截止到2020年9月7日,總共檢索到311個司法案例,其中涉及致特殊體質被害人死亡的案件共120個。經過人工刪選(排除不同級別法院對同一案件的同判與裁定減刑的相關案件),最終篩選出104個有效案例。
[2]張明楷著:《刑法學(上)》(第五版),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175頁。
[3]蘇惠漁著:《刑法學》,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124頁。
[4]吳建國著:《唯物辯證法對偶范疇論》,江蘇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5頁。
[5]周光權:《刑法因果關系:從哲學回歸刑法學──一個學說史的考察》,載《法學》2009年第7期,第119頁。
[6]許玉秀著:《當代刑法思潮》,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2005年版,第427頁。
[7][德]克勞斯·羅可辛著:《德國刑法學總論》第1卷,王世洲譯,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232頁。
[8]陳興良著:《刑法教義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第289頁。
[9]陳興良著:《刑法教義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第295頁。
[10][德]漢斯海因里斯·耶賽克、托馬斯·魏根特著:《德國刑法教科書(總論)》,徐久生譯,中國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347頁。
[11][日]大塚仁著:《刑法概說(總論)》3版,馮軍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163頁。
[12]曾濱:《客觀歸責理論探究》,中國政法大學碩士學位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