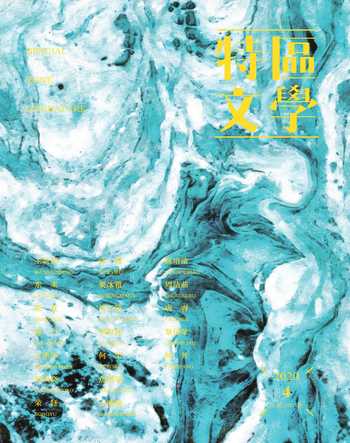西渡導讀
招隱山中
顏 隼
當燃燒的小池塘仍在做它零碎的夢
在松樹附近,在萬物那最高的藍天下,
男孩有限的生命在白色石頭中飛逝,
而這造化與孕育新生命之所
在三角楓中發出神圣的回響;
請再一次贈予我們游蕩的夢境吧—
在他善良的軀體上忘掉嚴酷的時間—
只有他的與我們面對面敞開的溫馨
和讓人清晰地注視的純潔高雅的陽光。
把榮譽給予上蒼,把榮譽給予他的烏龍,
被遮隱著正面的臉,—開闊的后山嶺……
道觀,自然,他使我們的靈魂感到異常樸實——
并從世界上獲得前所未有的自由—
他像花兒一樣長久地洋溢著芬芳,
帶著我們永恒的夜鶯守候在校園旁,
帶著我們的松鼠、象牙詩篇棲居在地球上。
讓我們總是知道某種饑餓的心靈
能忘卻日子排除障礙覓得一方歇息之所。
西渡:燃燒的池塘與最高的藍天
隱逸詩在古典詩歌中是非常發達的一類,但在新詩中卻逐漸淡出。這是因為隱逸在現代生活中已經不具有啟示和捍衛生命自由的意義。古人所謂隱士其實是統治群體中的一員,但他自愿放棄統治者的特權,放逐到山林中(當然也沒有成為被統治的一員)。進入現代,大部分知識分子早已不屬于統治群體,也就是草民,換句話說,他本來就處于隱的狀態,說隱逸就是自抬身價了,也是對自身處境的一種誤解。所以,他和隱士追求的方向剛好相反:隱士追求的是由顯而隱,現代知識分子追求的則是由隱而顯—如此方能體現知識和知識分子的價值。因此,現代詩人缺少寫作隱逸詩的動機,隱逸詩也難以感動現代的讀者。在詩歌主題的范圍內,只在為人的生命尋找安放場所這一點上,現代詩人和隱逸詩人還存在某種交集。正如其最后兩行所表明的,這首詩正是圍繞這一點展開的。
除此,這首詩的主題和古代的隱逸詩并無共同之處—雖然它也提到了“自然”,但這里的自然是一個“造化與孕育新生命之所”,它的池塘是“燃燒”著的。這個自然的方向是向上的,指向“萬物那最高的藍天”,充滿著昂揚向上的氣息,而且這一指向在詩人看來具有“神圣”的性質。這和隱逸詩傳統中那個消極的、無為的、虛靜的—明顯指示著一個向下的方向—自然,全然不同。
這種不同不僅體現在這首詩的意義層面,而且也體現在它的聲音層面。這首詩的語調、節奏都表現出一種興奮、發揚的特征。也就是說,這首詩在處理隱逸題材的過程中,實際上走向了這一題材的反面,用生命的張揚主題替代了這一題材中原本所含有的生命的消解主題。這使他回到了隱逸詩的源頭陶淵明—這里存在一個有趣的悖論,作為隱逸詩之祖的陶淵明,其實是反隱逸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