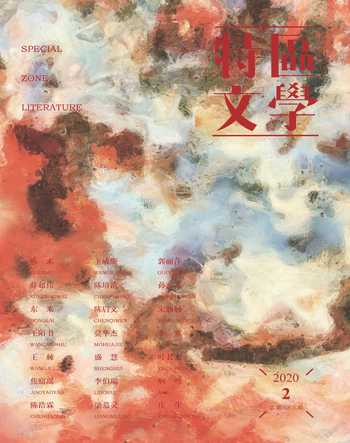佛山:粵味的根系與柔軟的佛系
王威廉 陳培浩
陳培浩:我先談談對佛山的印象。佛山是一個非常低調的城市,這座城市在2019年已經成為中國第三個GDP超萬億的地級市,佛山在經濟體量上一直是廣東第三大城市。但這座以佛為名的城市似乎也比較“佛系”,比較低調。就城市形象來說,佛山可能不如東莞具有標簽效應。佛山地理上很大的優勢就是毗鄰廣州,廣佛同城大概是從十年前就開始的城市發展戰略。廣州地鐵直通佛山,從佛山南海區到廣州的距離其實并不比花都、從化到廣州中心城區更遠,廣州的房地產發展也自然溢價到佛山。跟廣州地理上的接近,既給佛山帶來便利,可能也使佛山在城市形象上處在廣州的陰影之下。就城市內部發展來說,佛山不是那種以一極為中心、等級秩序分明的前現代城市。佛山內部有多個中心,佛山的城區禪城自然是很有底蘊的一個中心;毗鄰廣州的南海區也是一個中心,南海的金融高新區和千燈湖地區是高科技企業集聚又十分宜居的區域;佛山更為人所熟知的地區可能還是順德,粵菜的起源就在順德。現在佛山又在靠近廣州南站的區域打造新一極—佛山新城。因此,從均衡性上說,佛山非常符合一座融合高科技和人文性的多中心未來之城的標準。
在我看來,北上廣深已經變成具有某種“惡魔性”的城市了,這種城市像一個龐然大物,一頭既能騰云駕霧,也能吞噬無數個體肉身的怪獸。龐大的城市往往是資源的聚集地,也是標準的制訂者,但它對平民、青年、底層等弱勢人群的不友好性往往更加突出。反而是佛山這類兼得了現代性、科技性和人文性的城市可能會成為未來理想城市的樣板。
王威廉:佛山文化在廣東來說,是非常富厚的,佛山是粵劇的發源地,有舉世矚目的舞獅傳統,還有南國陶都的贊譽等等。佛山自古以來不僅經濟發達,商業繁榮,而且文教也很鼎盛,據統計,自唐代至清光緒三十年(1905年廢除科舉),佛山有文進士786人,武進士98人,舉人近4000人。其中文狀元有5人之多。因此可以說,佛山一直是嶺南文化的核心區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來理解“廣佛同城”,才能體會出這種“同城”所意味著的重要性。嶺南文化如果要在今天的文化體系中煥發出新的特質,佛山是不容忽視的重要存在。今天我們談論大灣區,那么佛山跟廣州一道,提供的是一種文化的創造,從而構建一種區域文化的真正的地方品格。如果沒有這點,灣區便不能產生深刻的文化認同,也不會產生更加有機整體的活力。就珠三角來說,佛山作為歷史文化名城的知名度應該是僅次于廣州的,因為影視作品中的佛山形象特別多,甚至可以說,大眾對佛山的一般性印象大多都來自香港的功夫電影。比如黃飛鴻、葉問系列的電影。這股浪潮的源頭自然可以追溯到祖籍是佛山順德的李小龍。佛山形象帶動了佛山旅游,但是,這種影視塑造的形象也會變成某種符號,遮蔽城市的多元性。這是阻礙也是契機。
陳培浩:佛山文化有三個讓我印象深刻的點:一是順德菜所代表的粵菜文化;二是黃飛鴻、葉問所代表的武術文化;三是康有為所代表的近代改良思想文化。很多人知道“食在廣州,廚出鳳城”,這里的“鳳城”就是順德,也就是說,廣州美食是佛山順德的廚師發展出來的。很多人對粵菜的特點無法說出個所以然來,但對廣州早茶所代表的那種市民文化的悠閑特征印象深刻。廣州早茶并不僅僅就是喝茶,它的茶還連著各式精美的小吃餐點,從早餐吃到午餐。所以粵式早茶的概念其實大于茶,也大于餐,它是一種商業文化和市民文化相融合之后的日常生活方式。為什么廣州作為一座特大型城市依然給人一種親民的氣息,跟這座城市融進骨髓里的市民生活觀是有關系的,而這種生活觀其實來自于佛山。我對這種生活觀有一個概括,叫做“味大于神”。順德師傅窮盡舌尖美味的那種想象力和探索精神,正是這種日常生活觀在支撐著。所以,不管是廣州還是佛山,其城市文化氣息是市民的、世俗的、及物的、歡樂的,這里對高蹈的形而上思索相對淡然。這種城市文化性格從明清以降就是如此了,近代以來國際文化格局的大變,廣州是最早通關的城市之一,毗鄰廣州的佛山也產生了晚清政治改良文化的代表人物康有為。
王威廉:你說的我很認同,前兩點我在前面也提到了,粵菜便是生活文化,而武術在我這里則是放置在影視形象的框架內。武術不是一種生活文化,不是生活的必須,又不能完全作為表演文化,因此,武術作為一個傳統文化元素,要落實到現實層面,今天有它的困境。反而是影視文化能夠繼續解放武術的文化潛能。在這里,我想重點談談康有為。我覺得我們對康有為的研究是不夠的,或者說角度是不夠的。我期待著那種能夠還原歷史語境的研究。我們都知道康有為的“戊戌變法”,他所提倡的“君主立憲”,但他論述的細節我們未必深入思考。比如他說:“民之立君者,以為己之保衛者也。蓋又如兩人有相交之事,而另覓一人以作中保也。故凡民皆臣,而一命之士以上,皆可統稱為君。”這種闡述令人耳目一新,君也并非是傳統的無上皇權,而人與人之間是一種被某種象征性權力見證的契約關系。他還極為重視教育,創辦萬木草堂,以“激勵氣節,發揚精神,廣求智慧”為教育宗旨。他在書法上的造詣也是不能忽視的,他提出了書法“十美”:“一曰魄力雄強,二曰氣象渾穆,三曰筆法跳越,四曰點畫峻厚,五曰意態奇逸,六曰精神飛動,七曰興趣酣足,八曰骨法洞達,九曰結構天成,十曰血肉豐美。”當然,他還有著嶺南文化中對于商業的敏感,有人戲稱他是一個真正的炒房高手,在經濟上做到絕對自立。他和孫中山盡管是死對頭,一個保皇,一個革命,但在各自的立場上,他們都有自己的不容忽視的音色,代表了廣東這片地域對于中國近代歷史的重要貢獻。如今,我們把他們放置在同一個大背景一起思考的時候,就更能跨越歷史的局限性,找到其中鮮活而深刻的東西。
陳培浩:誠然,理解一座城市,不能只看到它的現在,它的此時此刻;要理解它的歷史,它如何從歷史之河中順流而下;也要理解它內在的深度和寬度。康有為對于佛山文化來說,便不是浮在水面,不是典型的,而更像是一個變體。傳統佛山文化本身是產生不了康有為思想里的“烏托邦”元素的。只有在近代的民族危機和思想革命的浪潮中,才會孕育出康梁,但康有為改良思想的底部,我隱約覺得跟嶺南文化特別是佛山文化也有關系,從一個文化代表身上去辨認近代文化的裂變和新生,這是很有意思的話題。
我們不妨把目光放到當下,談談當代以至當下的佛山文學。90年代佛山有一張文學名片,那就是《佛山文藝》,當年在面向打工群體推廣通俗文學方面做出的成績相當令人矚目。這是當年文學紙媒市場化的一個成功范例,《佛山文藝》的調性跟佛山的的務實氣質也是非常相近的。但后來紙媒衰落,《佛山文藝》的市場之路遇到了一些困難,再后來《佛山文藝》也轉型做純文學,于是和所有地方純文學雜志分享著共同的難題。
佛山作家近些年比較活躍的包括寫小說的盛慧、彤子;寫詩的張況、安石榴;寫兒童文學的洪永爭、亞明,這些作家的影響力已經不同程度沖出廣東。盛慧來自江蘇,小說在《人民文學》《花城》《十月》《上海文學》《山花》等重要刊物都發過,短篇小說還曾入圍華語文學傳媒大獎。盛慧早年的作品帶有很濃的江蘇才子味,短篇小說《水缸里的月亮》寫一個母親在生存與死亡之間的絕望掙扎,顯然受到先鋒小說很大的影響,語言很有想象力,也有詩性特征。近年盛慧頗有聲勢的作品《闖廣東》是一部務實之作。務實非常符合佛山的城市性格,小說處理的也是一個非常具有現實性、熱火朝天的重大現實題材,語言和敘事也是現實化的。這也是盛慧融入佛山的文學體現。從江南融入佛山,它在文學上產生的復雜效應需要更全面的評估。
在我看來,佛山作家作為個體當然有很多相當優秀的代表,但作為一個城市,其文學活動所形成的辨析度似乎跟這座城市的經濟體量還不匹配。近年當然也有華語傳媒文學獎永久落戶順德,一年一度的華語文學文學周和佛山自主創辦的佛山文學周,還有廣東省有為文學獎多個獎項也都由佛山的不同區鎮承辦,這都是佛山為廣東文學做出的貢獻。佛山經濟體量龐大,又有獨特而悠久的民間文化,其經濟文化在粵港澳大灣區中當然享有一席之地,但在大灣區文學視野下看佛山,可能要思考的依然是其自身的定位和辨析度問題。佛山不僅是一座對味覺有極致追求的城市,它還是一座有“佛”之城。佛山文學,如果挖掘出這個象征意義上的“佛”,可能會有新的氣象。
王威廉:你提到的這些佛山作家和詩人都很優秀,他們的作品已經很有個人的辨識度。但如你所說,能否將個人的生命體驗與佛山這座城市融合起來,煥發出一種更大的氣象,是他們接下來要思考的。把佛山的文化轉化成文學上的優勢資源,并不容易,可一旦有能力去融合并創新,那一定會是驚人的閃電。其實還有一位重要的作家不得不提,那就是吳趼人。他雖出生在北京,卻在佛山度過青少年時代,自稱“我佛山人”,并以此為筆名,寫了大量的小說、寓言和雜文,被文學史稱為近代“譴責小說”的代表作家。他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在中國幾乎無人不知,無人不曉。“我佛山人”這個筆名中有著多么強烈的對于佛山的自豪感。《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是一種描摹中國現實復雜性的經典,依然對今天的寫作具有巨大的啟發性。你說到佛山文學要挖掘象征意義上的“佛”,確實很有意思。佛山原名“季華鄉”,傳說后來在唐貞觀二年,人們在一道山坡上發現了夜晚有金光射出,挖掘后得到了三尊小銅佛,人們十分驚喜,便在山崗上重修佛寺,成為塔坡寺,“季華鄉”也重新命名為了“佛山”。現在多認為這佛像是南北朝時期的高僧曇摩耶舍帶來的,曇摩耶舍是佛教自南海的海上絲綢之路跋涉來到中國的重要高僧。在這里,我又要提康有為了,提他的一部書:《大同書》。這是康有為的一部非常重要的書稿,1884年開始寫,成于1901至1902年,1913年在《不忍雜志》上發表兩卷,1935年由中華書局出版十卷本。他利用今文經學的公羊三世說和《禮記·禮運》中的大同思想,又吸取了歐洲空想社會主義、資產階級民主主義和達爾文進化論,指出當時的中國處于“據亂世”,必須向已進入“升平世”的歐美資本主義國家看齊,然后才能進入“太平世”,即“大同世界”。他非常具體地描寫了“大同之世,天下為公,無有階級,一切平等”的人類社會遠景,主張用改良漸進的方法去實現這種社會,“去九界”以達人類“大同”。我的意思是,從曇摩耶舍到康有為,從佛教的普度眾生到人類大同的高貴理想,佛山所孕育的文化氣魄是極為博大的,是有著終極性追問的,這樣的追問是文學作品的根本靈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