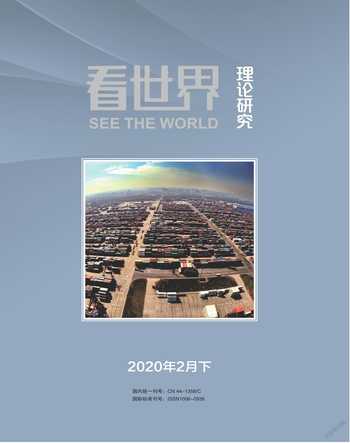簡論元代詩歌與科舉的關(guān)系
摘要: 在王國維“一代有一代之文學”的影響下,提起元代文學,首先想到的就是元曲。其實不然,元代作為多民族多元化的一個時代,在文學方面也體現(xiàn)著多元化,具有充分的包容性。雖然元代詩歌很少能進入大眾的視野,但是在元代,詩歌依舊是蓬勃發(fā)展的,并且比起宋詩,更加活躍,更加接近唐詩的盛大恢弘氣象。但元代的詩歌創(chuàng)作并不是一帆風順的,這和統(tǒng)治階級實行的選官用人制度息息相關(guān),從而,因詩歌創(chuàng)作而形成的詩社也與元代科舉制度產(chǎn)生了聯(lián)系,本文就此簡要分析元代詩歌與科舉之間的關(guān)系。
關(guān)鍵詞:元代詩歌;科舉;詩社
科舉制度作為中國歷史上重要的政治文化制度,淵源于秦漢,肇始于隋唐,成熟于宋元,完備于明清。自唐宋以來,隨著科舉制度的日趨完善,知識分子可以說百無一遺地都被吸引到科舉入仕的這條道路上。這既是這些文人實現(xiàn)“拯物濟世”的社會政治理想的必由之路,也是改變他們社會地位和物質(zhì)生活條件的必由之路,參加科舉早已成為他們最為重要的人生目標。詩社也是在魏晉時期已具雛形,如三曹、七子、竹林七賢等文人墨客遣詞作賦的文人雅集交游活動。唐宋時期更加盛行,蘭亭雅集、香山老九會等,在元代之前,這樣的文人交游活動數(shù)不勝數(shù),除了有消遣玩樂的目的外,大多數(shù)文人通過廣泛交游,使詩歌作為自己的名片,結(jié)交達官顯貴,將自己的名氣傳播于考官及判官耳中,從而為自己的科考添一份額外的助力,這也是這些交游活動對科舉考試有利的一方面。但是,與以往的讀書人相比,元代文人通過科考而進身的機會非常少,但元詩的創(chuàng)作并沒有由此而消歇,反而出現(xiàn)了詩歌創(chuàng)作的繁榮。科舉制度長期廢止,詩社卻蓬勃發(fā)展,似乎冥冥之中使二者產(chǎn)生了另一種反向聯(lián)系。
元朝是一個少數(shù)民族主宰中原的王朝,統(tǒng)治民族蒙古族以其固有的政治及文化傳統(tǒng)影響著元代社會發(fā)展。漢族的科舉選官作為收攬士人與建立正統(tǒng)的重要手段,則是以“學而優(yōu)則仕”為原則評準行政菁英的征募方式,在考試面前人人平等,是為打破世襲與貴族的特權(quán),這和蒙古社會的用人方式是格格不入的。觀元之前唐宋文學為何如此宏大,唐代統(tǒng)治者為了鞏固統(tǒng)治,提倡“守成以文”,采取“大闡文教”的統(tǒng)治策略,科舉取士的取士制度也使知識分子受到極大的重用。清代同樣是由少數(shù)民族入主中原,明清之際,江南文人被統(tǒng)治者多次鎮(zhèn)壓,揚州十日、嘉定三屠等慘案對文人的打擊異常激烈,但自康熙十七年的博學鴻詞科開始,清政府為了穩(wěn)固統(tǒng)治,開始有意識地籠絡知識分子。反觀元朝,元蒙統(tǒng)治者靠武力征服天下,他們重視實用的直觀思維,故重視武備,精騎善射,元代前期的統(tǒng)治者和大多數(shù)人士鑒于宋金滅亡的歷史事實,或反對以科舉取士,或認為科舉考試不能以詞賦作為取士標準。從而輕視文化教育,一直發(fā)現(xiàn)不了儒生對鞏固統(tǒng)治的重要性,致使?jié)h族文人的社會地位普遍下降。蒙古統(tǒng)治者在這種輕視漢文化思想意識的支配下,幾乎停開科舉,阻塞了元代士人進仕的門路。元代文人想通過讀書,通過科舉取士的這一目標就此被阻斷,讀書這條路不再能夠?qū)崿F(xiàn)文人政治抱負,但文人對待讀書的態(tài)度仍是積極的,在詩歌方面表現(xiàn)的尤為突出。劉辰翁云《程楚翁詩序》云:“科舉廢,士無一人不為詩。于是廢科舉十二年矣,而詩愈昌。前之亡,后之昌也,士無不為詩矣。”就先有文獻可知,元代詩人有五千多人,曲作家只有二百多人。在元代,人們看重的依然是文章,是詩。就詩歌發(fā)展史說,詩至南宋之末,其弊已極。宋亡入元,詩風復盛。
雖然元初科舉廢止,呈現(xiàn)給我們的是元代詩歌的興盛,但對于元代文人來說,是被動的,是不得已才將精力和情緒投入詩歌創(chuàng)作上。宋元易代后取消科舉考試,使宋元之際的文人唯一所從事的藝能失去了施展空間,此外又別無所長,生活境遇可想而知。這猶如人生道路的一場大塌方、大斷裂,帶給文人的沖擊和震撼是難以想象的。面對這突如其來的歷史巨變,他們感到惶惑,感到迷惘,感到恐懼,孤獨無助,無所適從成為一種普遍的心態(tài)。因此,吟詩成為他們?yōu)閷W的主要趣向,同時他們希望到群體中去獲得精神慰藉希望在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中獲得面對生活的勇氣和相濡以沫的力量。所以詩人間唱和之風日趨濃厚,宴聚冶游、結(jié)社唱和遂成為士人的常態(tài)生活,大量的詩社在元初開始出現(xiàn)。在科舉遠離文人生活的元初,文人們一方面以耕讀教子為樂,享受著擺脫科舉羈絆帶來的快樂讀書時光,另一方面,他們以結(jié)社賦詩的形式證明著自己作為詩人的存在,以此尋求某種社會認同。
與元初文人不同的是元初文人在科舉停滯后是被迫無奈且又無所拘束地從事詩歌創(chuàng)作,元后期文人則是以更為主動的姿態(tài)抉擇于仕進與作詩之間。元初文人的苦悶來自亡國之痛,對異族統(tǒng)治的不適應,而元中后期江南文士對蒙古統(tǒng)治者并無深度不滿,虞集《玉堂讀卷》云:“書閣暮年偏感遇,但歌天保答皇仁。”張雨《上京賜宴王眉叟有詩次韻》云:“金莖剩有三清露,潤及葵心向太陽。”可見他們對異族帝王的感恩和忠誠之心。然而江南絕大多數(shù)文士入仕無門,無緣被賞識。科舉考試至到延祐元年八月才在全國范圍內(nèi)實行。恢復科舉,對于長期受到壓抑的文人來說,本是一件快慰之事,但不屑于仕進者也大有人在。由于元代后期科舉取士名額的限制,能夠順利通過考試極為不易,多數(shù)士人成為科舉落第者。然而即便有幸擠入鄉(xiāng)試榜列,多數(shù)亦成為下第舉人,或往往因為交通阻塞而不能如期參加朝廷會試,只能充任教授、學正、山長、學錄、教諭等教職,成為進入中心的邊緣人。在科考舉行了二十二年、七科之后,在順帝后至元元年再度被中斷。元代科舉制度的弊端已顯露無疑。后至元六年(1340)科舉制度再次恢復,這一時期伯顏專權(quán)戰(zhàn)亂突起,時局鼎沸,大量經(jīng)籍散遺,文人淪落,學校荒廢,鄉(xiāng)舉、廷試始終不暢,士人遭遇悲慘。在中舉艱難、仕途蹭蹬的情況下,文人們不僅感嘆宿命的無奈,也開始重新思考實現(xiàn)人生價值的新途徑。士人群體流向民間,多以引領(lǐng)士風、振興詩道為己任,很大程度上促進了民間文壇活動的興盛。殆至元末,科舉制度雖延行不廢,但對于士人的吸引力已大不如前。對于親身經(jīng)歷過元代科舉的后期士人來說,他們有著更加真切的體會。正所謂“國家不幸詩家幸”,在如此的人生遭際下,元人用詩歌記錄著世變中的感受,這一時期詩歌創(chuàng)作的主要內(nèi)容在于表現(xiàn)時代主題,作品中往往展現(xiàn)了詩人的真實心境,但對于社會的種種亂象,作家既深惡痛絕又無力改變,所以許多作品中又包含了詩人以世俗的縱樂消解期待有所作為而又無能為力的復雜心緒。雖然各地戰(zhàn)事頻發(fā),但在吳中等地,時局卻相對穩(wěn)定,為這一地區(qū)詩社的興起和詩人間唱和的興盛提供了條件。這一時期的詩社雅集活動是在科舉制度衰頹的背景下展開的,完全是發(fā)自個人意識的,更加主動,不再考慮科舉仕進等問題的文人活動,反映的是科舉影響漸弱之后士人生活和志趣的一個側(cè)面。
元朝統(tǒng)治總共不過百年,科舉時斷時續(xù),文人現(xiàn)狀卻一直不太樂觀。從元初的文人因科舉廢止不得不選擇吟詩作賦,到元后期文人已不再對科舉報太大希望,把吟詩作賦真正當作自己的興趣。這種態(tài)度的轉(zhuǎn)變也滲透在書社雅集這些文人活動中。總的來看,由于時代和歷史的原因,相較于前代詩人,元代詩人的詩歌創(chuàng)作和詩社雅集活動更加遵從自己的內(nèi)心,更能表達自己的真實情感。
作者簡介:
祁晴(1997.4—),性別:女 民族,漢:籍貫(省市);甘肅天祝,學歷:碩士,單位:西北師范大學 ?職稱:無 研究方向:古代文學元明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