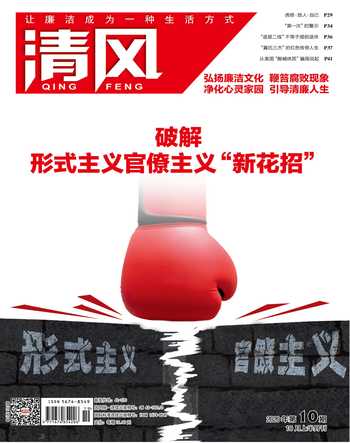黑茶·陶澍
汪太理

喜歡品茶的人,知曉陸羽者多,而了解安化陶澍(1779-1839)者,可能寥寥無(wú)幾。安化黑茶從2010年進(jìn)入世博會(huì)十大名茶行列,即昭示著橫空出世,如今已是家喻戶(hù)曉。與黑茶的顯赫形成強(qiáng)烈對(duì)比,關(guān)于這位晚清高官的種種軼聞,似乎隨著歷史發(fā)展,已漸漸湮沒(méi)在他故鄉(xiāng)的莽莽山野中。
陶澍寫(xiě)過(guò)多首詠黑茶的詩(shī)。有贊美新茶的:“芙蓉山頂多女伴,采得仙茶帶露香。”有描繪黑茶特色與歷史的:“茶品喜輕新,安茶獨(dú)嚴(yán)冷。古光郁深黑,入口殊生梗。寧吃安化草,不吃新化好。宋時(shí)有此語(yǔ),至今猶能道。”有寫(xiě)安化茶農(nóng)的:“茶成與商人,粗者留自啜。誰(shuí)知盤(pán)中芽,多有肩上血。我本山中人,言之益凄切。”
黑茶廣告,若論文采神韻,沒(méi)有比陶詩(shī)更好的“金句”,可惜一些人把他淡忘了。
陶澍是文人雅士,更是晚清重臣。他的降生對(duì)于安化,是多了一位黑茶知音;而對(duì)于萬(wàn)馬齊喑的晚清,卻是產(chǎn)生了一位杰出的思想者和實(shí)干家,他似乎是為振作晚清的頹勢(shì)而生,是為改革晚清的“經(jīng)濟(jì)體制”而生,是為樹(shù)起“經(jīng)世致用”的湖湘文化而生。這或許是歷史伏筆吧。
作為道光朝兩江總督太子少保的陶澍,是湖南這塊土地上自古以來(lái)最大的朝廷命官之一(明朝茶陵李東陽(yáng)為明弘治朝內(nèi)閣首輔,嚴(yán)格講他是出生京城的湖南人,并未在湖南生活過(guò)),而且,陶還是清官、能官、改革家,這在封建專(zhuān)制社會(huì)尤顯難能可貴。他不僅與道光帝為首的清朝廷有良性的互動(dòng),得到道光帝的高度信任和贊賞,還對(duì)魏源、賀長(zhǎng)齡、曾國(guó)藩、左宗棠、胡林翼等人的提攜扶持,起著不可低估的作用。
咸豐年間,朝野流傳一句話(huà):中國(guó)不可一日無(wú)湖南,湖南不可一日無(wú)左宗棠。陶澍任職兩江總督到江西閱兵,順道回安化老家掃墓時(shí),與左宗棠有過(guò)一次相遇。因?yàn)樘珍呐e薦,歷史留下了一個(gè)慧眼識(shí)珠、禮賢下士的傳奇。左宗棠后來(lái)當(dāng)過(guò)陜甘總督、兩江總督,被人稱(chēng)為晚清官場(chǎng)上的“鷹派”,他立下了從沙俄手中收復(fù)新疆的不世偉業(yè),為中華民族立下了功勛。若沒(méi)有這次在醴陵與陶澍的會(huì)見(jiàn),歷史會(huì)不會(huì)改寫(xiě)還真難說(shuō)。
當(dāng)時(shí),陶、左二人地位之比,堪若天淵。
陶:兩江總督,朝廷柱石;左:舉人一枚,淥江書(shū)院山長(zhǎng)(相當(dāng)于中學(xué)校長(zhǎng))。
陶:年紀(jì)58歲,政壇耆宿;左:年僅26歲,任山長(zhǎng)兩年。
陶:政聲清名滿(mǎn)天下;左:在地方小有名聲。
醴陵是由贛入湘的必經(jīng)之地。在這里,最亮的一顆星與一盞豆油燈相遇了,其緣于左宗棠應(yīng)縣令之請(qǐng)寫(xiě)在侯館(類(lèi)似于縣政府招待所)的一副對(duì)聯(lián):“春殿語(yǔ)從容,廿載家山印心石在;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翹首公歸。”作者是左宗棠。二十幾個(gè)字的對(duì)聯(lián),濃縮了陶澍一年內(nèi)兩次被道光帝接見(jiàn)君臣相得的殊榮,又贊譽(yù)了其先祖陶侃督八州軍事的光輝歷史,還寫(xiě)了家鄉(xiāng)子弟對(duì)陶的欽仰。
陶澍從對(duì)聯(lián)中察覺(jué)出作者手筆不凡,于是兩人促膝長(zhǎng)談,竟至達(dá)旦。一宵談話(huà)改變了左宗棠的命運(yùn)。陶視左為天下奇才,年齡相差二十多歲的二人竟訂忘年之交。一年后左進(jìn)京考進(jìn)士落榜,轉(zhuǎn)道南京總督府作客,兩人約定為兒女親家,陶澍將兒子桄托孤于左。正是這次相見(jiàn),左宗棠在陶澍去世后,到陶的老家小淹當(dāng)了陶桄八年家庭教師。八年中左閱讀了陶澍家中藏書(shū)和奏稿、邸報(bào)。對(duì)左熟悉國(guó)內(nèi)局勢(shì),朝廷運(yùn)作方式,乃至奏折的寫(xiě)作起了極大作用;尤其藏書(shū)中有關(guān)經(jīng)濟(jì)、輿地的著作,對(duì)日后左熟悉新疆山川地理,為收復(fù)新疆打下了深厚的知識(shí)基礎(chǔ)。
一代名臣俯身與一位山長(zhǎng)抵膝傾談,需要不俗的胸襟;視一個(gè)舉人為奇才,需要過(guò)人的洞察力。
陶澍直接影響了晚清湖南人才群體的勃興,又施澤于一撥撥湖湘人才的蔚起。史家蕭一山說(shuō)清朝“中興人才之盛,多萃于湖南,則由于陶澍種其因”“不有陶澍之提倡,則湖南人物不能蔚起,是國(guó)藩之成就,亦賴(lài)陶澍之喤引爾”。說(shuō)陶澍是晚清湖湘諸杰的精神導(dǎo)師和為官行政的楷模,應(yīng)該可以成立。
如果說(shuō)黑茶是安化經(jīng)濟(jì)發(fā)展的名片,是響當(dāng)當(dāng)?shù)挠矊?shí)力,那陶澍則是安化耀眼的文化歷史名片,是光閃閃的軟實(shí)力。
安化人無(wú)疑意識(shí)到了陶澍于安化發(fā)展的巨大作用,所以在縣城修建有陶澍廣場(chǎng),有陶澍路;并且在小淹重建了御碑亭。
然而令人遺憾的是,對(duì)小淹陶澍故居、陶澍陵園,雖進(jìn)行了一定程度的修復(fù)修整,但仍難掩荒涼之象。
與滿(mǎn)大街都是黑茶店、黑茶館、黑茶企業(yè)越做越大的興旺景象比,對(duì)陶澍文化的挖掘,對(duì)陶澍故居、陵園明顯重視不足投入不夠。在陶澍故居、陵園,甚至看不到一本介紹的書(shū)籍,也難怪游人稀少。
安化人,不僅僅要以黑茶為榮,更應(yīng)該以陶澍為榮。
我想,把陶澍這塊文化名片擦亮,應(yīng)該成為安化人的共識(shí),并見(jiàn)諸于實(shí)際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