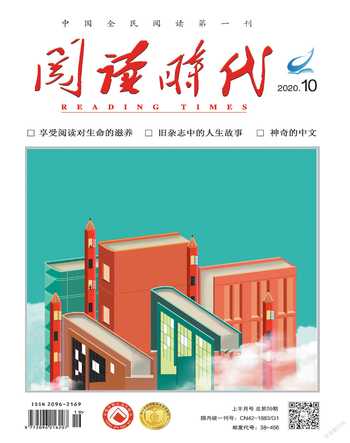宋詞中的芍藥
吳倩

宋代文人鐘愛以芍藥入詞,字里行間吟詠著芍藥的萬種風情,展示內心豐富的情感世界。芍藥與情的聯系最早可追溯至《詩經》,“維士與女,伊其將謔,贈之以勺藥”(《詩經·鄭風·溱洧》),借芍藥表達惜別之情。魏晉南北朝至唐代,文人側重于在詩詞中展現芍藥的形、神、色,如“光譬朝日,色艷芙蕖”(辛簫《芍藥花頌》)。這一時期的芍藥詩詞數量不多,查《全唐詩》(1999年中華書局版),有七十四首提及芍藥的詩作。經過數代的錘煉,芍藥意象在宋代發展至巔峰,據統計,《全宋詞》(1999年中華書局版)中有一百二十八首吟詠芍藥之詞,八十次稱作“芍藥”,五十四次直呼“紅藥”,稱“將離”的有一次。更重要的是,宋代文人在文學意象的使用上,將芍藥作為觀賞物的主題明顯減少,注重其情感意蘊的詞作大幅增加,文人豐富的情感世界通過芍藥詞的創作得以展現。
宋詞中的芍藥,常被文人視作愛情的象征物。楊澤民的《四園竹》記載了一段纏綿悱惻的愛情故事:“殘霞殿雨,皞氣入窗扉。井梧墮葉,寒砌叫蛩,秋滿屏幃。羅袖匆匆敘別,凄涼客里,異鄉誰更相知。念伊其。當時芍藥同心,誰知又爽佳期。直待金風到后,紅葉秋時。細寫情辭。何用紙。又卻恐、秋深葉漸稀。”一抹殘霞,幾番風雨,落葉滿庭,砌蛩訴情。深秋時節,文人獨在異鄉,對心上人的思念之情如潮水般洶涌而來。無奈芍藥之約已過,情意難寄,只盼情深望伊知。詞中脈脈含情的芍藥是文人與心上人的愛情信物,象征著他們情深似海的愛情,令人心動。周邦彥的《解連環》傾訴了戀人分離后的相思之苦,“燕子樓空,暗塵鎖。一床弦索。想移根換葉,盡是舊時,手種紅藥”,燕子樓空,琴箏蒙塵,樓前花草不再是她舊時所種的紅藥。語短情深,當年親手所種芍藥是愛情的見證,如今芍藥不再,這一意象亦蘊含著分離的凄楚。
芍藥又稱將離,“芍藥一名可離,故將別以贈之”(崔鮑《古今注》)。南渡分流后,宋人體會漂泊之苦、分離之悲,芍藥蘊含的離情意蘊被文人們在宋詞中廣泛地運用。曾惇的《訴衷情·別意》云:“鄞江云氣近蓬萊。花柳滿城隈。風流謝守相遇,應覆故人杯。煙浪暖,錦帆回。莫徘徊。玉霄亭下,芍藥荼,都望歸來。”繁花如畫,云濤煙浪,一壺酒,兩相離。玉霄亭下,芍藥盛放,以此贈別,望君早日歸來。詞中借芍藥表達惜別之情,與古典詩詞中常出現折柳贈別的意蘊同出一境,此時的芍藥不同于普通的花卉,而是寄寓離情的象征物。陳德武的《望海潮》,描繪了文人與親人依依惜別的畫面,“陵山載酒,泗河揚柁,尊前折盡將離”,分離之際,正是芍藥盛放,濁酒一杯慰愁腸,此去經年,多相思,莫相忘。全詞未提“芍藥”二字,而是以其別稱“將離”代指,其蘊含的離情更加清晰易懂。
一春花事,芍藥為殿,芍藥開放的時節注定了其意象亦承載了文人的愁情。芍藥有一別稱,名為婪尾春,“婪尾酒乃最后之杯,芍藥殿春,亦得是名”(宋陶穀《清異錄·花》)。芍藥殿春,不免寂寞,故芍藥多以孤寂、哀愁的意象出現在宋詞中。姜夔《側犯·詠芍藥》訴孤苦之情:“恨春易去,甚春卻向揚州住。微雨,正繭栗梢頭弄詩句。紅橋二十四,總是行云處。無語,漸半脫宮衣笑相顧。金壺細葉,千朵圍歌舞。誰念我、鬢成絲,來此共尊俎。后日西園,綠陰無數。寂寞劉郎,自修花譜。”春光已去多怨恨,惟有芍藥訴柔情。細雨朦朧,二十四橋間,芍藥吐蕊,脈脈含情。芍藥風韻依舊,而文人已兩鬢斑白,置身于這紅花綠葉間,顯得分外突兀。姜夔一生孤苦,漂泊于江湖,生性清高孤僻,詞中“千朵圍歌舞”以熱鬧之景反襯白石寂寞之心境,詞末“寂寞劉郎,自修花譜”道盡無數滄桑凄苦之情。
通過宋詞中的芍藥意象,我們可以感受到宋代文人對情感的體驗和認知。就“芍藥”及其各別稱的使用次數而言,南宋文人的使用次數遠高于北宋。那么為什么芍藥意象會在宋代,尤其是南宋集中出現,并且被賦予了更深層次的情感內涵呢?
宋代動蕩的社會環境,應是芍藥意象頻繁出現,情感意蘊得以豐富的主要原因。宋代政治內有冗官、冗兵、冗費之弊端,外有對外戰爭屢戰屢敗之恥辱,同時朝內激烈的黨派戰爭加劇了政治局面的混亂。為鞏固中央集權,宋代高度重視文治,為文人提供了更多的入仕機會,所謂“布衣草澤,皆得充舉”(《宋史紀事本末》卷7)。原本“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汪洙《神童詩》)的仕宦之道應該塑造出積極入世、充滿抱負的文人,但宋代內憂外患的政治局面令文人逐漸變得深沉內斂。尤其是南渡分流后,文人歷經現實的坎坷與磨難,體驗百味人生,在詞作中詠史懷人、感慨滄桑,借以表達南渡文人飽經滄桑后傷感多情的心境以及婉約細膩的情感,呈現出沉郁頓挫、婉轉多愁的一番意境。芍藥作為一個典型化文學意象,也由此生發了傷感悲涼、寄托遙深的詞作。如姜夔《揚州慢》“二十四橋仍在,波心蕩、冷月無聲。念橋邊紅藥,年年知為誰生”,詞中多用“寒”“冷”等字眼,字里行間散發著一抹清冷,彰顯著文人愈發內斂深沉的性格特征,與唐代意氣風發的文人氣度迥然不同。芍藥意象因此承載了文人深沉的悲痛之情,寄寓著愁緒哀怨,展示了有宋一代文人內在的情感世界。
宋代重視理學的社會風尚,使文人更加注重芍藥內蘊的挖掘,這一轉變為芍藥意象在宋詞中高頻出現以及其內涵拓展提供了契機。宋代理學發展,文人對內蘊的重視超過對物色的推崇,芍藥詩詞創作于此時推陳出新。如果說,芍藥在宋前多以物色之美、形象之美出現在文人墨客的作品中,那么芍藥在宋詞中已突破自然觀照的束縛,發展出情感的意蘊,實現從自然特征的描摹到情感意蘊的解讀這一轉變。文人注重內在品格的修養,“紅藥殿春,更作薄寒清峭”(劉塤《惜余春慢》),芍藥以其不與群芳爭春的清高氣節成為文人托物言志的載體。尤其在政局不穩、內憂外患的社會環境下,芍藥意象蘊含的遺世獨立的高潔氣質以及多層次的情感意蘊更加令文人向往,芍藥便由此成為宋詞中的高頻意象,在宋詞中展現了文人豐富的精神世界。

芍藥自身的形神色與宋代文人的審美心理相契合,也使得芍藥意象逐漸成為文人情感的載體。芍藥莖葉柔軟,香氣襲人,色彩艷麗,這些自然特質無一不洋溢著柔美和優雅,其風姿綽約的情韻,與宋代文人至柔的創作情懷和審美心理相契合,因而在宋詞中被賦予充沛的情感,承載含蓄婉轉的意蘊,逐漸成為文人抒發情感的載體。
王國維先生云:“一切景語皆情語。”宋代文人或借芍藥象征纏綿悱惻的愛情,或以芍藥表達惜別之情,或將愁怨附著于芍藥,可以說是借著芍藥展現了豐富的情感世界。然而任何一種文學意象都不應僅僅局限于是文學創作主體的產物,“凡交情之冷淡,身世之飄零,皆可于一草一木發之”(清陳廷焯《白雨齋詞話》),社會環境、時代背景影響著文人的價值取向和情感體驗,故他們在借助草木抒發情感時,表達方式各有不同。從先秦至宋,芍藥的意象大致經歷了從形至神,由觀到魂的發展過程,在這一過程中,文人將其充沛的情感體驗灌注于詞中,使得意象的內蘊更加豐富與深刻。宋詞中的芍藥意象的發展正是我們探尋宋代文學發展的窗口,透過文字,我們可以看到宋代文人豐富的情感世界,體味文人的百態人生,也能深入了解宋代文學創作的時代特征和風貌。
責編:何建嬌